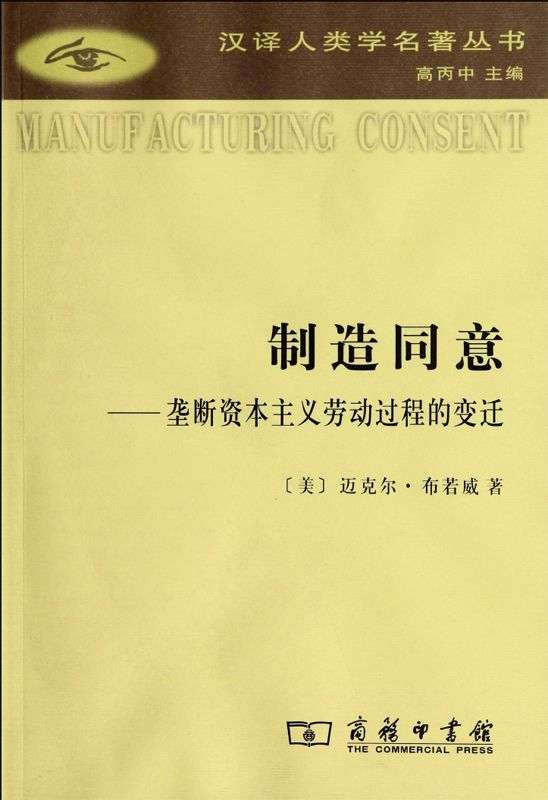转载 | 第三章:半无产阶级化与身份政治 — 《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 潘毅 卢晖临
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和抗争
潘毅 卢晖临
目录
第三章:半无产阶级化与身份政治
老张是个瓦匠,是我们在美丽新世界简陋的工棚中遇到的资格最老的工人。从70年代后期起,老张就来到北京搞建筑,至今已经三十年。老张初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个刚刚完婚的小伙子,现在已经50出头,女儿都已经上大学了。长期在工地上工作,老张的腰早就被压弯了,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他早就不想在这行干下去了,但是为了女儿的学费,他还是得一次次出来。这么多年干下来,老张已经数不清他盖过多少楼。他看着北京城一天天长大,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他熟悉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哪栋楼什么时候建,哪条路什么时候修,都能娓娓道来。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真正的落脚地。每逢麦收、秋收和春节,他都要回到河北的老家。无数次往返于北京的工地和河北的老家之间,他却从来都不敢想要把老婆和孩子都接过来,在城市安家。像老张这样的工人为什么一定要背井离乡?为什么能够长期忍受那么恶劣的劳动条件?又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农村的家?简陋的工棚,作为他们在城市临时的落脚地,既承载着他们的责任与梦想,又呈现着他们的痛苦与创伤;城市中的大工地,让他们既想离开,又不得不回来。在这个过渡性的空间中,一个新兴工人阶级破茧而出的痛苦与挣扎,被如此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并非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就好像这个阶级的形成过程一样,一早便已开始,却似乎永远不能结束——一个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半无产阶级化
改革开放,既是与世界经济接轨,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同时把它打造成了“世界工地”。这一状况是前所未有的,而与之相伴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却有很多先例。三十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打工的现象,我们在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指的是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使其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的过程。换句话说,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往往会同时出现一个急剧的城市化过程,即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转移,农业人口不断地转化成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渐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化的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受控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也无法占有他们的劳动产品。
工业化及其相伴而生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主导。而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除了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之外,更受到体制力量的影响。为了实现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国家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限制,允许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与此同时,却没有为其完成城市化提供必要的条件,如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的集体性消费设施。
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的长期存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历史上,无论是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源地之一的英国,还是代表先进资本主义的美国,或者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日本和韩国,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整体进行的。劳动力在迁移的同时也将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同时转移到城市中,从农民转化为工人,成为无产阶级。而对中国的农民工而言,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很多农民工之所以无法在工作的城市安家,是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居留受到双重的限制。一重是来自制度层面的限制,户籍制度为他们在城市的长期居住预先设置了障碍;第二重是阶级层面的限制,低微的收入使得他们无力承担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Solinger,1999)。在双重的限制之下,农民工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空间发生了实质性的分离。他们在城市中的停留往往只是出卖劳动力,参与生产活动,而劳动力的长期再生产——生活和繁衍——则只能放在农村老家进行。可以说,对于农民工而言,其阶级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诞生伊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之所谓长期得以维持,根本上是它有利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需要。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意味着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同时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们像历史上所有工人一样在城市中参与生产,却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工人。
于是,老张这样的工人只能背井离乡,年复一年地奔走于城市工地和农村老家之间,在城市打工,在农村生活。作为带工的技术工人,老张在2008年每天可以挣100多元,按照每个月出工28天计算,月工资收入接近三千元。然而,即使他每个月都能有活干,也无法维持一家四口在北京的生活开支。即使将家人留在农村生活,老张还是欠了很多债。他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在张家口上大学,小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两个孩子读书给老张很大的经济压力。麦收时节回家,小儿子生病住院,医药费要花好几千块钱。老张无奈的说,这次回家又借了三千块钱。老张的工资收入在建筑工地的普通工人当中算是高的。自从06年建筑工人工资普遍上涨后,技术工人的工资通常是70元,非技术工人当中,男工是50元,女工则只有45元。连老张都无法在城市中立足,这些普通的工人就更加困难了。
像老张一样,大多数建筑工人一方面无法在城市立足,必须在农村安老家生活;另一方面,为了生计,又必须一次次来到城市工作,与家人团聚的时间十分有限。如果顺利,老张每年有十个月都要在外地工作,只有春节的一个月,以及麦收、秋收的半个月可以呆在家。一般的想象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老张作为中年人,上有老,小有小,家庭负担要重一些。而事实上,年轻人并不比他更轻松。袁飞的哥哥今年20多岁,结婚第三天就去了工地打工,08年的春节刚过,又依依不舍的离开不到一周岁的孩子,踏上打工之路。
如今,袁飞也要重复他哥哥的道路。刚刚结婚没几天,马上就得重返工地。为了给他盖房子和结婚,家里欠下了一大笔债。债务当头,他只能选择独自在工地上度过蜜月。想起这些,他心里就感到烦,总是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却不知道该如何发泄。谈及带老婆来北京的做法,他说自己也这样想过,但实在太困难了。老婆在家里的服装厂上班,一个月能挣1000来块钱,在家里不需要什么花销,一年下来多少还能攒下点钱。到北京未必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两个人一起生活还要租房子,生活费用太高。将来有了孩子,还要负担孩子上学,仅凭他们现在挣的钱根本负担不起。再说,工地上的工人们都住在宿舍,早上5点多钟起床,6点钟开工,晚上通常6点多才能下班,即使自己花钱租房,来回折腾太辛苦,时间上也赶不上。没有办法,他只能和其他工人一样,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像老张和袁飞这样常年待在北京的人非常多。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市区并不会太远,但他们却没有办法把家安在北京。他们在身体劳累的同时,还要饱受思乡之苦。不仅如此,作为建筑工人,他们连基本的工资都不能及时兑现。工资长期遭受拖欠,使得他们只能靠微薄的生活费度日。劳动关系的不明确将老张这样的工人推入了无产阶级化谱系的更低位置。建筑工自进入建筑行业的生产体系开始,其作为工人的身份就未曾得到合法的确认。如果存在一个无产阶级化的系谱,以福特主义体系下的产业工人的生活境遇为相对受保护的完全无产阶级化的标准,那么,中国建筑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则是远远未完成的。他们连完全的商品都称不上,只能算作半商品化的劳动力。
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符合资本增殖的内在需要,正如沃伦斯坦指出的,“半无产阶级化”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资本寻求更低成本劳动力的过程,资本家“更愿意其雇佣工人位于半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而不是处于无产阶级化的家庭中”(Wallerstein,1983:27)一般的看法认为,半商品化,指的是与完全商品化的工人相比,建筑工在家乡还有土地,他们并没有与生产资料完全的分离。当他们失去城市的工作以后,还可以回家养老。而事实上,农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早已虚空化了,土地已经失去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只能提供简单的生活资料,甚至被抛荒,很多农民工已经与农业生产发生实质性的分离。表面上看,一片土地,为农民工提供了一片美好的田园和坚实的堡垒,是他们退回农村的基本保障;而实际上,土地却成为新的枷锁,为资本肆意的剥削农民工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并将他们推入更加无保障的境地,让他们处在“饿不死,养不活”的状态中。半商品化,似乎意味着建筑工比完全商品化要有更多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们因为有了一小块土地,可以更多地决定是否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吊诡的是,他们比完全商品化的工人处境还要艰难。就劳动关系而言,半商品化真正的内涵则在于建筑工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却不被当做一个正规的雇佣工人来对待,一方面他的劳动力价值被贬低,另一方面,他的劳动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甚至无法按时拿到最基本的劳动报酬。
在马克思的讨论中,劳动异化状态的极限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bodilysubject),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马克思[1844]2000:53)讽刺的是,在现在的建筑行业,劳动者从属于资本的极限被进一步拓展,异化状态的顶点是必须把劳动者维持在不完整的工人的状态,才能维持其作为肉体的主体,而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还不能是完整的工人。
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维持和再生产工人阶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必要条件”(马克思[1867]2004;660)。劳动力的生产是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活的个人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它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马克思[1867]2004:198)。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了对于劳动个体来说基本身体再生产的必要性:“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变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在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出生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夺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1867]2004):660)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劳动个体的精神与社会需要的同等重要性:“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马克思[1867]2004):269)
劳动力再生产包括生产资料以及使生产资料得以实现的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长期的再生产。从最根本上来说,社会再生产主要依赖于以代际以及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生物性的劳动力再生产,通过衣食住行以及医疗照顾等方式完成。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还要求一套文化形态与实践。在西方的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工人斗争都是围绕着劳动力再生产的内容和边界而展开的,在福特主义之下,工人阶级的这类斗争取得很大进展,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教育获得机会、福利、以及有益于工人的社会与文化的服务的增加。这些进展都是对工人社会再生产的边界与内容的重新界定,而每一个进步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成本的相对增加。除了工人斗争之外,政府、家庭、资本以及市民社会等都是对劳动力再生产进行重构的重要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调节行为(通过税收的循环和国家支持的债务表示出来)在确定社会工资和规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Harvey,1982:111)。布洛威(Buroway)从生产政治的分析范式出发,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的批判,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生产体制概念共包括四个基本维度:即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等两个微观层面的维度,以及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两个外部的宏观层面的维度。他将劳动力再生产作为生产体制的重要维度之一,并强调工人用以维持自身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和其家庭生存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必然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制度安排(产业制度、福利制度、就业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条件下甚至还包括国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国家干预的影响。他认为,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削弱和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参见沈原:2006)。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人享有国家主人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工人为国家工作,国家通过“单位”制度不仅发给工人工资,更是全面介入并且承担着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即终身雇佣、住房、医疗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李培林、张翼:2000)。总而言之,“单位”制度曾经是中国改变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在这种制度中,国家全面控制着劳动力再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与管理。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仅带来了经济形态的转变,也带来了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国家干预的深刻转变。国家不仅逐渐退出了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劳动力再生产领域,而且从一开始便缺位于农民工这一特殊劳动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行政与市场的双重壁垒限制了农民工在城市安家的可能性。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户籍制度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国家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
保留农民工的土地,同时不给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权利,这种制度安排将农民工牢牢地锁在了土地上,让他永远难以转化成为真正的工人。对于建筑工人而言,尽管一年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城市工作,但他在心理上永远认同自己是农民,自己属于农村(陈映芳,2005;王小章,2009)。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被隔离在工棚的四周。尽管常年在北京工作,老张从来去没有去游览过那些名胜古迹。他的活动范围就在工地的周边,偶有闲暇,会坐在马路边数数汽车。
同时,制度壁垒的安排给资本提供了机会,使之可以无限地压低工人的工资,给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设置了第二重的壁垒——市场壁垒。不仅如此,在将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农村以外,资本还肆意地简化了工人在城市进行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建筑工主要居住在为方便生产而在工地附近临时搭建的各种宿舍里,条件简陋,隐患无穷。具体的住房类型主要有三种:活动房(或简易房)、平房和工棚。平房条件相对较好,但所占比例往往很低。活动房是最主要的住房类型,一般内设高低床,每间宿舍面积约20平方米,居住8~12名工人,住宿区有简易的厕所和洗澡间。工棚多由草席或石棉瓦做围墙,脚手架做支架,石棉瓦做顶棚,既不防风,又不挡雨。建筑工宿舍几乎都与施工现场连为一体,即使在夜间,加班运转的机械轰鸣声也会造成严重的噪音问题。对于建筑工而言,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主导和组织的。工地上的临时的宿舍虽然依然承担着劳动力日常生活再生产的功能,但却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宿舍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主要提供给短期雇佣的农民工,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体企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之可能。工地为工人提供的住所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任焰、潘毅:2006)。工棚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建筑物,本身就隐喻了建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性和临时性存在状态。即便他们常年转战于城市各个工地上,即便很多的城市建筑物都由他们亲手建造,但是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在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地位。城市不断推卸和否定对于农民工的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责任,而他们在城市打工的工资中,并没有被计入可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再加上就业、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源的供给匮乏,因此在空间与社会的意义上劳动力的使用与再生产过程长期割裂状态下的农民工,只能不断游走于城市的边缘,无法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源。
自2003年温家宝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之后,在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压力下,国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意图将农民工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但迄今为止,推行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签订劳动合同是农民工享有有限的社会保险的前提条件,根据国务院2006年调查,尚有46.3%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这意味着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农民工没有办法享受任何社会保险。在建筑行业,根据我们在北京的调查,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更是低于10%,不仅社会保障对于广大的建筑工人来说遥不可及,就连基本工资的按时发放都成为问题。
在国家和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无法完成给中国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制造出更大的张力和更深层的矛盾,而这些张力和矛盾反过来又使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身份政治
我是一名“民工”,尽管我心底讨厌这个字眼
建筑工地的风霜雨雪,酷署(暑)严寒,我能忍受但>我接受不了
城里人那鄙视的目光,生冷的态度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是贼吗
出门前,母亲的训导还在耳边
“做人要本分”
我不明白
城市的建设哪里没有我们的身影
我们的衣服脏
口音土
但我们的手不笨
我们能盖出漂亮的高楼
我们能修成宽广的马路
我们是祖国的建设者
我们拒绝歧视和冷眼
我们要有尊严地生活!
——“我是一名‘民工’”,一首出自建筑工人的诗歌
在中国传统社会,盖房子是一门手艺。大户人家盖房子要雕梁画栋,非常细致,需要请技术精湛的工匠。普通人家盖房子也要请有经验的师傅来把关。手艺人不但能养家糊口,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声望。老张的父亲就是当地有名的泥瓦匠,那时候谁家盖房子都要请他去把关,对他毕恭毕敬。能成为包括泥瓦匠在内的手艺人曾经是很多农村人的奋斗目标。
随着分包制度在市场化大潮中的再次引进,建筑工人的身份却一落千丈。规模庞大的建筑工人,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人身份。他们既不是受人尊敬的工匠师傅,也不是乐于奉献的劳动模范,而是靠出卖自己的体力,挣点血汗钱的人。从业多年,他们从来都没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只能跟着大大小小的包工头,以游击队的形式转战于各个工地。作为建筑业农民工,层层分包的体制将他们打造为一个残缺的劳动主体,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城市用一道道制度壁垒将他们阻隔在外面。城市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想承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公共福利,甚至不给他们永久居住的权利。他们在城市永远只是暂住人口。最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市民的身份,不时遭遇到制度性的暴力。在我们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年纪比较大的工人向我们讲述辛酸往事。
老张回忆说,刚进城打工的时候,他们被称作盲流,随时面临被警察扣留的危险。他们白天不敢到处乱走,见了穿制服的就躲,与城市管理人员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要求农民工办理暂住证,但不少持有暂住证的农民工仍有被警察带到派出所的经历。在工地上,也会有警察来查暂住证,态度稍微不好就会遭受蛮横对待。有一个工人向我们回忆说,97年冬天的时候,有天下午警察到工地上查证,他说没有,警察让他出示身份证,他出示后,警察就把身份证拿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他已经睡下了,警察又来到工地上,把他和同屋从被窝里抓起来就带走了,关在区公安局,不给吃喝,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六点才放他们走。当晚很冷,他们就都往屋子里的暖气边上凑。凑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放在暖气上烘干的警察的鞋碰掉了。第二天警察发现了很生气,而他刚好在暖气旁边,警察便打了他两个耳光,又踢了他两脚,他的后背撞到暖气片上,从此落下毛病。说起十年前这段经历,他还忍不住激动地流泪。
无奈之下,有些工人只好将在城市里来所经历的这一切当成是对自己的磨难,当成一种“修炼”的过程。
“以前我们到城市就是一头猪,到年底老板随便赏你俩钱儿。我们就是散仙,不是正仙,要修炼,当初说抓我们就抓我们,农民工进城打工要三证齐全,没有三证被警察抓住就送到昌平筛沙子,啥时候筛够路费了啥时候送你回老家,现在社会进步啦,可以谈价钱啦,什么时候我们修炼成正仙就好啦。”
城乡分割让他们遭遇制度性的伤害,而城里人的歧视又仿佛在他们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他们亲手建造起精美的城市,却被打上耻辱的烙印。在今天的中国,农民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群体,其悲惨的处境博得了一些舆论同情,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社会污名化了(张慧瑜,2005;李红涛,乔同舟,2005)。在城市人的日常语汇中,“农民工”往往是素质低下、愚昧无知、不文明等等的同义词。农民工的身份对于建筑工人的个人尊严造成极大的伤害,让他背负着沉重的污名,彻底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
袁飞在回顾这些年的打工经历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出来打工以来,曾经去过很多地方,有繁华有荒凉,虽然有时会想家,但是也学到了一些在学校没法学到的知识和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经验,可是有一点,我到现在还接受不了,就是有少数城里人总是看不起我们建筑工人,每次出来和回家,坐车时,有些人看到我们背着行李,他们看你的眼神让我总是感到不舒服。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一个家长对孩子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就让你和他们一样打工去。”那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我伤透了心。他说:“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我才不要向(像)他们那样呢。多丢人!”
这种公开的歧视行为让他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这也是建筑工人这个群体普遍的感受。一个建筑工人向我们说,现在他们已经很少坐公交车了,就是为了避免和城市人接触。他们下了火车有时宁肯直接打车到工地,就算多花很多钱也不愿坐公交车遭受城市人的白眼。建筑工在城市里遭遇的这些经历让他们深深地知道,他们和城市之间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更加清楚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更加固化自己作为“农民工”的身份。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诸多困境,经常被放到“城市融入”这一话题之下讨论,论者多从农民工的主观意愿和自身素质,从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角度探寻“不融入”的原因。农民工的认同问题,其结构性的原因在于背后的身份政治,而后者正是国家配合资本增殖需要而沿袭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结果。
中国特色的“圈地”
改革开放,使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工地打工,这是一种离开家乡的自由,释放着他们渴望改变的欲望,而伴随着这种自由的,则是向城市资本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一旦他们获得这种自由,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失去了前进或者后退的自由:在从一个工地跳向另一个工地的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无法继续前进——成为真正的工人或者城市人,他们在城市是一个陌生者,是一个永久的过客;另一方面,他们也无法回头——重新去做真正的农民。在今天,“农民”这个前缀,除了仍然清楚地标示着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的正式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次等属民身份,它原本所暗含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形式、内容以及本质的意义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劳作方式的贬值、农业生产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再在物质与精神的层面上继续支撑他们的生活,农民工与其农村社区之间的实质性的分离已经开始发生。
在以往关于农民工的研究中,土地被认为是承担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依托,并被视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亿万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却没有引起巨大社会震荡的一个重要的“减压阀”,但是,土地不但在经济意义上已经失去了生产资料的位置,也渐渐在文化意义上失去作为精神依托的地位。换句话说,农民工虽然拥有土地(使用权),还没有发生英国资本主义初期的“圈地”运动,但在经济生活和精神意义上,中国特色的“圈地”业已发生。这种“圈地”无疑令他们逐渐丧失了返乡的欲望和实际的可能性。于是,他们只能一次次走向城市,在城市中体验着“做小”的生活:“家里没钱,小孩儿要上学,不出来怎么办?村子里从学生一毕业到50岁的人都出来啦,全家人都出来啦,和封建社会一样,给人家做小啦,我们养活人家,自己得养活自己。”
城市呆不住,家乡回不去,一首源自建筑工人的歌曲,将这种困于城乡之间、进退无据的漂泊无根感揭示得淋漓尽致:
剪不断的思念
北京好大好大
北京好冷好冷
北京好热好热
北京没有我的家
我已多年没回家
家里的爹娘还好吗
我好想回去看看
看看我的爹娘和故乡
……
北京啊北京
你是否是我心中的北京
你难道只是我的驿站
离开你,我又要去何方?
对于这些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建筑工人来说,家是他们难以割舍的牵挂。作为“农民工”,他们长期漂泊在外,不但忍受着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饱受思念之苦。
袁飞兄弟都是新婚不久就到工地上打工。在河北尧村,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刚刚结婚没多久就出去打工。袁飞的哥哥告诉我们,“要是在家里能挣到钱,谁出来受这份罪啊?!”在家里有他的老婆孩子,在家里他不用大热天和很多人挤在一块儿,在家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人时时刻刻监督着他。他结婚之后在家里养猪,两年赔了十万块钱。弟弟刚刚结婚,家里又借了一大笔债,没办法,他只能离开老婆孩子,一个人到北京的工地上打工。他很想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在随身带的钱包里放着孩子的照片。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指责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制限制了人身自由,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人间悲剧。改革开放给了人们自由流动的机会,让很多牛郎织女可以相聚。人们欢呼市场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但却往往忽略了市场在两亿农民工那里造成更多牛郎织女、更多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事实。同样是分离,不过现在是市场的力量取代以前的行政力量,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分离。
建筑工地上的河北人还能经常回家看看,四川、江苏等地方的人一年顶多回去一次,一些工人甚至几年都没有回家。老张出来打工三十年了,三十年里老张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今天的小老头,把整个青春洒在北京的工地上。女儿常常问他,为什么总是不在家?老张很心酸,觉得对不起家里人。
陈勇是四川人,和所有四川籍的建筑工人一样,一年才回一次家。他一个人常年在工地上,妻子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他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家庭没法照顾,他尤其对于自己的父母感到深深的愧疚,父母年事已高,自己在外面打工,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道。
在许多工人的日记和信笺中,“想家”和“梦到回家”等字眼也经常出现。回不去的家,成为他们在漂泊的生活中想象中的停泊地。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须依靠对农民工这一劳动大军的使用,然而这一群体的劳动者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略。农民工一方面为城市提供着廉价、新鲜而丰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打工阶级的命运实际上是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所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农民工身份中劳动力使用与劳
动力再生产本应是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可是在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进行资本积累)与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们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却表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国家一边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满足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一边却拒绝承担他们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换句话说,尽管农民工的劳动力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对于农民工群体自身来说,他们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却由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无法统一起来。这使得其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城市中难以完成,而这一劳动主体便只能永远停留,更确切地说是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
行文至此,我们又一次想起了老徐和等着跟他在老家相聚的妻子。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想到了这样一首诗:
轻轻的你走了,
又轻轻的来,
轻轻的你,
便如一阵风。都说你真洒脱,
六十年的岁月,
飘来荡去。都说你真懂事,
风有风的风向,
雨有雨的泪水。都说你真自由,
随风而来,
又随风而去。轻轻的你,
南柯一梦三十年,
放下左右逢源。都说你真美好,
风有风的风骨,
雨有雨的轻泣。轻轻的你倒下,
夜夜守护家乡的星空,
不带走一分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