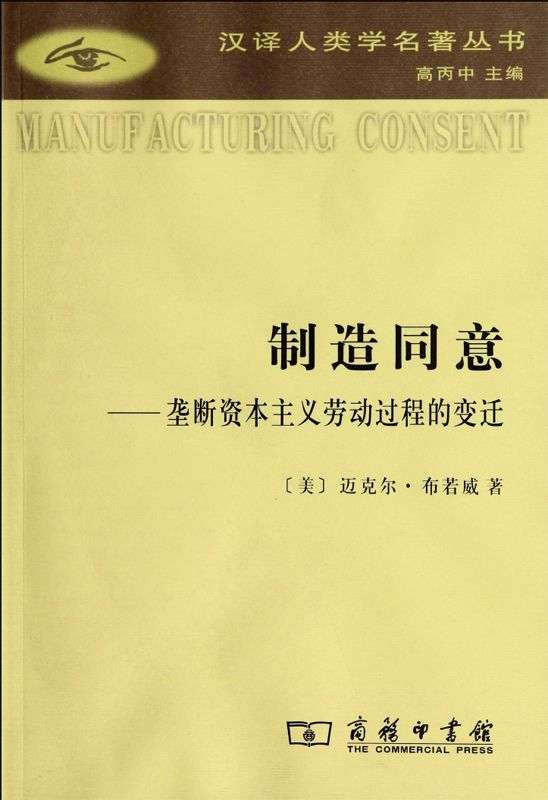序—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序
1974 年 7 月 2 日,我开始作为一名杂项机床操作工在联合公司——一个生产包括多种农业装备等产品在内的跨国企业——的发动机分部工作。小零件分部的计件工作机械车间使我想起了唐纳德·罗伊的关于产量限制的那些著名的报告。在重读了这些文章之后,我被他的观察与我自己在联合公司的观察之间的相似打动了。不过这也不足为奇。我知道英国的机床操作工和罗伊所描述的一样——对计件工资以偷懒、配额限制以及与辅助工人间建立非正式的关系等方式来应付。于是我求助于罗伊的 546 页的博士论文,其中密织着与他 1944 年到 1945 年之间在一家生产轨道支架的工厂时的经历相关的全部生动的细节。在开头的篇章中我发现机床的布局——钻床、磨床、车床等——与我自己所在的工厂的布局非常相似,于是我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结论:机械工厂通常都是按相似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随着每天对他的论文阅读的深入,我终于遇到了一处提及罗伊,像我一样,是沿着伊利诺伊中央铁路从芝加哥大学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的。接着我又遇到一处提到了那个他称之为吉尔的公司所在的小镇。这恰恰也是我所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地方。但这还不算太令人惊奇;毕竟在这一地区有很多机械厂。接着我找到了一处提及了一座四层建筑。看哪,据我的工友说,联合公司曾经位于一座四层建筑内。没错,那座被废弃的建筑矗立于离现在的地方约 1 英里远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轨道边上。是的,一些老前辈们还记得一个支架厂。在邻近论文结尾的地方定论出来了,在那罗伊留下了他的本地工会的号码。这一号码与我自己的一样。我的确误打误撞地来到了罗伊 30 年前研究过的那个工厂。即使吉尔已经为联合公司所接管,罗伊的支架厂和我工作的小零件分部仍具有极为接近的相似之处。30 年来,车间里什么保持未变,什么又发生了改变,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我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
罗伊的论文提供了一个经验语境。但是对车间的分析需要一个理论框架和关注焦点来评估时间带来的变化。罗伊的理论关注深植于工业社会学的传统之中,并围绕着“产量限制”这一问题。通过将这一“问题”的根源归因于工人们对管理的非理性的理性反应,罗伊成功地颠覆了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提出的信条,即以工人信仰不合逻辑的体系以及他们未能理解管理逻辑来解释产量限制。贯穿工业社会学著作的争论陷入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工人不更努力地工作。激进解释与保守解释之间的差异在于他们所作的假设。激进派认为产量限制是阶级意识、资本和劳工之间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冲突,或劳动的异化本质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保守派则从根本的和谐这一假设出发,将产量限制归因于工人们的天生懒惰、工人和管理者间沟通不充分、对工人们人性一面的关注不足,或工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与管理层的利益一致这样的“错误意识”。就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冲突或者一致的观点似乎都与车间里实际发生的事不着调。相反,讨论的范围应该转换,并且最初的问题应当用另一种方式提出。正如林德夫妇(the Lynds)1929 年所提出的:为什么工人这么努力地工作?
罗伊论文中的实际叙述表明这是个更加合理的问题。罗伊的那家千斤顶工厂里的机床工人以一种狂热的步调工作,一旦被打断会大发雷霆。诚然,这是个计件工资体系,但是正如罗伊明确指出的,工人们才不会为了多挣几分钱而“屁滚尿流”的。他们也不是因为热爱他们的老板而投入工作。贯穿他的整篇论文,罗伊的的确确地强调了他们对于被像“新手”那样对待的愤懑。然而,矛盾的是,他又试图估量和解释工人们“浪费”的时间。他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没有浪费更多的时间,尽管答案在他的解释中就可以找到。在他所作的观察和他提出的问题之间似乎有种基本的不和谐。
联合公司的劳动强度使我大吃一惊,其程度不亚于罗伊关于吉尔的描述。一开始,主要是出于害怕和不熟练,我对这种我认为是体力和技巧的透支既轻视又敬畏,情绪在这两者之间游移。为什么工人们强迫他们自己来提升公司的利益?为什么要和那些“不惜一切要从你身上再榨出一点油水”的那些“楼上的家伙”合作,有时甚至是超出他们的期望?但是没过多久我自己也设法超额、完成配额、寻找新诀窍、同时完成两件工作——冒着失去性命和肢体的危险来多做一个零件。是什么驱使我来增加联合公司的利润?为什么我主动地参与加强对我自己的剥削,并且当做不到的时候还会发脾气?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
对卡尔·马克思来说这也是个问题,而他的解答是强制。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劳工对于资本的毫无限制的从属关系可以解释很多车间里发生的事情。计件工资制被用来任意加强工作强度,因为工人们无法抵制随意的价格削减。对于采用计时工资的地方,工头可以随意解雇没有完成定额的工人。但随着工会和对某些最低雇佣权利的保护的出现,失业或不能获得生存所需工资的威胁已经逐渐与在工作场所工作的努力程度相脱离。仅仅强制已经不再能解释工人们到达车间后所做的事情。如我的白班搭档比尔向我保证的,“在这没人会强迫你,你要自己让自己继续工作。”一种自发的、同意的元素与强制相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对于同意的最精致和最富启迪性的分析可以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作品里找到。不过,他对于政治领域上同意的组织比起在劳动过程中的同意更为关心。在关于国家、政党和知识分子理论的发展中,他把强迫和劝说、强制和同意、支配与霸权混编并结合起来。只是在一篇题为“美国精神与福特制”的文章中,他才分析了劳动过程本身。在文中,他思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后期,在美国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在美国,整个生活都不受以往的支配体系的寄生残余所影响,而是围绕生产来运转;“在这里,霸权是在工厂中诞生的”。在我的研究中,我试图对这一有建设性的却又难以捉摸的意见加以发展和详细阐述。与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持有的见解不同,我打算论证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之际产生的——独立于学校教育、家庭生活、大众媒体、国家等等。简言之,本书从对马克思的批评出发,只是为了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回到他对劳动过程的兴趣焦点。
让我赶紧补充一点:这不是一部新马克思主义的习作,也不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学家们给他们希望认真对待的马克思主义加上的各种其他标签的习作。确切地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意味着至少三点:首先,我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中被认为是从直接生产者手中窃取无偿劳动的那种特有手段的变化和连续性。其次,我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历史上的最后一种社会类型。认为历史就应该停止在资本主义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我认为一种与现状根本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你愿意就把它叫做共产主义好了——是可能的和可欲的,并把这作为我的出发点。在这样的社会中,男人和女人都免受匮乏的压力,并从资本主义社会每天都存在的不安中解脱了出来,从而去塑造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共同决定谁来生产、怎样生产、何时生产和生产什么。马克思正是依据这种可能性(尽管其必然性未必充分)解释现在和过去。另一方面,社会学则要么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乌托邦,要么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因此它认为将来只是要消除目前的不完美,并且将现在认为是过去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终点。
正如社会学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了很多东西,并且部分地透过与之辩论而崛起,因此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抛开社会学。相反,马克思主义必须有选择地吸纳社会学的部分真理。确实,20 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安东尼奥·葛兰西、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德拉沃普(Galvana Della Volpa)——都大量地借用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社会理论与哲学。马克思自己就建立了这种范式:他以黑格尔(Hegel)、斯密(Smith)和理嘉图(Ricardo)以及其他人作为出发点,并将他们的见识变换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元素。在我构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努力中,我将以工业社会学的主流观点为出发点,并把其中的许多见识重新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去。
从而,贯穿于本书中的主要内容是与社会学的对话。为了篇幅和阅读方便起见,我避免进入到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去。但是不应由此推断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过程的研究方法。这其中最显著和最全面地要数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这本著作出现的时候我正在联合公司奋力超额。在 1978 年写关于劳动过程,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写作的人必定会受到这部创造性地复兴马克思自己关于劳动过程的理论的著作的影响。如我在其他地方详述的那样,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透过对《劳动与垄断资本》中许多主要论点的反对而形成的。[^1]
篇幅的限制还带来了本书内容的一些其他约束。为了理论探讨更加深入,我决定牺牲一些我搜集到的丰富的民族志的数据,尽管那能使得解释更富生动性。同时被放弃的还有用来统计性地证明我做的一些结论的 14 个图表,主要在第八章——在那里我讨论了因 1974—1975 年的衰退而导致的劳动过程的一些变化。所有的这些图都可以在我的博士论文《车间里的超额》(“Making Out on the Shop Floor”)(芝加哥大学,1976)中找到。第三项省略是例行的方法论的附录,对于这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人类学家而言,参与者的观察即是全部——不同,他们认为这项必须加上。对于基于一定时间段的研究的特定问题(该研究中某个参与观察者的观察被与其他观察者的观察相比较)来说,可能做这样的一个附录显得更加有必要。在评估罗伊与我的观察的差异时,我所面临的一个特定问题在于:要将劳动过程中的真实变化与因我们俩的视角和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区分开来。由于我们在劳动过程中几乎处在同一个位置上,并且由于我们俩所记录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该位置的,所以我对于我所表达的变化是“真实的”变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的理论定位而产生的假象这点很有自信。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罗伊的对于产量限制的关注并没有限制他的视野及其对在一个机床工人之前所显现的整体状态描绘。为了帮助读者就比较的正确性做出自己的判断,我广泛援引了罗伊论文中的内容。
毫无疑问,有些人在扫过我通过单个案例所作出的结论时会开始皱眉了。有人会问:关于中西部一个相对不怎么重要的计件工作制的机械车间的研究,对于理解现代工业的基本生产技术——生产线、连续流技术、办公室工作等等,是否恰当呢?这样的怀疑论是那些沉溺于统计方法论的人经常提起的,他们从一个样本归纳到全体。但是对于理解部分之于整体的关系除了通过统计的外推方法外还有其他的途径。首先,存在一个将部分看作整体的一种表达的立场,也就是说,每一个部分都在其内部包含了整体的基本法则。通过对联合公司和吉尔公司的比较研究,我可以提炼出关于先进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的基本属性——例如,通过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建构同意。其次,有一个认为整体由相互依存的部分所组成的补充观念。通过理解联合公司与其他机构的关系,比如家庭、学校、政府、工会以及其他公司等等,我们可以开始构建整个社会的图像。这就是从部分扩展到整体的一般化方式。
至此,我主要的努力在于用个案研究来阐明和发展一个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对之进行提问的理论框架。如果我的结论可以唤起读者来否认它们的正确性,我将会因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感到满意。
田野工作者总是有数不清的恩惠要记,无数的礼要还。在当前的这个案例中要表达这些答谢多少有些困难,因为作为我以参与观察者的身份进行研究的条件之一,我不得不向联合公司的人员——从管理者到工人——保证,我将保持他们个人的匿名性,对于公司也同样如此。出于这个原因,我还要在引用关于联合公司的报纸和杂志时隐去所有的出版日期。
我首先要向我的工友们致谢。至少这个研究是关于他们在车间里的生活,而且其完成是依赖于他们愿意将我纳入他们的圈子中。尽管我经常解释为什么我在那,但他们是带着一种混合着怀疑和消遣的态度看待我的事业的。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有一种比在工厂里干一年活更好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学位。有些人则向我保证如果我能把我的论文出版了,并且在里面提到了他们,那它一定会是本畅销书。人们时不时地会走到我跟前,给我讲个有趣的故事并且说:“哎,把这个加到你的书里去。”他们的好脾气和愿意回答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使得我的任务变得愉快得多。尤其要感谢我的白班搭档比尔——他教会了我如何糊弄和超额。他容忍了我的笨拙并以他的荒诞感调和了工作生活中粗糙的一面。即使像莫里斯(卡车司机)、埃德(破坏工作速率者)和吉姆(工会主席)这些角色,尽管他们经常会惹火他们的工友,也仍是给车间里增添了些戏剧性。
我还要感谢工会的官员和管理层,他们给我提供了数据和采访(的机会)。人事部门在给我提供信息方面总是很帮忙。我还可以追踪到远在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和南加州这些地方的曾与老吉尔公司合作过的许多管理层官员。我很感谢他们给予我采访的机会。
在智识方面我欠下的情就广了。我对工作组织方面的兴趣最初是在赞比亚培养的,1968 到 1972 年间我在那里担负了不少关于铜矿产业的研究。在此期间,亚普·范维尔森(Jaap van Velsen)给了我一个深入的“曼彻斯特学派”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的教导深深地嵌入于我定位理论和研究的方式中,并且渗透于本书的分析中。我欠比尔·威尔逊(Bill Wilson)的情多得难以计数,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论文委员会的主席。从我进研究生院的头一年的开始,他就给予我坚定的精神上的支持,并对我所有的智识上的努力提供了建设性批评。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他对于他自己判断的信心,即认为我所做的事的确应被认为是社会学——在这点上他是与他的许多同事相对立的,那么这篇论文以及现在这本书都是永远不能写成的。我欠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的情则可以很简明地表述。他在 1973—1974 年所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研究课程不愧为一次振聋发聩的智识体验。它就像成年仪式那样的令人兴奋。比尔和亚当在论文的各个阶段都为指导论文投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查尔斯·比德韦尔(Charles Bidwell)、雷蒙·史密斯(Raymond Smith)、理查德·陶布(Richard Taub)和阿瑟·史汀区孔(Arthur Stinchcombe)等人也助益颇多,他们提出有益的质疑和批判性的评论,迫使我重新思考和表述这个研究中的许多部分。特别要提到唐纳德·罗伊,他热心的支持我回到吉尔公司。他对初稿的评论极其重要,确证了我对过去 30 年间所发生变化的阐述。要不是我特意计划了采取这样一个“重访”,我怀疑我能否找到一个更敏锐更有洞察力的田野工作者或者更丰富的关于车间生活的说明。
自从到了伯克利之后,我就被迫将我的研究定位偏移了少许。我曾想在社会学的地盘上建立与之竞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玛格丽特·赛如(Margaret Cerullo)和汤姆·朗(Tom Long)都一直说服我这一念头的危险性。于他们使我信服未经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是危险的,正如说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是不光彩的。他们的影响可以在书中的不少地方找到。作为与我共享乐趣以及我与之分享论文成果的朋友,埃里克·赖特和比尔·弗里德兰(Bill Friedland)对整个论文的鼓励和批评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评阅人,莫里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所做的要远超出责任的要求,他给了我 25 页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原初手稿相当程度上的重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他让我注意的很多弱点的回应。我要对在不同阶段给我评论和建议的人表示感谢,他们包括:若斯·德·阿兰卡(Jose de Alencar)、保罗·阿特威(Paul Attewell)、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戴维·布罗迪(David Brody)、米切尔·费恩(Mitchell Fein)、鲍勃·菲茨杰拉德(Bob Fitzgerald)、格雷琴·富兰克林(Gretchen Franklin)、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兰迪·马丁(Randy Martin)、林恩·派特勒(Lynne Pettler)、戴维·普洛克(David Plotke)和艾达·苏舍(Ida Susser)。我还要为奥利维娅·伊娜巴(Olivia Inaba)的专业的打字技巧以及挑出我手稿中的许多错误向她表示感谢。
在适应或抵抗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特征化的研究生生活的苦行过程中,我依靠了不少朋友在精神上和智识上的支持。我感谢他们所有的人,尤其是特伦斯·哈利迪(Terence Halliday)和凯瑟琳·施瓦兹曼(Kathleen Schwartzman)。
[^1]: 参见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的《生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