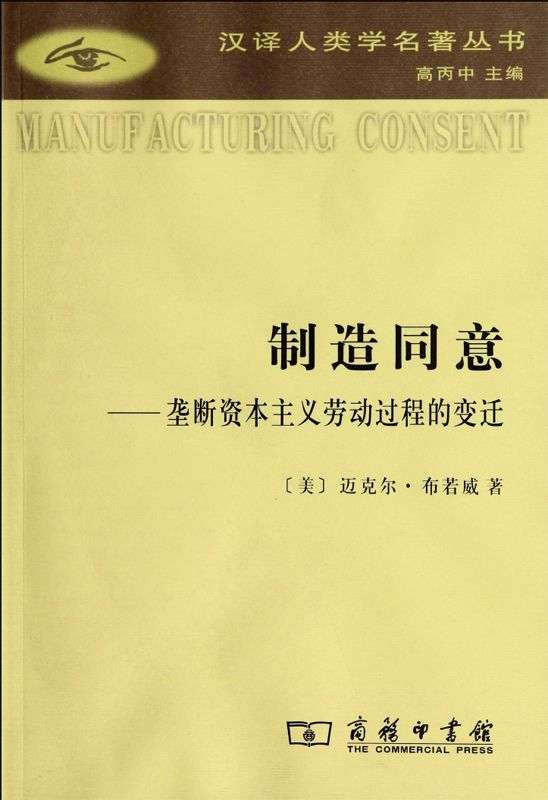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一章 工业社会学的衰退—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一章 工业社会学的衰退
要说明工业社会学的衰退,必须研究社会学的趋势以及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变迁之间的关系。1950 年代,“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说法的兴起使得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和其他人宣称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已经被克服了。剩下的事只是使现代社会更完美。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就中他们算上了产业工人的社团化和产业斗争的体制化。罢工已经“萎缩”了,并且那些仍在爆发的罢工也只是影响到劳动力的边缘部分——那些还没有被整合到更广泛社会的部分。[^1] 产业工人们已不再是革命的行动者而成为中产阶级的萌芽一族。进一步而言,工人们被描绘为“专制的”而不是激进的,是“资本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2] 一种欣悦之情突降到冷战时代的社会学家身上。尤其是蓝领工人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并因此退出了社会学的关注焦点之外。[^3]
将兴趣从产业劳动者身上转移到其他地方的现象,伴随着因认为其短视而对产业行为的早期研究所做的批评。这些评论经常以西部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关于“产量限制”的开创性研究为出发点。工厂社会学(Plant Sociology)——克拉克·克尔和劳埃德·费希尔(Lloyd Fisher)这样提到它——几乎不关注环境因素。它忽视技术的约束而过多地关注“人事关系”,忽略了对工作的外部定位,倾向于低估工人的经济理性。它忽略阶级斗争而只是呈现了管理的视角。[^4] 毫无疑问,各种批评都姗姗来迟,但也提供了重要的纠正。但是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在早期研究中深嵌有真理的事实,即使只是部分的真理。在本研究中,我试图通过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将这些部分真理主题化,从而来挽救工厂社会学的合理内核。这样,胜于强调将工厂与其环境隔离开的谬误,我将试图弄清楚其隔离或者相对自治——这种自治允许早期的研究者为理解产业组织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的精确本质。胜于争论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是地方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我将展示冲突与同意是如何在车间内组织起来的。胜于喋喋不休的谈论关于试图通过人事关系引出工人们更加合作这种观点的生捏硬造和无能为力,我将强调其本质的真理,即车间里的活动不能脱离生产组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来理解。认为工人在他们对工作的反应上有点非理性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同样地,认为工人会倒向经济理性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这个研究中我将展示理性如何是一种特定生产组织的产物并且是工厂“文化”的重要部分。简言之,胜于摒弃工业社会学的发现,我将把它们置于并且有时是把它们结合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从而超越它们。
组织理论的出现
新出现的研究取代了工厂社会学,研究焦点转变到了一般组织——医院、志愿协会、工会、政党等等——上。一般理论、概念图示和焦点问题是围绕着各种组织中的行为而构建的。文献著作中出现了三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首先,是对科层制——规则的功能和功能障碍——的研究。[^5] 这些研究是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科层制和效率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所触发的。其二,这一系列研究发展了一个从作为决策者的个体的视点来看待组织的行为主义者框架。[^6] 这些理论的心理学上的侧重点可以看做是源于人事关系的视角对产业工作的观察。最后,许多研究者开始发展用于理解组织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框架。其中一些集中在社会化、社团等对于产业行为的影响上,而另一些则详述组织对具有不同程度不确定性的环境的依赖。还有另外一些则开始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试图理解产业发展的条件。[^7]
无论它们的缺陷何在,我在下面要说得更多的是,所有的这些发展都代表了与早期研究的重要的分道扬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基于的那些问题,在本研究中一再出现。规则的重要性将是我对车间政治的阐述的中心,尽管他们的含义将被理解为支配而非效率。即使是最受压迫的工人也得做出重要的决定,这一事实是任何研究都不可回避的。然而,我要讨论的焦点是:工人的这些选择对于同意的产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个体或者微观层面上的这种“不确定性”与宏观层面上的更有限的变化之间的纽带。最后,我要讲清楚在市场和社会化进程方面,组织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且在附录中我将致力于这些问题在赞比亚的产业发展方面的情况。同在早期工业社会学的研究中一样,我将把组织理论带来的进展结合进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
随着工业社会学被纳入组织理论,逐利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特性消失了。同时,涵盖组织和社团所有形式的概念图示与理论的发展表达了一个非常真切的事实,即科层制模式和商品关系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渗透。然而,由于对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源未加思索,组织分析将这一事实投射到了一般理论中而遮蔽了资本主义尤其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特征,结果失去了其真实性。汤普森(Thompson)对于组织控制或者遏制其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的关注,反映了拥有资源用来从事缓冲、调整、预测、配给等等工作的大型公司或政府机构的兴起。如我在本研究的后面希望表明的那样,将汤普森的洞见复原到其所属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中,会使得发生于当代社会的变化清楚得多地显现出来。同样,对于诸如向西部电气公司这样的研究的批评经常是基于对不同时期组织的观察而做出的,而缺乏对于历史语境(这一语境是研究本身不予强调的)变迁的恰当考虑。今天的银行配电间难道看起来还会与 1932 年的一样吗?人们的观察会有何不同,而我们又要如何解释它?这些是一个对于历史变化敏感的理论应当提出的问题。
当然也有解释组织变迁的尝试,但关键在于这些尝试有着非历史的本质。通过建构发展的自然法则——不可避免的理性化进程、科层化、对于效率的追求,诸如此类等等——关于变化的描述被提升到一个似是而非的关于变化的解释。[^8] 而其他人则以不那么宏大的视野,用购物清单式的经验主义取代了对发展的解释。[^9] 在试图解释的地方,他们也倾向于在除了发生转型的时刻外都保持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隔离。这些是组织持续性的理论,它们强调效率、传统化力量、既定的利益、缺乏竞争等等。[^10] 但是组织并不仅是简单的“持续”而已。像任何其他持久的社会关系模式一样,他们必须被持续生产——也就是可再生。虽然资本主义企业的独特特征之一是其显而易见的可再生产其自身关系的能力,但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自治也仅仅 是表面上的(相对的)。组织持续的理论将持续的条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忽略了关系的再生产侵蚀这些条件的趋向。
一旦再生产的问题被提出,人们就必须超越组织,并考察保证其再生产的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这包括了:首先,考察不同的组织生产什么;其次,承认他们不仅仅生产有用的物品或“服务”,并且也直接的或间接的生产利润。它包含了构建代表资本主义或者先进资本主义的实在整体——事实上,是关于先进资本主义的理论构建。它不仅会超越组织理论,它还将否认后者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存在的权利。它要将组织理论无时间性的归纳放回其特定历史语境中去。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它还将揭去表象,连接部分与整体、过去与未来,从而粉碎当前事物次序中被视为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表象。
组织理论的悖论
在对其一般及抽象概念的发展中,组织理论丢掉了特定的和具体的组织产物。它以形式理性取代了实质理性,并且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一方面将天然的或原材料转变成有用之物,另一方面将其变成利润——轻描淡写。透过详述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以及排斥具体的行动、实践、干活做事,组织理论非历史性的说明得到了维护。而恰恰是由于这幅片面的图景,一个根本的矛盾显现了出来。这些研究不论早期或晚期的,都依赖于两个彼此分歧的前提之一,或者二者的某种结合,即对潜在和谐的预设 以及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把它们放在一起的话,这两个前提就显得彼此对立了;因为如果社会具备潜在的和谐,并且一致同意不成问题的话,那为什么社会控制是重要或必要的?反过来,如果社会控制如此重要,那我们又如何能将一致同意视为既定的?
这一矛盾一直是潜藏的,部分是因为这两个主题一般是被取材自不同的社会学传统——一方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另一方是马克斯·韦伯——的作者们分别发展的。这样,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预设是相分离的。此外,这两个传统中的作者们并不总是深入反思其各自立场的意涵。这样,在社会控制成为焦点的地方,并没有发展出关于冲突的理论以此来确立社会控制的必要性。而当重点是和谐时,和谐则是被预设的而不见解释,并且冲突被看做是病态的,甚至是偶发的。我将对每个主题依次探讨。
阿诺德·坦纳鲍姆(Arnold Tannenbaum)阐述了社会控制文献中的预设:
组织意味着控制。社会组织是对人类个体互动的有序安排。控制过程有助于限定特异行为,并使他们服从组织的理性计划。组织需要一定的服从也需要对多样行为的整合。正是控制的功能使得服从达到组织的要求,并实现组织的终极目标。控制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分歧的利益和成员潜在的弥散行为中创造出协调与秩序。[^11]
但这些“特异的”行为,“多样的”利益等究竟是什么,以至于要被控制呢?当一个人研究组织中的控制时,可以不去探讨究竟什么要被控制吗?坦纳鲍姆设法通过这种类型的一般性问题来解决:“一般而言,你们那里经理对于他下面的团队做什么有多大决定权或影响力?”[^12] 这样,既没有提及被控制的行为,也没有提及用以行使控制的资源,更未提及控制所指向的“偏差”趋势,坦纳鲍姆就能够根据组织中的控制总量及其分布对它们进行刻画。这个纯粹从形式角度来测度控制的模式(事实上他测量了一点控制吗?)使得他可以比较非常不同的组织类型,并建构“控制”的类型学。然而,关于“控制”是什么——为什么控制会被置于首要地位,以及至少是部分的、在其功能的方面它必须被理解的可能性——完全从视野里消失了。
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的综合论述的确认识到了社会控制背后的驱动力是不能被忽视的。[^13] 埃齐奥尼立足于组织理论中的韦伯传统并创造了类型学,该类型学基于集结权力(资源)以达成服从(顺从)的类型以及参与者“涉入”的类型。尽管埃齐奥尼承认冲突在组织中是地方性的,但他却没能提出冲突的特定模式的基础或其来源。虽然他确实在界定参与者的不同倾向方面取得的进展超越了韦伯,但是他没能给出可以说明这些倾向或者解释它们怎么产生冲突的理论。充其量他提供了专门假设,而这些假设在发展更一般的解释的压力下倾向于丢弃历史的特殊性。
在另一个传统中,假定了在产业组织的成员间存在一种潜在的和谐,而关注的焦点是冲突真切地出现。那些关心效率和生产力的人经常将冲突的缘由定位为工人们遵守“低层的社会规则”以及他们无从理解管理的“经济逻辑”。[^14] 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同样的观察数据则意味着一种阶级意识的萌芽形式。
其他人提出冲突滋生于工人们与组织间整合不足。新的管理模式,包括雇员自我监管和赋予工作团体更多的责任,被提议以重新整合个体与组织。[^15] 另一些观点则将其归结于缺乏与产业工作机构的合作,并且建议小幅改组生产组织。“工作扩大”、“工作丰富化”、“工作轮换”等等,是管理顾问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较少关注社会工程学的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曾试图建立“异化”程度与“技术”的类型之间的曲线关系,他提出自动化将宣告一个更少压迫的劳动体制。[^16] 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所倡导的社会技术系统研究方法强调,技术系统与社会系统间缺乏协调是无效率和冲突的根源。[^17]
有关“产量限制”的著作中,工人们被描绘成逃避工作的人。与此观点相对立的许多研究则指出,管理方应对将劳力转化为产量的过程中的失误负责。换句话说,“产量限制”的责任要由管理者承担。[^18] 一种相关的分析则将冲突归结于生产过程或者环境的不确定性。^19 像上面所有的案例中一样,在此,它暗示着冲突的根源在理论上是可以被消除的。也就是说,冲突不是固有的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反映了人、技术或环境上的非理性,而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特性。
最后,必须要提及的是那些虽然坚持利益的潜在和谐的预设,但仍将冲突看做是产业组织的普遍现象的观点。产业关系的“单一”框架被“多元”框架所取代,后者将车间想构想为一个许多竞争群体的竞技场。[^20] 工厂的多元主义是政治领域多元主义的同属成员,其中,群体通过一个共享的规范与准则框架而角逐各种“价值”。的确,我将这些研究强塞进“和谐”或“社会控制”的视角模子内对它们是有些不公平,毫无疑问,它们中的许多结合了两个视角的特征。但是没有哪个解决了这个矛盾,因为它们都遗漏了劳动过程中特定的资本主义维度——而正是这些特性提供了我研究的焦点。
悖论的一种错误解答
有必要探讨一种当前颇有点流行的悖论解决方式。它来自于有时被称为“冲突”的视角。该视角假定了一种潜在的、常存的并且是结构性的冲突,所以为了使和谐成为一种普遍状态,社会控制必须也是无所不在的,并且是有系统的。此外,冲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某种非理性,而是意味着某种社会控制的失效或不充分。我将以威廉·巴尔达穆斯(William Baldamus)的重要研究作为这种相当松散的思想学派的代表,他视“产业生产的整个体系……为一个调节人们劳力的数量、质量与分布的行政控制系统”。[^21]
我们将假定,从一开始雇员 - 雇主的关系就呈现为一种反映了优势与劣势不均等分布的分化的权力结构。从而重点将落在冲突和组织解体的原因上。较之到目前为止可能有的解释,这种观点具有获得对相关观察更加连贯的解释的优势。但是也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一旦不再采纳关于和谐的与自我调节的系统的假设,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庞大复杂的产业行政的丛林,而它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体系可言。如果冲突是基本的且不可避免的,我们又如何解释在没有罢工、没有不平、没有不满的情形下,雇员 - 雇主关系明显的稳定呢?换句话说,现在必须要解释的就是平常工作及常规行为的运作。[^22]
然而巴尔达穆斯从未连贯地阐释过这一框架,就像其他社会控制的著述一样,他依然未对潜在冲突模式做出系统的分析,未对“反映了优势与劣势不均等分布的分化的权力结构”做出系统的分析。
巴尔达穆斯成功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因为他提出车间里日复一日的劳动支出是由付出与回报之间的标准化关系所支配的。比起他把标准的来源(“公平的一日工作”的内涵)置于工厂之外的社会化进程中,巴尔达穆斯未能对标准而非常态的存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是那么显著。[^23] 如此一来,勤勉的付出就与假定的潜在冲突相脱离,而冲突接下来又在巴尔达穆斯的框架中变得无关紧要。回报与付出之间的标准化关系以及潜在的冲突本来应当是必须被解释的,现在却被视作已知事物了。为什么在一开始回报应该基于付出?为什么当资本主义在其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叫嚣着反驳这一法则的合法性的同时,工人们却仿佛将其作为掌控他们一生的法则呢?这些问题是认为资本主义理所当然的框架所不能提出的,更不要说回答了。
结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他们强调社会控制的情况下,他们充其量只是趋向于引入一些类型学而丢掉了其历史根源。此外,就算这些理论承认某种潜在冲突的存在,他们也未能界定其形式和起源。另一方面,和谐理论如我们所见,难以解释冲突的爆发以及惩罚性或强迫性控制的经验性存在。工业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从一致同意或社会控制的事实出发,却没有解释这些事实。因此有必要打破产业社会学和组织理论中超越历史的一般性与片面性视角,并摒弃关于潜在冲突或和谐的形而上学假设。冲突和同意既不是潜藏的也不是隐含的,而是直接指向可观察的行为,而此行为必须透过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过程的组织来洞悉。冲突和同意不是原生条件,而是特定的工作组织的产物。我们必须避免陷入到“一致论”和“冲突论”之间的种种争辩中,而要把讨论转移到完全不同的领地。为此,我们必须修复讨论的历史语境。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将是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区别于前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
[^1]: 阿瑟·罗斯(Arthur Ross)和保罗·哈特曼(Paul Hartman),《工业冲突的变化模式》(Changing Patterns of Industrial Conflict, New York: John Wiley, 1960);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和亚伯拉罕·塞格(Abraham Siegal),“产业间的罢工倾向——一个国际比较”(“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收录于《工业冲突》(Industrial Conflict),阿瑟·科恩豪泽(Arthur Kornhauser)、罗伯特·迪宾(Robert Dubin)和阿瑟·M. 罗斯(Arthur M. Ross)编(New York: McGraw-Hill, 1954)。
[^2]: 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政治人》(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59)第四章;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第十章。
[^3]: 1970 年代对蓝领工人的兴趣有某种程度的复苏。例如,参见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和乔纳森·科布(Jonathan Cobb)的《隐藏的阶级伤痕》(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哈罗德·谢泼德(Harold Sheppard)和尼尔·赫里克(Neal Herrick)的《所有的机器人都去哪儿了?》(Where Have all Robots Gon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以及威廉·科恩布卢姆(William Kornblum)的《蓝领社区》(Blue Collar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4]: 例如,参见利昂·鲍里茨(Leon Baritz)的《权力的奴仆:美国工业中社会科学被使用的历史》(The Servants of Power: A History of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Industry, New York: John Wiley, 1965);亚历克斯·凯里(Alex Carey)的“霍索恩研究:一个激进的批判”(“The Hawthorne Study: A Radical Critic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 [1967]: 403—416);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等的《富裕的工人:工业态度与行为》(The Affluent Worker: Industr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克拉克·克尔和劳埃德·费希尔(Lloyd Fisher)的“工厂社会学:精英与土著”(“Plant Sociology: The Elite and The Aborigines”),收录于《社会科学的共同边界》(Common Frontiers of Social Sciences),米拉·科马尔科夫斯基(Mirra Komarovsky)编(Glencoe: Free Press, 1957);亨利·兰兹伯格(Henry Landsberger)的《重访霍索恩》(Hawthorne Revisited,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的“效率与拉拢:一个计件机械厂的非正式群体间关系”(“Efficiency and the Fix: Informal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a Piecework Machine Sho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 [1954]: 255—266);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的“工作场所的人际关系:对近来研究的评价”(“Human Relations in The Working Place: An Appraisal of Some Recent Research”),收录于《产业人际关系研究》(Research in Industrial Human Relations),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编(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第 25—59 页。
[^5]: 例如,参见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第八章;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的《工业科层制的模式》(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彼得·布劳(Peter Blau)的《科层制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以及最近的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的《科层现象》(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6]: 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组织》(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1958)是这种方法的典型。
[^7]: 例如,参见戈德索普等的《富裕的工人》;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的《行动中的组织》(Organizations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以及克拉克·克尔等的《工业主义与工业的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此外,当然还有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的经典之作《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工业化过程中的管理意识形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Ideologies of Management in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56)。
[^8]: 这些研究中的许多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s)的严重影响。例如,参见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法律、社会与工业正义》(Law, Society, and Industrial Justi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
[^9]: 例如,莫里斯·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汇编了在 50 年期间促使军事上的变化的一系列因素,但是从未想到把握解释那些变化的问题。他在某种形式的技术决定论和主张下列本质之间犹豫不决:“对于同等对待的普遍要求随着工业化而增长。在生活水准提高的同时,对于军事生活的不适的忍受降低了。城市生活的怀疑论延续到军事中比起以前的世代达到了更强烈的程度,因而人们不会再盲目的行动了,而是从他们的指挥官那里要求某种解释。”《职业军人》(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60),第 40 页。
[^10]: 阿瑟·史汀区孔(Arthur Stinchcombe),“社会结构与组织”(“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收录于《组织手册》(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詹姆斯·马奇编(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异化与自由》(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11]: 阿诺德·坦纳鲍姆(Arnold Tannenbaum),《组织中的控制》(Control in Orgniz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第 3 页。
[^12]: 同前书,第 46 页。
[^13]: 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复杂组织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plex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14]: 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工业文明的人的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3),第 116 页。
[^15]: 伦西斯·利克特(Rensis Likert),《管理的新范式》(New Patterns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克里斯·阿吉里斯(Chris Argyris),《整合个体与组织》(Integrating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rganiz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16]: 布劳纳,《异化与自由》。不过也请参考西奥·尼科尔斯(Theo Nichols)和休·贝农(Huw Beynon)的《活在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与现代工厂》(Living with Capitalism: Class Relations and the Modern Fac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该书有力地驳斥了布劳纳的文章。
[^17]: 例如,参见 E. L. 特里斯特(E. L. Trist),G. W. 希金(G. W. Higgin),H. 默里(H. Murray)与 A. B. 波洛克(A. B. Pollock)的《组织的选择》(Organizational Choice, London: Tavistock Institue of Human Relations, 1963)。
[^18]: 罗伊,“效率与拉拢”,汤姆·勒普顿(Tom Lupton),《在车间》(On the Shop Floor,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3),都有力地指出了同样的观点,尽管他们并非来自于相容的理论视角。
[^20]: 例如,参见艾伦·福克斯(Alan Fox)的《超越合同:工作、权力与信任关系》(Beyond Contract: Work, Power, and Trust Relations, London: Faber & Faber, 1974);但是也请看克拉克·克尔的《工业社会中的劳工与资方》(Labo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21]: 威廉·巴尔达穆斯(William Baldamus),《效率与努力》(Efficiency and Effort, London: Tavistoc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1961),第 1 页。
[^22]: 同前书,第 8 页。
[^23]: 同前书,第八章。也请参考希尔达·贝雷德(Hilda Behrend)的“公平的一天的工作”(“A Fair Day’s Work”),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961): 10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