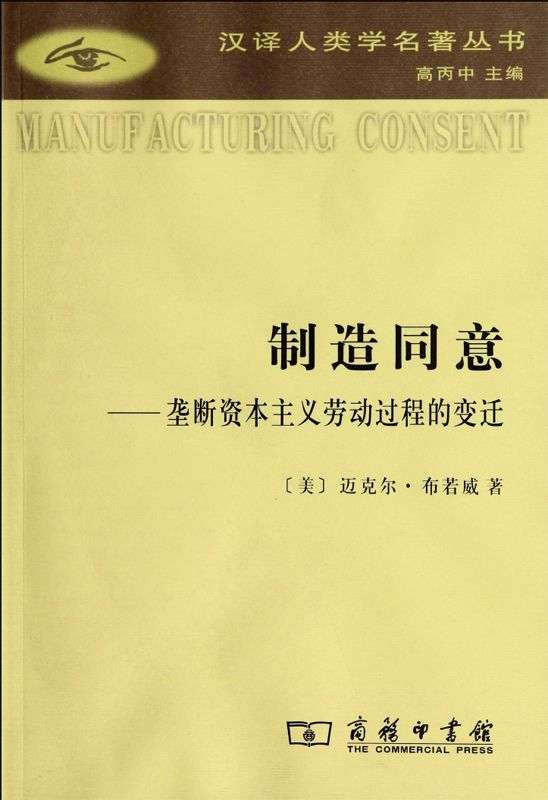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二章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二章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社会学的政治内涵源于对特定历史哲学的吸纳,该历史哲学认为未来是对现在的完美化,而现在是过去的必然发展顶点。其他社会学论述皆循此而来。通过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经验形塑为普遍经验,社会学对于构想未来有一种类型上截然不同的社会无能为力,历史被赋予了一种目的论,其实现即为现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被铆在了现在。存在的就是自然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为了构想和预期一些“新”东西,必须从不同的预设出发,即认为历史是不连续的,并且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差异只有在彼此间的联系中才能把握。比较的基础——一套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性概念——是必要的。但是,它们的适用性必须取决于它们的“独特性”。为了发展关于特定社会的理论,一般性概念可以具体化。没有一般性理论,只有一般性概念 和特定理论。历史并不作为“事实”的接续,也不作为现在的目的论的显现;更确切地说,历史是由特定社会的不连续的更替所组成。在历史作为某个既定社会的变迁发展与历史作为从一种社会转变到另一种社会的过程之间存在着区别,前者仅是关于该社会的一种理论。只有这种双重的历史概念才能理解未来与现在不一样,而不至于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之中。[^1]
在这一章中我将介绍一些一般概念——生产模式、生产关系、劳动过程、生产中的关系、再生产、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等等——然后将简要说明如何将其特殊化,从而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不同的社会。我将概要介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以便掌握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殊性。
前提和概念
我们必须从起点开始:
一切人类生存的首要前提,因而也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即人必须处于某个位置生存从而才能够“创造历史”。然而,生存首先需要饮食、居所、衣物和许多别的东西。因此第一件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的生产,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2]
为了创造历史,男女必须生存,并且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将自然转变为有用之物。这些活动我们称之为经济活动。在男女改变自然的过程中,他们进入了彼此的社会关系中,此时社会就形成了。如此被生产和再生产的特定关系界定了经济活动的性质,即生产样式或生产模式。历史是由不同的生产模式——也就是说,男女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进入的不同社会关系的模式——构成的。换句话说,历史被划分为占有支配性地位的生产模式的更替。
阶级社会中一套清晰的社会关系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人与依靠其他人的生产过活的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剩余者与剥夺剩余者之间的关系,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透过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的不同形式可以区分不同的阶级社会,也就是透过生产关系 来彼此区分。
生产关系并不只是界定了如何分配与占有劳动时间及其产品的特定方式的一组关系。它还是一种占用自然或者生产有用之物的特定样式。[^3] 从而,生产关系总是与一组相应的关系相结合,后者是男人与女人在对抗自然,将原材料改造成他们想象之物时进入的关系。这就是劳动过程。它有两个分析上有别但具体上不可分的方面——一个是关系方面,一个是实践方面。^4 我将劳动过程的关系方面称为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或生产关系(production relations)。举例来说,他们是车间里工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或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其实践方面,劳动过程是一套借助生产工具将原材料转变为制成品或者半制成品的活动。这包括劳动者、劳力的付出、将工作能力转化为实际工作、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正是在这种实践的活动中人类展示了其创造潜能,而关系方面则表达了自由合作的生产者组成族群共同体的潜质。生产关系塑造了劳动过程的形式和发展,而劳动过程反过来为生产模式的转型设定了限度。
剥削剩余劳动的特定模式,界定了如果该生产模式要持续就必须满足的一系列条件,即如果其生产特有的社会关系要被再生产 就必须满足的一系列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既定生产模式存在的条件,必须有保证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一整套机制。由定义可知,这些机制是政治 结构。政治活动关系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或变革)。^5 因而,一种特定的生产模式界定了一种相应的政治模式:
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抽走无报酬的剩余劳动的特殊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因为它从生产本身直接成长出来,并且又反过来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作用于生产。然而,正是在此之上建立了从生产关系本身成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整个构成,从而也同时建立了其特殊的政治形式。总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与直接劳动者的直接关系——一种与劳动方式从而也是社会生产力的确定发展阶段天然地相对应的关系——揭示了最隐蔽的秘密,揭示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隐秘基础,以及统治与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简言之,相应的特殊国家形式。[^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来决定的”;也就是我们可以说社会结构作为一个整体,要在经济活动的存在条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方面来理解。当我们致力于生产的特定模式时,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如何具体运作的。
事物的生产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同时也是这些关系的经验 的生产。当男女在从事生产时,他们创造了一个表象的世界,“……不是他们与他们的存在条件之间的关系,而是他们在这种关系中生活的方式:这既预示着一种真实的关系又预示着一种“想象的”、“生活的”关系。”[^7] 于是,在讨论商品拜物教时,马克思写道,“人们之间明确的社会关系却在他们的眼中呈现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8 也就是说,在一个商品生产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本质是只通过市场来表达的,在那里,“彼此隔离的”生产者或生产者集团交换他们的货品。正是在那里他们发现货物的价值是由其所包含的劳动来决定的。他们的货物所能交换的东西是由别人的生产中所包含的劳动决定的,这是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的。也就是说,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品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社会本质被烙印于物品之上,而这些物品如同异己力量施加在生产者身上。这种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以及一体两面的物品的人格化)作为一种生活经验使自身与生产它的条件相脱离;从而呈现出一种自主性,并表现为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
生产关系的结构与这些关系的生活经验之间存有无法分割的联系,关于它的知识(理论、科学等)再怎么多也不会改变这些经验,正如再多的科学也不会影响太阳看起来围着地球运转或者棍子被放进水中时看起来是弯曲的这样的事实。“近来的发现,即劳动产品就其价值而言,无非是人类花费在生产中的劳动的物质表现……决不会驱散劳动的社会性质在我们看起来是产品自身的客观性质这样的迷雾。”[^9] 生活经验将社会产物呈现为“自然”产物,且超出人们的控制。它不受知识或个体所持有的意识的影响的。占有生产位置的无论是卡尔·马克思、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还是乔·希尔(Joe Hill)都无关紧要,商品拜物教对他们而言都是同等真实的。
这个表象的世界与意识形态 的关系是什么呢?在马克思主义的著述中,意识形态的自主与生活经验之间有一种张力,一种在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的张力。[^10] 很清楚,这种关系是被历史地决定的,但是在此我倾向于强调生活经验及其加诸于意识形态之上的限制。因此,意识形态不是被社会化机构——学校、家庭、教会等等——依照统治阶级的利益任意捏造的东西。恰恰相反,这些机构阐释和系统化生活经验,并且只是在这种方式下才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中心。[^11] 此外,统治阶级被意识形态所塑造多过他们塑造意识形态。就他们热衷于欺骗的程度而言,他们所传播的仅仅是宣传而不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最初的逼近,是生活经验产生了意识形态而不是反过来。意识形态植根于使之出现的行为并表达了该行为。正如阿尔都塞引用帕斯卡尔(Pascal)的话写道:“跪下,活动双唇来祈祷,你就会相信。”[^12]
人们的头脑中并不会装着意识形态。而是有意识地承载着理论、知识和态度。这些变成了意识形态,“一旦掌握了大多数,它就成了物质力量。”[^13] 意识形态既不是“冰冷的乌托邦”,也不是“学来的理论化”,而是一种“具体幻想的创建,它作用于被分离和打散的人们,使之觉醒并组织其集体的意志”。[^14] 意识形态担当了社会关系的黏合剂;它使个体彼此结合;它使当下的经验彼此相连,也使之与过去的、未来的经验相连。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理论,就能够 在特定时期或者工人阶级的特定部分中间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政治力量。它也许 更可能在工作场所以外的政治活动中而不是在工作场所中掌握群众,虽然后者在传统上被认为“最有意义”。在危机或斗争时期,当生活经验的“天然性”被动摇的时候,诸多理论会形成为一股政治力量。然而很清楚,在学校教授理论同生产意识形态并不一样。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的官方“思想”并不必然影响人们工作中的行为。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何在?在何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物质力量?由于意识形态表达了人们体验关系的方式,所以通过意识形态“人们意识到……矛盾,并通过斗争来解决它”。[^15] 尤金·杰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展示了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斗争是如何被家长制——在不承认奴隶有别于物体的生产模式的语境中,一种表达了奴隶的“人性”的意识形态——所形塑的。[^16] 当奴隶反对奴隶制时,他们依照宗教意识形态的形式或拥护或抵制家长制。在杰诺维斯看来,宗教在南方奴隶对于家长制的迁就以及其他地方对其反抗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斗争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时,斗争的后果必须通过细查意识形态背后的真实关系来理解。举一个相对清晰的例子,南非阶级之间的斗争发生在种族主义领域,但是其结果只有通过分析那种既形塑种族主义又被种族主义弄得模糊不清的关系的再生产才能把握。
但是,如果这些斗争不是关于利益 实现的斗争,那它们又是什么呢?并且利益从何而来?从目前为止所说的来看,他们显然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不过,这不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许多社会学观点将利益当做既定的。正是在这里我们遭遇到了从实际与假设行为之间的差异中滋生出的下述问题,即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非逻辑行为、利益的实与虚、短期与长期、直接的和根本的等问题。在利益被作为既定的地方,意识形态就变成了人们可操纵它来提升他们的“利益”的资源,或是抑制冲突、使紧张最小化的黏合剂。[^17] 另一方面,当利益不是给定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事后被以一种同义反复的方式经验性地发现或构建出来。某个特定集团之所以会如此投票是因为其利益是如此这般。为什么其利益是如此这般?因为他们是这么投票的。但是为什么,比如说,工人们有时为其种族利益而斗争有时又为其阶级利益而斗争?问题在于要去解释任何既定情形下的利益,而不是经验性的描述它们。胜于形而上地或者经验主义地假定利益,我们必须发展一种利益的理论,一种关于它们如何从意识形态之中建立的理论。
显而易见,利益如同我们定义它们的那样,不能在对社会关系的特定自发意识之外,也就是在这些关系自身的理论之外来理解。在商品生产社会的角逐中,利益在于物质受益、在于量而不是质,这作为特定生产形式的后果,在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拜物教”得到了深刻的刻画。这同理性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将个体经济行为的理性视为更广泛的社会理性的一个方面,后者基于不同社会形态中经济和非经济结构间的内部关系……然后可以理解,如果没有关于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科学知识,经济学家将无法得到个体偏好的统计数据之外的任何知识,而个人偏好在他看起来只是品位问题,理性问题并不会由此提出。[^18]
但是,如果利益完全系于一个既定社会,并且是该社会与生俱来的,那我们如何讨论超越该社会的斗争呢?我们如何想象一个具有“理性”的社会,一个历史在其中被自觉地、集体地而非无意的制造出来的社会,一个表象与现实之间、经验与表象的客体之间没有差异的社会——简言之,一个没有意识形态,从而也没有“利益”的社会呢?的确,正如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利益的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场,个体在其中变成了超乎他们控制的动机的奴隶。利益的概念传达出对需求已经堕落为贪欲。赫勒不谈“基本利益”(fundamental interests)或“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s),她说的是“根本需求”(radical needs)。“阶级利益”不可能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动机:真正的动机,要从拜物中解脱出来,被工人阶级的“根本需求”所代表。[^19] 但是资本主义容许这种根本需求吗?它是否像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资本主义产生它们来作为自身发展的条件呢?如果这样,那又是如何这样做、在哪里这样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呢?并且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种根本需求可以在新社会中实现?什么样的环境可以成为将潜在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基础?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发展了一些一般性概念后,我们现在可以将其特殊化,并用以阐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了。但为了突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性质,并建立起独特性,有必要将其与一个非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相比较。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比较方式呢?为了同时进行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与社会主义作比较似乎相当吸引人。不过,没什么迹象说明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过程是那么的不同,从而这一比较几乎不能澄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质。另一种方式是,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理想类型;但是这种理想化通常是透过倒置资本主义的部分特性,从而预设一种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理解来建构的。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相对比则是比较适当的。对资本主义和所有 基于“超经济”(extraeconomic)元素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做出比较是可能的——“超经济”元素在后者中对于占有剩余劳动是必要的,而在前者则不存在。但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变体如此之多并且它们间的共同点又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这种比较可预期的收效十分有限。因此我要选择一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主义——关于它的文章已经被写了许许多多,并且它是作为一种未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历史形式而存在。
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封建主义本质的争论有很多,通常是与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相联系的。[^20] 不过在这里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封建主义自身的本质或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我们用它只是作为与资本主义的对照。因此,没必要涉及下述争议:封建社会动力的本质、封建主义的解体、阶级斗争在其解体以及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的角色、城镇与农村的关系、市场在上述所有中的角色等等。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对封建主义的概念化将致力于突出其劳动过程的形式。此外,我们的概念化并不对应历史上任何具体的封建主义,因为那样将呈现出比我将要提供的更复杂和斑驳的图景。事实上,我将把自己限定在关于封建主义的一种特定形式——亚伊勒斯·班纳吉(Jairus Banaji)指称的纯粹的、经典的或者明确的,即以劳动服务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讨论中。[^21] 最终,其价值的证据依赖于它能否揭示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确定特征是以租金的形式占有剩余劳动。农奴为了在他们按照领主的意愿而持有的土地上维持生计,被迫以实物、金钱或劳动服务,或者更为普遍的某种组合的形式来缴纳租子。在此我的讨论将限定在农奴在其领主的土地上——领主的领地——履行的劳务形式。于是,生产周期最简单的形式如下所述:农奴每周在地主的领地上劳作若干天,而在剩下的日子里他们就是为了生存而耕作他们“自己的”土地。前者是固定和剩余劳动,后者是必要劳动。
这种封建主义的纯粹形式有五个特性是要着重强调的。首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分开的。农奴在领地上劳作以“交换”对一小块或一小条土地耕种的权利,获得对共有土地的使用权等等。其次,农奴对于他们留存的收入是直接拥有的,也就是说,他们消费他们自己种植的谷物。第三,农奴能够独立于领主而自行使用生产工具。固然,他们在犁地、收割等等,尤其是在轮作制的开放土地系统中是合作的,但是他们拥有自己的工具并且可以不受领主干涉的使用它们。[^22] 第四,尽管农奴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组织劳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地主的,但他们在领地上的生产是由领主的代理人——管家或土地管理人——来监督和协调的。实际的工作义务是在庄园习惯法中详细记载的,并在由领主代表的庄园的法庭中强制执行。[^23] 也就是说,构成剩余劳动的那些生产活动,被政治 - 法律的制度所制定和确保。最后,地主将农奴排除在他们为自身使用而耕种的土地之外的权力,被国家的地区性机关所保护的权力,使得劳动服务不可逃避。同时,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和军事保护使剥削体制呈现为自然的和必然的。
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模式下,剩余劳动是透明的。它既不是自动产生的也不是与自留生产同时产生的。更准确地,农奴可以独立于为地主的工作而生产其生存手段,因而剩余劳动必须通过超经济手段来榨取。简言之,由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相分离,所以剩余劳动的占有是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纠结在一起的。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吗?直接生产者是花一些时间为资本家生产又花一些时间为他们自己吗?工人们是占有自身行为的产物来维持生计吗?工人们能独立于资本家而自行开动生产工具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依赖于生产周期中的超经济手段吗?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
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不能靠自己改造自然以及自主地提供自己生计所需。他们是被剥夺了对自己的生产手段——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使用权的。为了生存他们别无他法只有出卖自己劳动的能力——他们的劳动力——给资本家以换回工资,然后他们再将工资变为生存手段。在为资本家的工作中,他们将自己的劳动力转变为劳动;他们的工资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在工作的整段时间的补偿。事实上他们只是被付给与他们在工作日的一部分时间——比方说 8 小时中的 5 个小时——内所生产的价值相等价的货币款项。这 5 个小时组成了必要劳动(对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必要的),而剩下的 3 小时则组成了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正如工人们为了工资而出卖其劳动力是依赖于市场的,资本家在出卖其商品时也是依赖于市场的。剩余劳动不仅生产有用之物而且生产可以被买和卖的商品,也就是具有交换价值之物。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 的形式,作为市场上的利润而被实现。
有五点与封建主义的对比是应当被强调的。首先,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没有分开。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过程的理论正是基于此——在现象层次上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劳动的整个产品是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在通常的时候只有通过其效果才能体验必要和剩余劳动:工人们每天出现在工厂大门和办公室门口,以及另外一面,敞开工厂和办公室大门、替换报废机器、付给工资并且在市场上实现利润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持续存在。只有在危机情形下资本主义的运转才可能暴露出来,并且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呈现为自身的无中介力量的存在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们不能依靠他们在车间里生产的东西生活。农奴可以靠土地生活,但是劳工不能靠销钉过活,更别提钉帽了。劳工们获得生存手段的唯一途径(当然,除了靠可怜的救济、失业补偿等以外)就是通过市场——通过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以换回工资,而工资又被转换为消费品。同样,资本家如果想继续当资本家,就要依靠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并购入劳动力及其他必需品。市场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 特性,生产的所有行动者都依赖于它,这使得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区别开来。尽管市场绝非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但它并不是封建主义必需的。
第三,工人们既不拥有生产工具,他们也不能自主使用。他们是通过对资本的代理人——指挥劳动过程的经理——的臣服从而是从属于而不是掌握劳动过程的。同时,也是第四点,这种对劳动过程的指挥与领主的代理人在领地的生产中的行使的监督和协调是非常不同的。在封建主义下,生产性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劳动过程以外于庄园的法庭里定下来的。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协调的功能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是分离的。在资本主义下,直接生产者缴纳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服务。这里并没有对生产性活动的预先的规范;管理的目的是企图从工人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也就是说,管理不是像在领地上的生产那样只为了协调而存在,他也是为了控制。控制和协调的功能在封建主义是分离的,而在资本主义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24 相应地,关于生产活动的斗争发生在车间里,而关于劳动服务的斗争则发生在劳动过程以外的庄园法庭的政治 - 法律领域内。[^25]
最后,正如超经济元素塑造了封建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支出而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则并非如此,同样的比较也可以延续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来。领主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领主可以将农奴排除在土地之外的这种被政治和法律制度所定义和确保的权力来保证的,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他们在经济上的 相互依赖性的。在资本主义中,商品生产一方面是劳动者的生产(通过必要劳动——工资的等价物),同时,另一方面也是资本家的生产(通过剩余劳动及其以利润形式的实现);也就是说,商品的生产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然而在封建主义中,为领主而进行的生产与为农奴自己而进行的生产是通过政治和法律机制来连接的。
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及意识形态的体制保证了生产的外部条件。与此相反,封建主义下的这些体制是直接介入了生产周期中,以保证其连续性并决定其内容,也就是说,再生产生产关系和生产中的关系。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体制依据身份来辨识——佃农、农场雇工、小地主、城镇官员、领主等等这些生产的代理人——然而,在资本主义中,这些体制使工人、资本家、经理等的生产性身份神秘化了。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机构将生产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了公民、性别、种族等之间的关系。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具有一种与封建主义不同的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所以可以呈现出多种形态——独裁专制、法西斯主义、议会民主、种族隔离等等。即便是这样一个粗略的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考察,也显示出某种生产模式的存在(再生产)条件,是如何塑造一套相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
通过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模式的一个特定理想化变体相比较,从而确立了它的某些独特的特征后,我们可以更近地聚焦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般特性上。工人是被资本家——公司所雇佣的。在周末工人被付给按照在他们进入工厂大门之前——即劳力支出前——就固定下来的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计算的薪水。而且,工人是在资本家有机会得以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之前就收到了薪水的。那么资本家对每件产品所承诺的薪水是如何能够不超过他可以从这件产品中获得的,并且又不低于吸引工人和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价钱的呢?更明确地说,劳动过程是如何被组织从而得以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的?
主张如果没有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就将崩溃并不是要解释其存在。如果阶级斗争可以迫使劳动力的价格(工资)高于其价值,即超过其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是什么给这个上涨的工资水平加一个限度呢?资本家如何能够预先知道每件产品的工资水平超过了其出售所能得到的价格呢?在谈到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时,马克思认为,除了别的以外,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量会不断增长,但是工人数量(可变资本)也在增长,因此总的剩余价值相对于总资本的扩张是缩水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衰亡的分析是基于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其工资的假定。
当我们比较资本家的位置与领主的位置时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个问题。在封建主义中,提前决定的是表现为地租形式的剩余劳动,而在资本主义中,预先确定的是工资。正如农奴不得不在为他们自己生产留下的时间内为自己谋生一样,资本家或他们的管理代理人必须组织劳动过程,以此确保对剩余劳动的榨取。
当然,马克思关于在劳动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的机制有很多东西要说。于是,他描述了英国的工厂法案(Factory Acts in England)实施之前,资本家们是如何延长工作日的。限制工作时间通过立法后,资本家们诉诸加速、引入计件工资制和机械化等手段来强化劳动过程。但是这些也只是给了个别资本家暂时的竞争优势,因为工作的步调最终会被其竞争对手们所赶上。通过提高生活必需品部门的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再生产中必要劳动的数量(即使其成本更便宜)是提高剩余价值比率的唯一的可持续途径。
所有这些机制,以及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大体上都是基于劳力的付出是由强迫来决定的这样的假设。为了经济上生存,工人被设定为完全受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的支配,资本家或工头可以任意地增加工作强度,只要他的命令不至于让工人第二天不再出现(有时甚至还不止这样),并且这些命令在某种宽泛的经常是非强制性的合法界限内就行。换句话说,马克思在他的劳动过程理论中没有为同意的组织留出空间,而同意的组织对诱发劳动者在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中具有合作意愿是必需的。这种疏漏即使不是合理的,在同意的舞台还很狭小的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语境中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工资变得日益独立于个体劳力的付出。相应地,强迫必须有同意的组织来补充。与合法性不同,那是个体承载的一种主观的思想状态,而同意则是通过行动组织来表现并且也是行动组织的结果。同意应当与从事这些行为的个体的明确意识或主观态度区分开来。在劳动过程中,同意的基础在于仿佛为工人们呈现了真实的选择,但又明确地限定了这些选择应是什么的这些行动的组织。正是这种对选择的参与产生了同意。只要强制的实施被限制在不逾越这种狭窄的但又是明确的和公认的选择界限内,它也可以成为同意的对象 [^26]。因而,对剩余价值的保证也必须作为强制和同意的各种组合的结果来理解。
但是赢得 无偿劳动不同于实现 剩余价值,并且正是它们的分离引出了对资本家的进一步的问题。在封建主义中,剩余劳动不仅是固定的,并且呈现为一种直接可见的、通常是可直接消费的形式。在资本主义中,剩余劳动既不是可见的也不是可消费的。于是无偿劳动作为利润的来源就被以多种方式遮蔽起来了。首先,资本家通常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新机械,即通过资本投资来增加利润。这样,资本看起来就像一种指向其自身的力量——产生利润的力量。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变动劳动强度贡献的仅仅是围绕平均利润的利润率的变化。也就是说,从那些指挥生产过程的人的立场上来说,利润的来源是资本而不是劳动。
其次,剩余劳动只有通过商品在市场上的出售才能以利润的形式实现。某种特定商品售得的价格通常是超出个体资本家的控制的。因此利润的多少看起来是由供求的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商品包含的无偿劳动时间决定的。尽管在价格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之间有一种关系,但是对于个体资本家来说它是复杂和朦胧不清的。因此利润不仅是在市场中实现的,看起来也是发源于那里的。简言之,资本家困境在于赢得剩余价值又使之不可见。^27
对资本家而言,掩饰剩余价值就像赢得和实现剩余价值一样是个问题,但就工人的从属性而言,这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要特性。如果无偿劳动的存在变成透明的,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身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领域,需要超经济元素的介入来进行生产周期的更新。那么对于资本主义中的工人来说,无偿劳动是如何被弄得神秘难解的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没有被区分开来,并且工资又遮蔽了这样的区别。工人们没有生产工资等价物或生存手段这样的观念,因为他们所生产的物品甚至有可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有用之物的一小部分。然而,生产的过程在工人看来就是劳动过程,即物品——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所有权与控制的体制化分离——即生产关系与生产中的关系的分离——强化了这一点。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们体验到经理是支配者的代理人,固然也是劳动力的出售者,凭借着他们的训练和专长,得到比工人更高的报酬。经理们也获得部分剩余劳动,这一点在劳动过程中是看不到的。
尽管对于工人和资本家而言,剩余价值都是神秘的,但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会向工人揭示出表象背后的运作。通过集体工人的出现,通过工作的相互依赖与均质化的发展,以及最重要的是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将会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同资本的利益之间的对抗,后者是植根于对无偿劳动的占有上的。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的预言是不充分的。大体上,工人们并不将他们生产的产品与他们得到的报酬之间的差别归结到自己的劳动中。^28 关于剥削与无偿劳动的观念,在今天的车间日常生活中比起马克思的时代更加感受不到了。
如果工人不把他们自己的劳动认作是利润的来源,那么他们同意什么样的关于利润的理论呢?我在车间里遇到的最经常持有的观点是,利润是某种形式的对以往的牺牲或者资本投资风险的报酬。其他人则认为利润是在市场上产生的,特别是一种对价格的操纵的结果。这种工人和资本家关于利润理论的汇聚反映了先进资本主义组织下利益的汇聚而不是分歧。当工人到了将自己未来的生计认为是取决于资本家雇主的生存和扩张的程度时,他们也将接受这样的利润理论,即利润反映了寻求利润的资本家出售商品的经验。[^29]
剩余价值是怎样持续地对工人保持晦暗难明的?劳动过程的演化和阶级斗争如何未能为利润的来源去神秘化?工人是如何未能将自己组织为一个其利益和资本的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的?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多答案——带着我们超越劳动过程而进入国家、学校、家庭和文化工业的答案,或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构建的答案。在本研究中我将有选择的借用这些发展的洞见,但仍将把它们重新放置回劳动过程中。我将回到马克思的焦点关注,但是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弹药。
结论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确定本质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资本家如何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不可见的时候确保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在生产时的零散和原子化——掩饰剩余价值的本质特性——但这些理论并没有解释剩余价值是如何赢得的。[^30] 掩饰剩余价值对于赢得剩余价值是必要条件的但并不充分。换句话说,不仅有必要解释为什么工人们没有按照一套被假定的利益行动,还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他们试图实现另一套利益。因此,劳动过程应当从强制和同意的特定结合方面来理解,这一结合能够诱发追求利润当中的合作。
通过考察一个特定工厂在 30 年的时期中劳动过程的变化,我希望阐明下述各种机制,即在车间内组织同意、使工人成为个体而非阶级成员、调整劳动和资本之间以及工人和经理之间的利益,并且重新分散冲突和竞争的这些机制。简言之,除了上面概括的那些之外,我要讨论这样一种机制:通过它可以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这就是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主题。在第四部分,我要展示市场变化和外来意识是如何在由劳动过程所界定的界限内起作用的。在第五部分,我将解释劳动过程中那些增强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能力的变化的来源。
[^1]: 本章中的阐述受到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的很大影响: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保卫马克思》(For Marx, London: Allen Lane, 1969);尼克斯·普兰扎斯(Nicos Poulantzas)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以及最重要的,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收录于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编著的《读〈资本论〉》(Reading Capital, New York: Pantheon, 1970)第 201—308 页。与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这些法国理论家试图离开对历史的目的论的观点,在其中生产模式的交替是遵循一种固定并且必然的与“生产力”的扩张相一致的范式。由他们引入的不确定性被巴里·海因兹(Barry Hindess)和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5)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形式。
[^2]: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第 48 页。
[^3]: 生产模式更经常的被视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一种组合。我一直避免使用生产力的概念有两个原因。首先,它经常被呈现为一组事物——原材料、机器、技术等——它们本身是对于剥削和支配是中立的。这里我要提出这种在其中生产关系在占有自然的模式上留下了他们不可磨灭的印记的方式。其次,生产力的观念常常是与对历史的目的论的观点相联系的,其中生产力的扩张必然会推翻资本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铺下基础。在本研究中我试图驱散这种无历史根据的乐观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概念的更详细的评论请参见布若威(Micheal Burawoy)的“生产的政治与政治的生产:对美国与匈牙利的机械工厂的比较分析”(“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chine Sho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ungary”),收录于《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 1》(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 1979)。
[^6]: 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第 3 卷(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7), 3: 791。
[^7]: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 233 页。
[^9]: 同前书,第 74 页。“对马克思而言,真实中的每种决定了的结构都有其对应的决定了的表现模式,并且这种表现模式是结构的某种自发意识的起点,其与意识和个体均无关。随之而来的是结构不会破坏该结构的自发意识的科学理解。结构修改其角色和效果但不会压制它。”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资本论中的结构与矛盾”(“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Capital”),收录于《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编(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第 338 页)。
[^10]: 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将意识形态视为被铭刻于商品的生产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指涉支配阶级通过垄断传播思想的手段来操纵和将思想注入于被支配阶级的能力。见马克思的《德国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第 64 页。同时,他坚持这些操纵是有限度的,并且在他的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讨论中说明了这事如何与资本家的观点相符合的。很自然地,与给定的活的经验相啮合的意识形态的范围是随语境而变化的。在阿尔文·古尔德纳的对意识形态的激烈的讨论中,他通过引用巴兹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关于受限制的精细的语言学编码的概念以类似的术语阐明了这个问题。[《意识形态与技术的辨证》(The 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6]
[^11]: 尼克斯·普兰扎斯很好的表达了这一立场:
在谈到意识形态的机构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机构既不创造意识形态,甚至它们也不是再生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的独立的或主要的因素。它们只是服务于倡导和反复灌输支配的意识形态。因此韦伯在主张教堂创造了宗教并使其永存这一点上是错误的:确切地说是宗教创造了教堂并使其永存。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系这件事上,当马克思将商品拜物教分析为直接与资本的稳定化相关时,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支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超越了机构的绝好的例子;这是被马克思本人在他的常看的参考书中记录为在“制度”与“社会意识的形式”之间的“一致性”的,其中他暗示了区别所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第 31 页]
[^12]: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列宁与哲学及其他杂记》(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第 168 页。
[^13]: 马克思,《早期作品》(Early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第 251 页。
[^14]: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ilishers, 1971),第 126 页。
[^1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稿件的序言”(“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收录于《马克思 - 恩格斯读本》,Robert Tucker 编(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72),第 5 页。
[^16]: 尤金·杰诺维斯(Eugene Genovese),《碾啊碾,磨啊磨》(Roll, Jordan, Rol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17]: 对于这两种观点的说明,可以参见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第八章。
[^18]: 莫里斯·戈德利耶《经济中的理性与非理性》(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第 45 页。
[^19]: 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马克思的需求理论》(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第 60 页。
[^20]: 例如,可参见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编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演变》(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Nooks, 1976);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专制主义国家的谱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海因兹(Hindess)与赫斯特(Hirst)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Robert Brenner 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亚当斯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批判”(“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 104 [July-August, 1977]: 25—92)。
[^21]: “唯物主义历史概念中的生产模式”(“Modes of Production in a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apital and Class no. 3 (Autumn 1977): 19。
[^22]: 海因兹和赫斯特为这个传统的解释加上了下面的重要的限制性注释:
尽管他[佃户/劳动者]可能拥有生产工具,对土地具有承租权,并且有能力组织维持其生计的生产,但他不能控制生产手段及条件的再生产。地主/剥削者主要是通过对生产手段的再生产的控制而将佃户/劳动者与生产手段分离开来的。尽管如此,应当注意到,对于领地生产下的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控制,以及对于某些重要的生产手段(磨坊、堤坝等)的所有权及操作,是对于封建领主的再生产的条件的重要的控制手段。[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p. 238]
[^23]: 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在其对 13 世纪的英格兰的分析中写道:
任何曾研究过庄园惯例汇编的人一定被它们达到的极端细微而震惊。例如,它们一般不会简单的说人们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耕地、播种并且耙地一英亩。它们说他必须以他所有的牛和他的犁来耕地,用他自己的马耙来耙地,并用自己的马和麻袋从领主的谷仓里拿种子来播种。服务被以极其详细的细节来记录的,并且如果进一步的细节,即使是最明显和最必要的,没有被惯例汇编所指定或被过去的很长的执行的历史所证明的话,它们也不是惯例并且不被执行。[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5), p. 272]
霍曼斯所采用的这幅静态的影像一部分是他的偏见的反映,但也是他选来研究的这个特定时期的一个反映,这段时期是封建英格兰的历史上最安定的时期之一。对于更多样化和动态的图景,包含了关于劳动租金的交换的斗争的,请参见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的《中世纪社会》(A Medieval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第五章;科斯明斯基(E. A. Kosminsky)的《十三世纪英格兰的农耕历史研究》(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6),第三章;以及波斯顿(M. M. Postan)的《中世纪经济与社会》(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75),第九章。
[^25]: 比如,参见希尔顿(Rodney Hilton)的“英格兰的自由与农奴制”(“Freedom and Villeinage in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 no. 31 (July 1965): 3—19。
[^26]: 或者,如阿尔都塞提出的那样,“个体被作为(自由的)主体来质询以使得他会(自由的)接受他的服从地位,即以使得他会‘靠他自己’而做出其服从的姿态或行为。”除了被其服从地位所驱使的和为了服从的之外别无主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是自己独力工作。’”(《列宁与哲学及其他杂记》,第 182 页)表面的自由,即有限的自由的创造以及同意在车间里的表达,可以用当我问工友们为什么那么卖力工作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回答来说明。一般的反应是一脸困惑,并且来上这么一句:“你觉得我工作卖力吗?”他们会一边自己吃吃笑着一边走开。换句话说,很多工人不仅不觉得他们工作卖力,他们还觉得自己在尽可能地吊儿郎当糊弄管理层。其他人则会说,“你总得讨生活吧。”这样的回答否认了来上班与在工作中卖力的区别——这样的区别在别的评论中被提出来:“工作中最难的部分就是来上班。”反过来,操作工们会说,“我来这还能干什么?”或者“这能让时间过得快点。你要是不干活会无聊的。”努力工作是对例行的单调任务中内在的剥削的适应。有人会主张,“如果我们不这么努力工作,公司就会破产而我们就会失业”——这是一种对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共同利益的承认。而另一些人,像我的白班搭档比尔,很明显的更乐于努力工作而不愿“吊儿郎当”。我猜想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过很少有人承认。在这些回应当中,有意思的是,没有把畏惧或者强迫作为动机因素的,并且认为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要多努力地工作是一个真实的开放的选择。此外,在评估这些选择和决定他们是否要努力工作时,他们毫无疑问地比照管理规范来量度自己的行为。并且他们承认如果一贯的“吊儿郎当”是有可能被开除的,但是这种惩戒行为是被视为合法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29]: 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利润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异——不只在于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异——在于生产的诸多领域,现在它们完全遮蔽了利润的真正性质与源泉——不只来自于对自欺为利润的源泉尤为感兴趣的资本家,还来自于劳动者。价值转变为产品的价格掩盖了决定价值本身的基础。[《资本论》第三卷,第 168 页]
[^30]: 例见,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编《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76);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公司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与劳动市场结构”(“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Firm and Labor Market Structure”), Politics and Society 5(1),第 83—1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