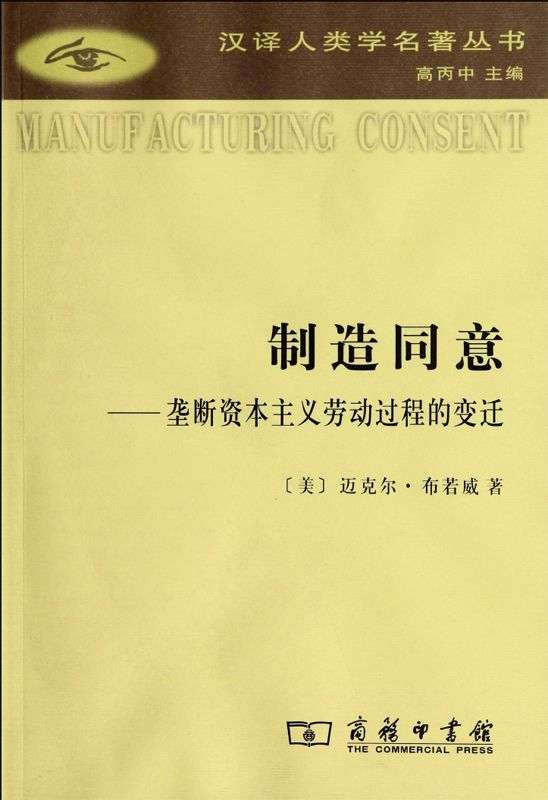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五章 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五章 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追随马克思,经常也太轻易地就把薪酬劳工简化为操纵的客体、在市场上买来卖去的商品、无力抵抗的抽象集合、资本主义积累的无情力量的受害者、社会关系的承载者、代理人或支持者。[^1] 重建劳工的主体意义、挑战没有主体性的主体观念、强调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抵抗,这些都留待工业社会学来处理了。但是在高举主体的意义的同时,工业社会学也轻视了客体的意义,视之为不可变的。它认为,薪酬劳工与对产业工作的掠夺,是匮乏体制中物质存在所不可避免以及永恒的伴随物。
并不奇怪,工业社会学以在工人中进行的态度调查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些调查指出工人顺从于固有的工作掠夺,并采取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指的“实用主义的角色接受”(pragmatic role acceptance)态度。[^2] 同时,工人们竭尽全力来补偿,或最小化他们所经受的无情的和不可避免的掠夺:
[一名工人]抓紧其工作中最后一点残余乐趣的机会……不论机械化把所有的行为变得多么冷酷无情,它们都提供了一定的主动的范围,这多少可以满足游戏本能和创造性地推动力……即使当行动的细节已经被以最极致细微的程度所规定时,并依照泰勒系统的最新指导原则,仍然为工人留下了某些漏洞,某些可以逃脱惯例的机会。所以当实际工作时,他会发现有可能不时地享受自我决断的奢华。[^3]
比起其他的社会学家,威廉·巴尔达穆斯对产业工人们能得到的补偿的性质做了更多的考察:
艰苦工作并不必然只反映在不适的感觉中。它还可以产生某种满意感。事实上,所有工作中的剥夺都可以与我所称的“相对满意”联系起来。它们是从某种工作现实的不适中暂时解脱的感受,是当这些因素变成工人对其境遇的惯常解释的一部分时产生的感受。就此意义而言,它们仅仅是实际上源自于剥夺的表面上的满意。[^4]
工作现实(物质条件、重复和惯例)引起了剥夺(损害、烦闷和疲倦),而剥夺造成了相对满意(习惯、吸引或驯良,以及满足)。^5
如许多作者所观察到的,这些相对的满意经常是以游戏的形式被构建的,这减弱了“无止境、无意义动作”带来的过度压力。[^6] 按照推测,工人对资本主义工作的要求似乎有自主回应;社会学家对此的评价中显示出了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承认这些相对满意对劳工的心理和社会健康有所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些满意会削弱管理的客体。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 Whyte)明确地表达了这一两难局面:“玩这个计件工作游戏所伴随的满意可以在我们工厂保持,而同时与游戏相伴随的冲突又会减少吗?”[^7] 游戏创造了利益的对立面,而在此之前只有和谐。在 F. J. 罗特利斯伯格(F. J. Roethlisberger)和威廉·迪克森(William Dickson)的经典研究中,他们提出,“雇员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和自己的‘逻辑’,而这经常与那些加诸于他们身上的规则与逻辑相对立。”[^8]“这个[产量的]标准并不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而显然是被工人们自身所阐明的。”[^9] 在其对“银行配电间实验”(Bank Wiring Room Experiment)的解释中,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声称团体的规范,比如产量限制,是被“自发生产的”的,以此保持团体的完整性。[^10] 在埃尔顿·梅奥的作品中,有关霍索恩工厂的工人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工作自主原则的观点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他谈到了一个“在更低层面上反对[资方]的经济逻辑的社会法规”[^11] 的形成。与之类似,米歇尔·克罗齐埃(Michel Crozier)主张,在工业场景的广泛多样性中,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是被从属者所利用的,这导致了针对资方的权力斗争与对抗性的非合作游戏。[^12]
所有的这些论述都共享了同一个观点,即工人们自主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生产系统以反对资方。反讽的是,恰恰是对其而言阶级分析是令人厌恶的那些社会学家,也正是为这样的进路提供了最大的支持的人。不幸的是,正如他们的理论框架是不充分的,他们的经验证据也是同样脆弱的。在《管理与工人》(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一书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团队主任、分部主任、助理工头以及工头都默许或者积极协助了按说是破坏资方利益的游戏的进行。^13 贾森·迪顿(Jason Ditton)说明了通过放松规则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是如何增强了资方的权力,而同时这又为游戏的构建提供了基础。[^14] 斯坦利·马修森(Stanley Mathewson)提供了许多资方组织产量限制的形式的例子,梅奥则将其归因于工人对资方本能的与非逻辑的反抗行为。[^15] 另一方面,当游戏(比如在组装线上加倍)真的威胁到经营目标,即危害到利润空间时,资方的确会强硬地介入。[^16] 克罗泽自己就指出,“要是它不加阻止地发生的话,权力斗争就会带来瘫痪性的冲突和无法承受的困境。”[^17] 简言之,游戏确实发生的时候,它既不独立于也不对立于资方。
我在联合公司对车间管理层在超额游戏中的角色的观察,以及罗伊在吉尔公司的观察证实了这些结论。我已经提到工头积极协助操作工超额的不同方式——向他们说明伎俩、抱怨方法部门严格的工资率、在保护绩效时对他们自己的老板使用超额习语,等等。当操作工上交超过可接受的限度(140%)时,不仅工友而且车间管理层也会抗议。因而,当操作工显示出超过 140%时,主管经常把工时卡返还给他们,要求他们减少零件数,并把剩余的攒起来。工时职员也会检查以留心 140%的最高上限不会被违反。车间各级管理层都关注稳定的产量和配额约束;他们并不比操作工更喜爱产业工程师。[^18] 指定一项工作的新工资率意味着人员的流动,因为工人们倾向于调到工资率更容易干的工作上去。结果,会造成培训成本增加、产量水平下降、废品量上升等后果。反过来,操作工也会因为新的工资率“不可能达到”而“偷懒”,而这也会引起更低的产量水平。我将在第十章中讨论这些以及其他紧缩工资率的有害后果。可以充分地说,车间管理层不仅鼓励操作工生产其配额,而且也积极地默许操作工设下限制产量的行为;也就是说,资方积极地参与到超额游戏中。的确,工头和计划员是这个游戏中的玩家。
作为总结,通常来说,并非像梅奥从一个视角观察这件事以及卡斯托里亚蒂斯从另一个视角观察所主张的那样,工人们所玩的这一游戏并不是在与资方的对立中自主地创造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从斗争和讨价还价中历史性地形成,但基本工资与可接受的利润空间限定了游戏进行的规则。管理层,至少是较低层次的管理层,不仅积极地参与到游戏组织中,而且参与到其规则的执行中。参加到工作游戏中去的驱动力,既源自无从选择必须工作的压力以及听从劳动过程的命令,也源自“基本需求”、“工作的新视界”或“非逻辑的法规”。游戏成为获得相对 满意,或者马库塞所称的压抑的 满意的一部分。游戏代表了一种需要,而需要确实是“支配性利益要求抑制”的社会的产物。[^19] 这种需要的满足不仅再生产了“自发的奴役”(同意),也再生产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现在必须转向具体考察参与工作游戏是如何有助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以及剩余价值的扩张。
掩饰并赢得剩余劳动
正如在第四章中描述的那样,超额不是将工人作为由他与生产手段的特定关系来区分的阶级成员,而是作为单个的个体,而插入到劳动过程中。工人控制他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所控制,而这提高了他们的自主性。他们单枪匹马的开动机器,而这造成了他们作为个体就能够将自然转变为有用的商品这样的表象。薪酬体系基于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努力程度。其次,对于机器的自主性和对于辅助人员的依赖这两者的结合带来的后果是使等级间纵向冲突转向横向冲突的重新分布,在其中,个体劳工以冲突或竞争关系来彼此面对。将工人建构为身处诸多相互竞争与冲突的他者中的一员,既掩饰了他们共同的阶级属性,即同属于一个为了工资而出卖其劳动力的生产者阶级,也掩饰了他们与占有他们的无偿劳动的另一种阶级的区别。
然而,从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游戏的重要性超出了超额的特殊性。正是这种参与游戏的行为产生了对其规则的同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显而易见但也重要的断言,即人不能参与游戏的同时又质疑其规则。问题在于:就逻辑和经验而言,参与游戏与规则的合法性,哪一方是先在的?在此,我不是要说参与游戏有赖于广泛的一致同意;正相反,同意依赖于参与游戏,通过参与来建构。游戏并不反映潜在的利益和谐;正相反,它是和谐的原因并产生了和谐。游戏自身的来源不在于预先注定的价值共识,而在于为了适应内在于工作中的剥夺的历史性特殊斗争以及与资方争夺定义规则的权力的斗争之中。
在超额这一例子中,以一系列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规则,是根据游戏的明确结果来评估的——超额还是没有超额——而不是根据游戏的广义结果来评估,例如利润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等等。因此,就其被体制化这点来说——就像在超额中那样——游戏自身即为目的,它遮蔽、掩饰甚至颠倒了它从中发生的条件。当工人加入一个含有他们与某一机器的关系的游戏时,他们对生产过程的从属关系就变成了默许的对象。同样地,加入一个包含了其他生产行动者(工人、工头等)的游戏中,会在铭刻于劳动过程中的社会 控制关系——即生产中的关系——中形成默许。至此,参与游戏的两种后果已经被描绘出来了:首先,对游戏的参与遮蔽了游戏最初被建构以回应的那些生产关系;其次,对游戏的参与产生了对界定游戏规则的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同意。
个体(作为与集体的对立)违反规则会导致例行的惩罚,这具有增强遮蔽及生产同意的效果。也就是说,违反规则具有加强它们控制生产性行为和关系的结果。因此,资方从工人身上额外压榨的企图常常会增强车间里的两厢情愿的关系。联合公司的操作工一直抱怨被公司“压榨”,一开始,我把这与某种剥削的模糊观点联系在一起。不久我发现这种苦痛指的是公司没能提供必需的条件来进行超额的游戏;例如,钻头可能被烧坏了、设计图可能不见了、机械可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等等。换句话说,资方是因没有按照游戏的规则来玩而被谴责的;而这些谴责有助于重申规则的合法性与超额的价值。这样这种两厢情愿的框架一直得到重建与加强。
仅仅遮蔽所有权关系以及造就对生产关系的同意是不够的;工人们必须创造超过他们的工资盈余。工人是如何被说服与追逐利润相合作的呢?显然,一种手段——不过通常来说不是很有效的一种——是通过持续的施加强迫,即通过解雇那些不能达到给定配额的工人。当然,强迫是位于所有 雇佣关系背后的,但是游戏的建立为组织积极合作以及使同意占上风提供了条件。
如泰勒与他的合作者提出的那样,计件工资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可以由劳工的额外努力来确保的资方与工人在财政收益上的共同利益而调整它们双方的利益。是货币刺激引出了额外的努力。人际关系研究传统将产量限制作为经济刺激失败的象征。正如罗伊所指出的,并且从迄今为止我所说的就可以明显看到的,产量限制与最大化经济收益相一致。同时,罗伊和我都观察到,货币刺激不能充分解释由超额所产生的合作。
如果技工的“口头”行为作为行动趋向的指数被接受的话,就可轻而易举地以“经济刺激”来解释计件工资体系的部分成功;也可轻松地将其部分失败 归因于刺激的处理不当……另一方面,作者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少数似乎否认“经济刺激”的全能影响的“反例”,并指出更加细致地考察计件工作的回应的需要。例如,在某些场合,在“配额”的达成被认为是可能的情况下,操作工没能竭尽全力来达到“配额”的收入,或者在低于“配额”水平线时就停了下来。操作工有时也漠不关心能否把“拿回家”的收入最大化:(a)不愿加班工作,(b)当工作不适合于他们时,还未到轮班就“早退”,或是(c)“歇息”以避免“整天工作”。另外,有时操作工的“口头”行为显示他们并不“在乎钱”。[^20]
当我在联合公司的时候,我观察到了类似的行为模式,它们与经济动机作为超额基础的理论相抵触,不过这些行为模式是以经济收益的习语 来表达的。此外,如果经济动机位于车间行为的基础,那么工作的偏爱等级就应与经济报酬相一致。可实情并非如此。许多按日工资率计算的服务工作被广泛地认为是比按计件工资率计算的工作更好的,尽管后者可以拿更多的钱回家。更确切地说,劳动过程被组织为游戏,而这个游戏界定的目标构建了当前车间里的价值。像往常一样,罗伊以图解形式表达了这一点:
“超额”可以被认为是“目的本身”吗?或许,“配额”的达成标志着成功地完成了一项“行动”或“任务”,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由操作工来控制的;尽管“机会”因素也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超额”要求技能的锻炼和毅力;它提供了“自我表现”的机会。总会存在的“糟糕的停顿”的可能性带来的结果的不确定性元素,把达成“配额”变成了一场与墙上的时钟之间的“刺激的游戏”;知识、技能、独创性、速度与毅力的运用所提供的控制元素,提高了游戏的趣味,并增添了“成功完成”的“胜利”感的愉悦。尽管操作工们经常以分享他们的计件工作经历作为主要的谈资,并总是以“挣钱”来聊,实际上他们是在沟通“游戏得分”或“竞赛结果”而不是金钱上的成败。我怀疑是否有操作工曾想过他“挣到了钱”。很可能如果有人真表达这样的信念的话,他会被嘲笑出车间的。[^21]
换句话说,超额不能简单地按照表面上达到更多收入这样的目标来理解。更确切地说,它在车间文化中的支配地位是从一系列特定的生产中的关系中显现并内嵌于其中的,这些关系反映了资方在创造利润中的利益。超额的报酬是按照直接与劳动过程相关的因素——减少劳累、消磨时间、减轻厌倦等等——以及从劳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因素——在艰苦的工作中超额的社会的和心理上的报偿感,以及搞砸一份有油水的工作而带来的社会耻辱和心理挫败——而界定的。
并不是货币刺激实际地调整了资方与工人的利益,而是参与游戏本身产生了游戏结果中以及游戏连续性上的共同利益。任何为其参与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报酬的游戏,都在其参与者中——不论他们是资本的代表还是劳动的代表——建立了一种共同利益,这为其再生产准备了条件。只要游戏涵盖了整个劳动过程,它所引起的价值体系就会在车间里盛行。作为游戏的后果,行为得到评价,并且利益被建立了起来。换句话说,利益并不是原生的被给定的,它们也不必然是被工作之外的社会化经验带到车间里来的。确切地说,生产中的关系的特定形式组织了利益;在我们的例子中,与超额游戏之间的关系界定了利益。一旦他们的基本生存——就工人而言,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工资——得以确保,日常经验就从工作组织中浮现出来,并且界定着各种生产行动者的利益。[^22] 当劳动过程被组织成包含了资方与工人的积极参与的某种形式的游戏时,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具体的调整。在其他工作情形下,劳动过程将不同的利益群体蹩脚地组织起来,造成工人利益与资方利益不可挽回的敌对状态。
再说一遍,通常,以游戏来表述的工作概念源于对不可化约的和谐的假设。游戏是工人自发的、自主的、恶意的创作物;它们产生权力斗争以及与资方的冲突。透过否认利益的原生性并强调它们从工作组织中显露出来,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游戏确实是起于工人的主动性,起于寻找忍受劳动过程的从属地位的手段,但是它们是被资方所管制、必要时是被强制的。然而,一旦游戏被建立起来,它就可能具有自身的动力,而且不能保证它会持续再生产其存在的条件。正相反,参与游戏可能会趋向于破坏那些定义了游戏的规则。因而,在马克思的计件工作概念中,工人力量不够强大,也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以执行产量限制。^23 相反,他们被迫彼此竞争,以更快的速率生产,而这刺激了资方削减计件工作的价格。计件工作的“游戏”变成了强化劳动的自我挫败的螺旋,除非通过操作工转变规则并限制竞争使其稳定下来,比如在超额当中。直到那时,工人们才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囚徒的困境”中:工人个体利益——产量的最大化——的操作会破坏工人的集体利益——更高的计件工作价格。彼得·布劳(Peter Blau)描述了一家州立职业介绍所的产量游戏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同样的冲突。在那里工人间的竞争提高了个体的产量但却损失了集体的效率。也就是说,游戏本身生产了使该游戏更难以进行的条件。布劳补充说,“这提出了在这里不能回答的有趣问题:什么条件决定了这个过程会最终平稳下来,还是会达到一个从竞争性结构到合作性结构的革命性转变的顶峰?”[^24] 或者,更一般些,人们会问:再生产游戏的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游戏自身的动力会破坏也由其产生的和谐,并从而导致危机?更明确地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超额可以持续地在车间里进行下去?这个游戏会有生产同意和利润之外别的后果——会有持续威胁其再生产的后果吗?超额播下了其自身毁灭的种子吗?
不确定性与危机
许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作者们都坚持组织的效力和效率的提升是视不确定性的最小化而定的。[^25] 这里我要提出,确保工人的合作有赖于最小的不确定性,有赖于工人坚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的可能性,即使仅仅是一个有限的类型:
但是操作工在“配额”计件工作中的利益似乎有其“收益递减”现象。例如,麦卡恩谈到一个“有油水”的计件工作的无聊,[说到]有那么多他“睡着觉都可以干”的活。他的体验表明计件工作的“超额”只有在工作表现为一种对操作工的“挑战”、只有当“不确定性”元素呈现在行为的结果上时……才是一个刺激的“游戏”。如果因为操作工可以完全控制工作以至于“胜利”退化为纯粹是例行的,而使得“超额”失去了它的价值,那么如果不确定性元素变得对控制性元素过于占优势,它也会失去这样的价值;即如果“糟糕的停顿”变得过于令人灰心以至于无法施用技能的话,工作也就变成了“伤脑筋的”。[^26]
在下面的三个条件的任意一条下,游戏都会失去其吸引玩家的能力:首先,当不确定性过大而结果完全超出了玩家的控制之外时;其次,当不确定性过小而结果可能变得完全由玩家控制时;第三,当玩家对于可能的结果漠不关心时。
让我们各举一个例子吧。我的工作之一,也是我特别讨厌的,是在一个钢质“滑板”上钻直径 3/16 英寸、12 英寸深的孔。比尔的被称为“蹦蹦跳”的东西被永久地为这项工作设定好了。它使用 13 英寸长的钻头,一次可以钻两个滑板。每切削一个很短的深度,钻头就会被弹起来以带出碎屑,然后被再次插回去钻另一个短的深度,如此进行下去直到孔被完成为止。一旦开始,蹦蹦跳就会自动地连续运行直到孔被钻完。由于钻头很长并且有时比较钝,所以它们经常会断掉,并且如果它们没能及时被弄出来,压力会使得钢屑四处飞散。这工作不仅危险而且是令人灰心的,因为工资率不允许打断钻头。此外,断裂可能发生的条件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预测的:钻头可能在其中断裂的钢铁的深度;它可能断裂的速度以及它在断裂之前可以被使用的次数。这工作令我紧张不安,并且在我打断一两根钻头之后我都没想要尝试超额了,而宁愿活着待着并保持心理上的健康。不过,我的白班搭档比尔,在杂项工作上有着 10 年的经验,并且他决不是在对其聪明才智和技能的挑战面前退缩的人,他试图超额,实际上一般都能做到大约 125%的数字。但是他也不喜欢这个工作。因而,对于某人来说有过多的不确定性的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但是道理仍在:当有着过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参与者就会中止进行这游戏了。
在相反的极端上的是在自动锯上的工作,它可以保证 125%的产率。这样的工作是乏味的,因为它只要求很少的注意力,尤其当库存为直径八英寸的条钢时,因为那时锯子一小时只能切削大约四段。当面对这种情形时,我在锯子运行时会走开找点别的活来干,以此来建立我的小金库。
最后,关于结果的评估我们可以说些什么呢?我已经提到了罗伊和我第一次进入车间时都带有的对超额蔑视以及我们最终如何都屈从于它的指令。的确,我们都沉迷于这场游戏并变成了热心的玩家。我必须承认,至少在我自己的案例中,我最初的轻蔑部分是一种防御,以掩盖我对于超额或者是对于预见任何这样做的前景的无能为力。不过,如果任何的汤姆、迪克或者哈里从大街上走进来就立即能够超额而不需要任何先前的经验的话,这会是什么样的游戏,又包含了多少不确定性呢?换句话说,罗伊和我——事实上任何其他进来并对机械车间毫无经验的人——花费了几个月才获得奖励津贴的事实是为建立与超额相连的价值与尊重服务的。新来者被分到工资率最严格的工作,这个惯例从短期来看会产生退缩和苦涩,但最终会增强对超额价值的承诺。正如罗伊和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们要成为车间里的一个人物的话我们最好开始超额。直到我们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会一直作为轻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被排斥。[^27] 我们拖延的越久,我们的名声就越差,并且我们会变得越加不被社会接受。超额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资方(在我自己的案例极少有这种),而且来自于工友和辅助工人。此外,参与这个游戏带来的不只是社会的回报——也就是还有心理的回报。当一个人在试图超额时,时间过得更快——事实上是太快了——并且他的劳累感也较少。因而超额与不超额的区别不是以我们挣得的几美分奖金来衡量的,而是在于我们的声望、成就感以及自豪感。参与游戏消除了大多数与产业工作相连的辛苦乏味与厌烦。
在分析计件工作的回应时,不能声称“经济的”动机在被调查的情形中对于“配额”的获得一点作用也没有。不过,这表明计件工作可能提供了一个激励的复合体。“计件工作的激励”可能包括“经济的激励”,但前者并非后者的同义词。因此,如果计件工作在某些条件下“奏效了”,即在一个给定情形下,刺激了机床操作工生发出生产性的努力,这并不一定表示这种刺激可归结为经济性激励的。或者,计件工作的“失败”也并不能证明经济激励生来就不充足。工人表达“我不在乎钱”所标明的可能并非经济刺激本身不充足,而是足够数量的经济回报的可能性情形的缺乏,无法刺激出“关注”。[^28]
对游戏的参与基于结果不确定性的两个限度:一方面,工人必须确保可得到一个最低限度的可接受工资;而另一方面,资方必须确保可获得一个最低水平的利润。虽然参与超额游戏并不会直接威胁到最低工资,但在某种情形下会危及利润。我把第一种类型的危机称为系统危机(system crisis)。第二种类型的危机滋生于由于达成超额的不确定性过大或过小(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抑或是由于超额对玩家而言不再具有任何价值(动机危机)(motivational crisis),从而造成工人们从游戏中撤离。[^29]
系统危机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资本主义是如何能够做出一个预先对工资许诺但同时又能确保一个可接受水平的利润呢?在吉尔时代,对剩余价值的抽取表现了吉尔作为一个公司的生存,而在他们对利润的渴望中,为了避免第一种危机,吉尔的管理层经常陷入第二种危机中。提高产率,改变规则,削减更新设备的成本等等,都促成了合法化危机,最终表现为一场罢工。与之相比,联合公司可以幸免于系统危机,同时又不会陷入到合法化危机中去。因而,当引擎分部亏损时(正如 1974 年的情况),由于一些与参与超额无关的原因(我在第八章中将会说明),管理层没有做出通过改变规则或产率而破坏超额基础的重大尝试。亏损被公司吸收了或者被转嫁给了客户,并且一位新的总经理被安插进了引擎分部。
系统危机的悖论在于在事前它是不可知的。1975 年的头 11 个月内,小零件部门的个体产量水平表明绩效持续低于由产业工程师所设定的标准产率的 75%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无从知晓能够确保利润的实际最低水平,因为这取决于机械车间里所有操作工的产量,而这些产量却是在持续变化的。
第二种类型的危机可以通过比较不同工作的产量水平来量度。只要不确定性超出可接受的限度,那么或低或高的,产量会集簇在 140%或 80%的分数附近,或者二者兼有。[^30] 产量水准位于二者中间表明至少有某些操作工在参与游戏,不确定性的水平是可接受的,并且操作工们对于他们行为的结果并非无动于衷。当操作工们获得了经验和资历时,他们可以调到可以产出 140%的稳定产量的机床上去——例如,自动卡盘和杆式车床或者自动螺旋机床。在这些机床上,设定需要相当多的技能和实践,但是,一旦这些被掌握了,不确定性就被消除了,并且超额对这些操作工而言 不再是一种重要的游戏了;不过,只要车间里没有动机危机,他们就会持续上缴 140%的产量。即只要其他人仍在为达到 125%而奋斗,他们就保持在声望阶梯的顶端。这些更加资深的雇员中的许多都沐浴在他们的权利和地位的光辉之中。在其他方面一样的情形下,这些雇员比起那些更积极地参与超额游戏的人来说应当更有阶级意识。的确,他们中的许多确实表现出了对公司的相当多的敌意,而其他的人则在工会中变得积极了。不过,在这些工人之间以及在与工厂里其他人的比较中,有着资历的复杂因素。资历一方面产生了对公司的更多承诺(基于对资历的奖励,比如养老金和工作的保障),另一方面则增加了介入工会的机会。作为前一个趋势的表现,甚至有一两个操作工冒着危及其声望的风险而向公司建言如何提升他们自己的机床上的产率!尽管有阿尔·麦卡恩的例子,合法性危机更可能由严格的产率而非宽松的产率中产生。自从罗伊离开吉尔之后,一般来讲,产率变得更容易达到,而这些转变是由议价的过程所推动的。结果是,过了几个月后,操作工们可以掌握那些提供了超额的所有挑战和回报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合法性危机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我们最后必须提出系统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或动机危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一场第二种类型的危机当然会促成第一种类型的危机。但是第一种类型的危机也可能由超额崩溃之外的因素所导致,例如,高的异乎寻常的培训费用或者过分的加班等等(见第八章)。另一方面,系统危机有无可能是依照其规则进行超额游戏的后果呢?如果可能的话,在何种条件下超额会促成这样的危机呢?显然,答案肯定在于操作工产量百分比的分布的可能形式之中。一个可能把该分布推向低端的事实是工作间调动率的增加。在何种条件下第二种类型的危机会被系统危机所促成?即在何种条件下管理层面对下滑的利润时会试图破坏超额的条件呢?换句话说,当存在利润危机时管理层会陷入斗争中吗?我将在第十章中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参与到超额中的条件及其掩饰并确保剩余劳动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区分至少两种类型游戏的基础。首先,存在着被限定于工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中的游戏,比如被威廉·巴尔达穆斯、罗伊和哈维·史瓦陀斯(Harvey Swados)所描述的那些。[^31] 如果游戏持续下去的话,它们可以产生对工作中固有的剥夺结构的同意。但是正如罗伊所指出的,他的“冲压”游戏没能吸引他很长时间,因为他能够轻易地掌握每一个细微的差别并消除了任何游戏的本质——不确定性。限定于单个工人及其与劳动过程的关系上的游戏,只能提供逐渐减弱的转移对剥削的注意的效果,并且,最重要的是它不能产生对于生产中的关系的同意。为了达成这种同意,必须建立起第二种类型的游戏,它涉及了生产的其他行动者。这种群体的游戏是潜在地更加永久的,因为它们更加深入地吸引着工人们的注意力并且扩大了不确定性的范围。它们需要技能,不仅仅是在机械技术上而是在人们关系的更不确定的语境中。
游戏所包含的车间日常生活越广泛,它们在掩饰和确保无偿劳动上就越有效。超额在这方面或许是一种极端类型。与之相对照,对装配线的从属在可能的游戏的范围上施加了限制,尽管这范围绝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受限制。大概劳动过程组织的越紧密,就越有可能会出现敌对的阶级关系。为了理解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如何被抑制的,必须考察另外两个在其中剩余劳动被掩饰并确保的领域——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
结论
在本章中我已经试图说明了将劳动过程构建为一个游戏是如何有助于掩饰并确保剩余劳动的。不过,“游戏”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解释工具。它也是,并且这是必要的,一个批判工具。[^32] 首先,它代表了个体理性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理性之间的连接物。正如游戏中的玩家采用能影响结果的策略,而并不总是以故意为之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为了影响结果而做出选择。结果的可能变化是有限的,但并非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之外。也就是说,我们确实创造了历史,但是并非如我们所愿。我们通过我们行动的有意和无意的结果而创造了“我们背后的”历史。游戏的隐喻暗示了一个带有其自身“法则”的“历史”,它超出了我们的控制,然而却是我们行动的产物。超额、下棋、买辆新车、选举总统或者打场战争是如此,不幸的是,发动革命也是如此。
其次,正如玩一个游戏会产生对其规则的同意,所以在参与到资本主义迫使我们要做出的选择中也会产生对其规则、规范的同意。通过将我们的生活构建为一系列的游戏、一套有限的选择,资本主义关系不仅变成了同意的对象而且还被认为是给定的和不可改变的。我们没有共同决定超额的规则应当是什么,相反地,我们是被迫来玩这个游戏的,我们继而去维护其规则。第三,正如游戏界定了一套目标,资本主义也产生了一套利益。尽管这些利益并非唯一的并且可能随时间而变化,但它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超额及其所界定的利益的确实是——如我所指出的——组织劳动过程的特定方式的产物,并且是其变动的产物。利益被认为是给定的,并且像规则一样,它们并非通过民意而形成。[^33] 第四,获胜或者最大化某人的效用的可能性使得游戏很诱人。与此相似,由资本主义(广义而言)界定的或是由超额(特殊而言)所界定的,实现某人的利益以及满足某人需求的可能性,正是产生对规则与关系的同意的手段,并且将规则与关系呈现为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其它可能性不是被消除了就是被当做乌托邦而抛弃了。出于同样原因,不满是未能满足由资本主义(广义而言)或超额(特殊而言)所制造出的需求;而不是未能满足某种先验的“根本需求”,或者甚至是共同决定什么是所需要的需求。简言之,大量存在着的不满,并未指向反抗资本主义而是指向其再生产。
作为一个批判的工具,游戏的隐喻意味着某种解放了的社会的概念,在此社会中,人们自己为自己、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历史。那里没有无意识的结果,并且规范同法律之间的区别被消除了。也就是说,那里有着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如果区别本身真的仍有效的话,那么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也有着合理的和不偏激的对话。需求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服从于集体决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社会里也会有冲突和矛盾、不同需求的实现之间的抵触;但是这些差异可以通过公开和公共的政治对话来解决。[^34]
聚焦于手段与目的之间、规范与法律之间的差异,以及需求的衍生本质和通过需求满足的可能性而产生的同意上,我们不可避免地构造了一幅非现实的社会的静态图景——一个游戏的隐喻迫使我们要超越的图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游戏的参与可能会破坏其再生产的条件。我已经说明了这些条件是什么,并指出了其可能发展出的危机。这样我们可以从游戏的隐喻中引出某种动力学,它促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下特定变化的意义。从而,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中工作组织的差异表明,限制越狭窄,选择的“数量”则越多。哈里·布雷弗曼考察了概念与执行之间的分离、对技能的剥夺,或是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广泛趋势而导致的决断力范围的变窄,但是,他遗漏了同样重要的并行趋势,即在更狭窄的范围下选择得以扩展的趋势。正是这后一种趋势构建了同意的基础,并使工作降级以使得在这一趋势的进行中不会延续危机。于是,我们看到了更可靠的机械、更轻松的产率、偷懒的可能性等等,全都增加了面向超额中的操作工开放的选择。这一趋势也更一般地表现在工作丰富化和工作轮换的方案中。如我们将在后面两章中将会看到的,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和内部国家的巩固尤其清楚地阐明了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下选择的扩展。
[^1]: “科学马克思主义”与阿尔都塞、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和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等法国结构主义者都是如此,而体现在卢卡奇(Georg Lukɑ́cs)、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著作中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然而,马克思主义最近在列文斐尔(Henri Lefebvre)、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蒂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及其他人的作品中,重新发现了“自发的主体性”,虽然马库塞很久以来就将这视为“虚假的主体性”,或者有保罗·皮科内(Paul Piccone)近来称之为“人造否定性”。
[^2]: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自由民主的社会团结”(“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1970): 423—439。
[^3]: 亨利·德·曼(Henri De Mann),《社会主义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 New York: Henry Holt, 1927),第 80—81 页,引自罗伊,“‘香蕉时间’:工作满意与非正式互动”(“’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1958),第 160 页。
[^4]: 威廉·巴尔达穆斯,《效率与努力》,第 53 页。
[^6]: 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 Whyte),《金钱与动机》(Money and Motiv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5),第 37 页。
[^7]: 同前注,第 38 页。
[^8]: 罗特利斯伯格(F. J. Roethlisberger)和迪克森(William Dickson),《管理与工人》(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第 457 页。
[^9]: 同前注,第 445 页。
[^10]: 霍曼斯(George Homans),《人类群体》(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第 155 页。
[^11]: 梅奥(Elton Mayo),《工业文明的人性问题》(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33),第 119—120 页。
[^12]: 克罗齐埃,“较量的结构与较量的游戏”(“Comparing Structure and Comparing Games”),收录于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Organization Theory,霍夫施泰德(G. Hofstede)和卡塞姆(M. Kassem)编(Amsterdam: Van Gorcum, 1976),第 193—207 页。也见于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
[^14]: 贾森·迪顿(Jason Ditton),“津贴,脏物与欺骗”(“Perks, Pilferage, and the Fiddle”), Theory and Society 4(1977):第 39—71 页,以及“道德恐怖对俗民恐怖:产量限制,阶级与剥削的社会组织化”(“Moral Horror versus Folk Terror: Output Restriction, Class,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Exploitation”), Sociological Review 24(1976),第 519—544 页。
[^15]: 斯坦利·马修森(Stanley Mathewson),《无组织工人的产量限制》(Restriction of Output Among Unorganized Worker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31),第二章。
[^16]: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虚伪的承诺: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False Promises: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3),第 38 页;埃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失落的天堂:汽车工业时代的没落》(Paradise Lost: The Decline of Auto-Industrial Ag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第四章。
[^17]: 克罗齐埃,《科层现象》,第 163 页。
[^18]: 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指出了英国工厂也有类似的工头与时效调查员之间的冲突。参见罗纳德·多尔的《英国的工厂——日本的工厂》(British Factory—Japanese Fac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第 93 页。在一次私人交流中,比尔·弗里兰德(Bill Friedland)表明工头与方法部之间的敌对,与美国汽车工业有相似的状况。
[^19]: 马库塞,《单向度的人》,第 5 页。
[^20]: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499—500 页。
[^21]: 同前注,第 511 页。
[^22]: 对内在于超额的价值的优势的更深入的洞察,在于与对某些不可能完成或难以完成的速率的持续抱怨相比,操作员很少抱怨最高工资水平或 140%的最高限度。正如罗伊所说:“对配额水平没有人表示不满;显而易见,大家接受工资限定。没有人抱怨每小时$1.25 不够;抱怨是由于配额收入日很稀少,这种收入比率只能偶尔获得。”(同前注,第 136 页)以这样的方式,将工作建构为超额游戏具有将注意力引向具体限度之内的变化,并将注意力从限度本身转移开去的效果。
[^24]: 彼得·布劳,《科层制的动力》,第 81 页。
[^25]: 例见詹姆斯·马奇和赫伯特·西蒙的《组织》(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8),第六章;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第六章;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的《行动中的组织》(Organizations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第一章;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
[^26]: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511—512 页。
[^27]: 或许可以下结论说,工作的差异越大,依照超额的容易性所作的划分越多,也就是说,车间所建立的等级制越强。1945 年时各机器间的容易比率并不广泛为人所知,但似乎比 1975 年低,这可能是 30 年前工人间较团结的另一个原因。
[^28]: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517—518 页。
[^29]: 这些术语来源于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第二部分,第三章。
[^30]: 聚集在这些点上同样可以表明有效的 crossbooking(作弊)的状况。
[^31]: 巴尔达穆斯,《效率与努力》;罗伊,“香蕉时间”;哈维·斯瓦多斯(Harvey Swados),《生产线上》(On the Line, Boston: Little, Brown, 1957)。
[^32]: 我在这里所使用的游戏(game)概念,与批判理论通常使用的玩耍(play)概念是相反的,它指的是“组织经验的一套规则,这是由自愿的、结果开放的(即免于内在与外在强迫)、非工具性的(指的是追求其本身的目的,旨趣的中心在于过程而非目标)以及超越了一般存在与意识状态的行动所构成的”。(弗朗西斯·赫恩[Francis Hearn],“关于游戏的批判理论”[“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Play”], Telos no. 3[Winter 1976—1977],第 145 页)对于马库塞来说,玩耍可以平衡工作:“玩耍表达了没有目标的自慰,满足了那些业已指向客观世界的构成本能。另一方面,工作满足了外在于自身的目的——即自我保存的目的。”(《爱欲与文明》,第 196 页)。在我的用法中,游戏比玩耍更接近于工作。
[^33]: 这里我所指的是哈贝马斯关于共识的政治形成、公共领域和未被扭曲的交往等概念。例见他的《理论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3)。
[^34]: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追随马克思的看法,倾向于认为在一个后革命社会或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不会存在政治。这是明显错误的。参见: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什么是社会主义?”(“What Is Socializ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 (Fall 1975),第 60—81 页;卡斯托里亚蒂斯,“匈牙利资源”(“The Hungarian Source”), Telos no. 29 (Fall 1976),第 4—22 页;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新鲜时代”(“The Age of Novelty”), Telos no. 29 (Fall 1976),第 23—3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