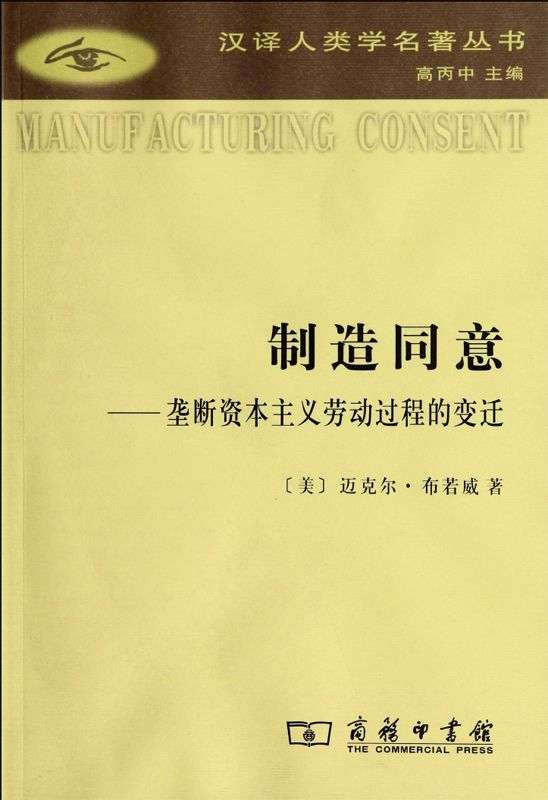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七章 巩固内部国家—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七章 巩固内部国家
在前面一章里,我考察了工业企业部分地吸收外部劳动市场的后果。现在我打算考察另一种内化过程的含义——“内部国家”(internal state)的成长。在对进步年代的描述中,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描绘了全国公民联盟(NCF)中的企业领导通过“超政治”(extrapolitical)的方式——即避免它们进入公共争论的领域——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1] 当时,这类“公共领域去政治化”的制度安排依然是简单的。从那时起,公司开始在它们自身的权限内,以集体讨价还价和申诉机制的形式确立政治过程,以此设法为它们诸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政治性阶级妥协的出现,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关系的再政治化”。^2 塞尔兹尼克(Selznick)则以一种稍微不同的路径切入,唤起了对产业内私人政府的兴起和工业公民的构成的关注。“由此可以得出,如果集体讨价还价‘创造’了一个政府体系的话,那么它是通过帮助重构管理过程而达成的。资方变得对权利更加有意识,更有能力使那种意识成为制度化生活例行程序的一部分。在这种重构过程中,对‘物’的管理变成了对人的治理。”[^3]
“内部国家”这个概念指的是一套在企业层面上,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虽然它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呈现了一种根本不同的形式,它绝不是一种新现象。在竞争资本主义之下,除了同业公会组织(craft organization)存在的地方外,调控生产中的关系主要是由专制的工头来执行。资方和工人的关系依照主仆关系法则。随着大企业和工团主义的兴起,内部国家的制度开始与资方对劳动过程的指令相脱离,并具体体现在申诉程序和集体讨价还价中。新兴的内部国家通过限制资方的任意决断,以及赋予工人权利与义务,保护了资方塑造和引导劳动过程的特权。
工会及其成员
内部国家从专制形式过渡到霸权形式依赖于劳动代表在产业政府中的有限参与。工会要从其成员那获得忠诚,必须足够强壮并对积极回应劳工,但其能力又不足以挑战资方在组织与控制劳动过程中的特权。自 1945 年以来的变化尽管微小却表明(如果有的话),工人对工会的支持更强有力,但工会对资方的挑战更微弱了。
正如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工会活动在战争期间缩减了。不罢工承诺夺走了工会最强有力的制裁手段,合同中的成员维持条款抑制了征募新兵的动力:
公司承认国家战争劳动委员会所发表的政府战时劳动政策,公司同意下述维持成员身份和代扣工会会费的条款。根据 1944 年 5 月 13 日的美国联合钢铁工人章程(复件见附录 1),从协定生效日起,协定覆盖的所有雇员都是遵守规章的工会成员。所有在那以后加入工会的雇员,作为雇用的条件,根据上述章程,在此协定有效期内应该保留会员身份。[Art.Ⅰ,sec.3]
不罢工、成员身份的保障以及代收工会会费的系统造成了一个被动的工会。罗伊知道没有夜班操作工会为工会说好话:
工会很少是支架车间谈话的主题,但它被提到的时候,评论表明工会不是为工人所尊重的一个组织。机械操作工对工会态度的特点是轻蔑:“所有工会能完成的事就是每月从你身上获得 1 美金。”[^4]
夜班没有工会干事,罗伊与白班的那个干事也很少有接触。在他待在吉尔的 11 个月里,罗伊与他仅有两次直接接触。在第一次情形中,干事希望他签署代扣工会会费的表格。在第二次情形中,罗伊想要抱怨他的一次操作的价格;操作被重新计时,但速率依然不可能达成。干事表示对此有兴趣,但他没做什么。
因为罗伊与工会联系不多,工会-资方关系的变化难以测定。虽然就此事他没有给我们提供确切的数据,他的观察还是表明了工会在车间的干事很少。现在合同有了一些变化,并且这影响了工会与资方的关系。参与工会制度被引进,所以一旦试用期满之后工会成员身份就是雇用的条件。纪律程序被合理化了,从而包括了在工人被解雇之前必须采取的一系列步骤。除了第一个步骤(口头警告)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通知工会并使之进入到纪律程序中。最后,管理条款中现在加进了一条限定条款;规定公司“在采取任何会对雇员的工作和工资保障有直接和负面影响的主要行动之前会告知工会”。
虽然这样,普通雇员的态度和 1945 年时差不多。他们普遍怀疑工会干部保护成员利益的意愿和能力。部分原因在于工会领导在其日常活动中行使了非常之少的可见 权力,而且极少代表成员发起干预。然而工会的角色是保持现状,并且它的权力通常是不可见的 ——用于防止资方的专断行为。尽管如此,这一权力却是重要的。工会的存在担当着制止资方违反合同的任务。从而,在资方“公平游戏”的程度上,工会看起来没做什么事。的确,只要协助工会保护其合法性和与资方面对时的自主性外观的话,时常违反合同也是有利于资方的。虽然工会的无能、中饱私囊、贪污、与公司勾结等等已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是,工会领导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合法性,必须将其表述为独立的。资方意识到它对一个可与之讨价还价的合法工会的需要,从而接受了它对其任意决定的适当限制。
与那些不属于工会的车间相比,突出了工会存在的重要性。前者没有申诉机制限制,也更加专断地对工人使用惩罚制裁。罗伊的一个受访者证实了这一点:
和我打交道的那个人先前在吉尔担任检验员。我注意到当我说我为吉尔干活时他没说什么而是保持沉默。我说:“我猜吉尔名声不好。”他说道:“在工会进入之前,他们没有公平地对待工人。工人 7 点上班,在那空等材料,等到 9 点钟,如果没有材料的话又被赶回家,其间的等待没有任何报酬。他们根本没有尊重工人。”[^5]
1975 年的联合公司,一种行为与态度之间明确不一致显示了部分工人持续的矛盾情感。一方面,连续不断地抱怨工会一文不值、官员贪污腐败、只擅长收会费花会费(会费在 1975 年的时候总计每个工人每个月约为 10 美金,这根据工人收入而交)。另一方面,一旦工人要申诉,比如说觉得资方在欺骗他们、别的操作工危及他们的岗位以及诸如此类的时候,他们的第一行动就是找工会。此外,工会被当作对任何冒犯者的威胁。一次当我在干别人的活时我被警告:“我会让工会找你。”——这表明工会并不是像有些评论可能会说的那样没什么用。对工会的抱怨看上去指向了在工会任职的个体 而不是作为制度的工会,它通常保障工人免于受资方的侵蚀而不顾现任领导。
创造工业公民
内部国家下的日常生活将劳动者作为有合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对一个更加含糊的“社会契约”有所承诺的工业公民插入进了政治过程当中。这种对企业的承诺有其物质表述:首先,对资历的回报,诸如养老金计划、补充失业福利、资历优先权(bumping rights)等等;其次,申诉机制,这旨在保证平等对待和“产业公正”。工会在保护工业公民的权利,以及在监督惩处违反合同义务的冒犯者中担当着仲裁人的角色。
你知道,我们认为工会是在产业领域推进民主进程的努力;在一个既定社会的框架内,组成社会的人们必须制定规则和条例来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社会就是基于这一原则的。[^6]
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工会每个月举行的会议点缀着吉姆——主席——的评论:“我们[原文如此]最大的问题是旷工”或者“我为你们骄傲,旷工只是 12 月的一半”。[^7](实际上,一个主要原因是失业率翻了一番。)在与普通成员的日常交往中,工会领导扮演一个个体化的角色。工会成员与工会干部——尤其是吉姆——之间最集中的互动是地方工会月度会议讨论申诉——曾经、未曾或正在处理的过程中的申诉。工会的努力,或更确切地说没有努力去保障某成员的权益,都会引起怒火。会议变成一个宣泄在车间积累的挫败感的安全阀,至少对于 6%到 9%的参与成员来说是如此。每当有影响全体成员或某一部门成员的集体 申诉,或是一个合同原则之外的议题被提出来时,吉姆总是坚持己见:“你要申诉吗?如果有说出来让我们听到。如果没有,把发言权给别人。”每一案子都是以个体为基础处理,根据神圣契约所写下的产业政府的规则来处理。
工人对某些工会干事或其他工会干部的抱怨,围绕着他们解决申诉时是否有歧视对待的问题。从而,最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议题关注的是工会人员的种族偏见。(三分之一以上的工会成员是黑人,但整个干部队伍都是白人。)换句话说,对工会干事、申诉处理者等人的例行的、有时相当深思熟虑的甚至激烈的谴责,只是强化了产业政府的规范姿态,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法律”所效力的利益从未被探究,更别说是质疑了。
利益的具体协调
在他们的日常行为中,工会干部仲裁并执行体现在合同以及像超额这样的惯例中的规则。他们保护规则的热情部分来自于他们每三年一次地商讨是否改变规则。在罗伊那时,新合同的制定或延续几乎每年都要协商。现在,在多数产业里,三年制合同已经牢固地制度化了。
集体讨价还价,一方面在车间的不同行动者之间转移冲突,那些冲突可以导致工作中断;另一方面,在协商框架内重构冲突。透过这种冲突的重组方式,集体讨价还价在工会与公司之间产生了 基于企业兴衰存亡之上的一种共同利益。[^8] 集体讨价还价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在其中工人被表述为一个与资本家相对的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形式里,阶级斗争围绕着边缘性变化的问题,这些变化对劳资关系的实质特性没有影响。与之相反,作为协商边缘性变化的结果,所有权与控制的资本主义关系变成了同意的对象。换句话说,集体讨价还价可以被视为另外一种游戏——这次是关于其他游戏的规则和结果的游戏,例如超额游戏。与往常一样,限定集体讨价还价规则的环境——作为游戏的结果——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违背集体讨价还价的既定规则,或者未能达成相互协商一致,可能会导致罢工或更高层出面强制仲裁。在集体讨价还价失败的特殊产业和企业,资本主义关系或许会被质疑,但在这些受到影响的产业和企业之外,协商破裂很可能会强化 对集体讨价还价的热衷,以及在公司兴衰存亡中的共同利益。我遇到一个有着胆怯与合作精神的地方工会的主要领导,他提到了街对面的科格(Cog)公司的例子。“几年前与工会的谈判破裂并有了一场罢工。后来公司关闭搬到了南方。大批人试图加入联合公司。”这并不是要说,强制执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协定本身不能把公司推向破产。这是可能的,因为工资承诺先于利润保证。但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不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组织原则的拒绝,而是来自于特定企业没有能力生产充足的产品,以此来满足资本与劳动的分配需求。于是,集体讨价还价象征着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代表之间,也就是资方与工会之间,共同利益的一种制度性产物,但这依赖于一种物质的先决条件——利润的增长。^9
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内部国家的兴起具有工人与资方都服从于非人化的法律规则的特点。此外,法律假设自身具有自主性,因为它只能以合乎规定的、非专制的方式被改变——最为通常的是集体讨价还价和联合控制。塞尔兹尼克描绘了雇佣关系从“特权合同”(prerogative contract)——如果有的话,根据这一合同,资方消费出售的劳动力较少受到禁止或限定——演变到“构成性合同”(constitutive contract)与“创造性的仲裁”(creative arbitration),这二者的确建立了利用劳动力的程序与规章。^10 对管理的任意决定与专断规则的限制以及对工人保护的增强,这两方面不仅反映了工会与内部 政府的上升,也反映了外部 政府机构的间接管制。这显现在“(1)利用政府采购在与公共机构签订合同的产业身上强加标准以及(2)管制作为主要指向其他问题——如公民权或对影响到公共利益的产业的控制——的立法与管理政策的副产品而发展”。[^11] 产业政府很少受到外部干预或控制的威胁,成为公共政策私人化的承担者。“因此,公共政策较少通过管制的积累而发展,而是更多通过政党调用公共目的的权威来支持新要求和权利主张的过程来发展。”[^12]
塞尔兹尼克证明的正是内部国家的相对自由,首先免于外部公共实体的干预,其次是免于资本家或经理的直接经济利益的过分要求。在下面的几章中我们会更多地说一些关于单个的企业与外部实体的关系。在此只要提一点就足够了:塞尔兹尼克的分析在联合公司的积极性行动计划中得到了体现。经理提交年度计划,为公司劳动力构成的种族和性别比例设定目标,然后交给政府获得批准。换句话说,外界机构并不介入和指导联合公司关于黑人、妇女等等的精确比例;他们履行更加消极的批准和限制的功能。
相对自主性的第二个领域对于本章的论述更为重要。在此,内部国家在三个相关意义上具有相对自主性。第一,它使资方和工人都要服从合同所写的规则规章。自主性从而是相对的,因为内部国家通过防范资方自身专断干预的倾向,这一专断干预会破坏生产之际形成的同意,从而确保生产中的关系的再生产。相对自主性在这一意义上是赢得和掩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自主性。第二,内部国家的自主性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它只有在剩余价值被掩饰和赢得的时候才存在。危机的到来会威胁到这种自主性,工人又变得屈从于资方专断任意的决定。第三,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表达了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通过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与权利的工会而组织)环境中资方的制度化力量。此外,合同的协商意味着工会也是相对自主的,也就是说,在积累要求所限定范围内的自主。只要把工会合法化为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那么拥护工会领导的相对自主是符合公司利益的。也就是说,公司与工会领导之间的协议保障了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只要没有可见的、通常与工会领导人为自肥而与顾主私下签订对工人不利的合同相联系的一类“勾结”。尽管“勾结”有时会采取一些更微妙的形式,例如这个高级资历条款:
发生解雇事件时,如果只出于解雇目的,工会干部……应该被视为比任何其他雇员具有更多资历……[Art.Ⅳ,sec.10]
我在联合公司工作的初期,合同协商的结果被公布了,工会的合法性被临时削弱了。新的集体协议包括一个更慷慨的养老金计划,这是劳动者最重要的胜利。一般员工嘲弄说大多数工会干部都快退休了。员工们在我面前表达的情绪几乎完全反对新的提议。的确,与我交谈的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将会投票反对。我问比尔他如何投票。他回答道:“他们提供更多的养老金,但那对我没用;我还有 15 年要干。我们都会投否决票。”我又问那工资增长情况怎么样。“百分之五,那是我们所能到的全部。没什么了不起。工会干部会接受但我们不会……他们会接受较多的养老金——这适合他们。”然而,奇怪的是,工会干部最终宣称其成员以 408 票对 307 票之差支持新合同。
资方无疑意识到养老金增加对工会干部有吸引力,他们知道一般员工不满意得到一个廉价合同,但仍觉得这值得一试。从我与人事主管的讨论中可以得知,资方看上去意识到了保障工会相对自主性以及响应其成员的重要性;例如,他就关注到了工会执行委员会中缺乏黑人代表。他知道只要协商的条款可以最低限度地被一般员工接受的话,工会的日常管辖功能就可以在每三年签订一次的合同期内有效地执行。
未能达成一个可接受的合同会削弱工会保持现状的能力,同样也可能导致在每三年举行一次的选举中推翻现任干部,尤其是主席。由于干部通常希望保留他们的位子,选举机制就是维护工会相对于资方的领导自主性的一种方式,尽管它不是如人们所想象那样的一种有效机制。但是选举具有更加重要的后果,即在成员中间形成一种观点:劳动者获利较少的糟糕合同是现任领导的错误,而非工会结构及其与公司的关系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地方工会层面上,只要有替换干部的有效选举机制,在工会政治中是否有一党体系或两党体系无关紧要;[^13] 因为选举机制有效地掩盖并保护了资方-工会关系的结构背景。工会相对自主性作为一种制度受到了持续的保障,即使是在面临——并且,有的时候的确是因为——其领导阶层的脆弱性时。在联合公司引擎分部,分会主席的位子一段时间以来在两个资深操作员之间轮转。对工会的不满通常指向这些人中的一个或另一个。一些更有资历的雇员偶尔会提到以前的主席,“实实在在为大伙斗争”的主席(前任主席因此调到了国际工会中一个较高的位置)。其他一些人会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工会的年轻血液。”
产业政府面对狭隘的资本经济利益以及外界干预的相对独立性,有助于掩饰集体讨价还价和“产业公正”分配所保护的财产关系。^14 进一步讲,当自主性被削弱的时候,所揭示出来的乃是人性的缺点而非财产关系。人性的缺点并不被视为一套结构性条件的后果,而是被当做既定的——人性的一部分。
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起着相似的作用。从而,在这一章我们看到,内部国家如何在其相对自主的形式中,通过联合使用申诉机制和集体讨价还价,具体地调整了工会与资方的利益。它具体地调整了利润扩张中工人与企业的利益,做出了以雇员福利和工资增长为形式的物质让步。通过将工人当作个体——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它掩饰了劳动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后,关于生产中的关系的斗争被申诉程序所调控并被转移到集体讨价还价中。[^15]
另一方面,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市场在生产同意中发挥着互补的功能。在本章和之前的两章里,我提出劳动过程的变化以及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扩展了工人的选择,并从而构成了同意的基础。然而,只有资方不专断地命令工人做出选择时,同意才会出现——例如,如果调动总是工人主动提出并且通过竞标过程实现,或者,惩罚性制裁只能针对逾越选择权限的行为,例如当工人决定留在家中而不是去工厂上班时。此外,当界定选择范围的规则未被违反时,强制力量的使用变成了同意的对象。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保证了强制在调控生产中会扮演一个更有限的角色。[^16]
然而,在内部国家的组织中却有明显的含混性。正因为它调整了工人与经理的利益、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它也承认那些利益是潜在地对抗的,例如在工人要求增加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时。与不承认其结构中有阶级存在的总体国家(global state)不一样,内部国家明确承认阶级,从而变得更易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至少潜在的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什么可以在合同中谈判出现了很多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自那时以来已经透过确立资方指导劳动过程的特权的各种方式解决了。不论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什么,结果是相对清楚的。
从而,我在第三章表明,1945 年到 1975 年期间,强力的使用渐渐被限制在违反了界定同意的扩展领域的规则的行为上。据此,我认为企业通过组织、转移和压制斗争、通过把公司的利益建构和表达成所有人的利益,以及通过促进个体主义掩饰并赢得了剩余价值。我也假设,可以独立于总体国家、市场和劳动力再生产等这些外部因素来考察如何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的过程。这些因素现在不能再被忽视,本研究接下来将会探讨对它们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形式、再生产以及变迁的关系。
[^1]: 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司理念 1900—1918》(The Corporate Ideal in the Liberal State: 1900—1918,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3]: 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法律、社会与工业公正》(Law, Society, and Industrial Justi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9),第 154 页。
[^4]: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434 页。
[^5]: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438—439 页。
[^6]: 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个体主义对工会主义”(“Individualism vs. Unionism”),收录于 Source Book on Labor,尼尔·张伯伦(Neil Chamberlain)编(New York: McGraw-Hill, 1958),第 144 页。
[^7]: 不幸的是,罗伊从未参加过 1944 年至 1945 年间的任何工会会议。从而难以估计工会领导层是否在其与资方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或多或少有点战斗性的角色。当然,我们也难以设想早年的工会主席会把旷工当做一个“工会”的问题。
[^8]: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把这种情形概括为“资本家的利润等于工人的积蓄”,对此,他指的是工人通过“同意”工资的有限增长来保证他们未来几个月或几年的就业。也就是说,今天的工资限制允许利润的积累从而明天增长了的工资得以可能。透过这种方式,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实际地调和了起来。普热沃尔斯基,“资本主义民主与朝向社会主义的转变”(“Capitalist Democracy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未出版论文,1978)。
[^11]: 同前注,第 215 页。
[^12]: 同前注,第 229 页。这自然是放任政策的产物,在此情形下,强大的工会设法保护其成员,而弱小的工会和无组织的工人却一事难成。
[^13]: 从而,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马丁·特罗(Martin Trow),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他们关于国际印刷工人工会(ITU)的研究中所描绘的两党体系,是更宽广的社会中政治组织的两党体系的类似物。在某些方面,它以与政党体系孕育全局政治的同意相同的方式孕育了同意。与此同时,对矿工、港口工人以及 ITU 的研究表明了地方自主在工业政府的“民主”实践的出现和维护中的重要性。工会的两党体系并非生产场所这些民主形式的起因,与之相反,却是其结果。(西摩·马丁·利普赛特等编,《工会民主》[Union Democracy , Glencoe: Free Press, 1956])
[^15]: 本章强调的是科层制作为一种支配形式的意涵。传统上,工业社会学趋向于从这一点出发,可能在韦伯的作品中更加盛行,其中,科层制被视为“技术上优于其他任何组织形式”。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3vol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3: 973。从而,工业科层制被或多或少地视为组织化生产的有效方式。例如,参见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第八章;彼得·布劳的《科层制的动力》;塞尔兹尼克的《田纳西河谷管理委员会和草根性》(TVA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与此相反,古尔德纳和克罗齐埃意识到了韦伯的科层观点中的另一条线,说明了规则如何减弱了工人与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见古尔德纳的《工业科层制的模式》和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克罗齐埃把支配视为工业工作中不可避免的特质,古尔德纳则质疑这种不可避免性;但这两种观点都与内部国家中所隐含的说法不同,其中,支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产物。
[^16]: 强制与同意的双重视角贯穿于葛兰西关于支配与霸权、暴力与文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形式的作品当中。他关于两种面向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既是发展尚不充分也是具有启示性的:“就真正的事实而言,常常出现的情形是,第一种‘面向’越直接、越根本,则第二种面向越‘疏远’(不是指时间,而是指辩证关系)、越复杂、越野心勃勃。”在另一段文章中,葛兰西写道:
霸权在当前议会体制的传统领域的“正常”实践,具有结合强制与同意的特征,这可达成一种互惠式的均衡,无需强制绝对地支配同意。的确,努力总是用于确保强制基于多数人的同意,由所谓公意机构——报纸和协会——表达出来,因而,它们在特定的情形下是被人为操纵的。[《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第 170 页,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