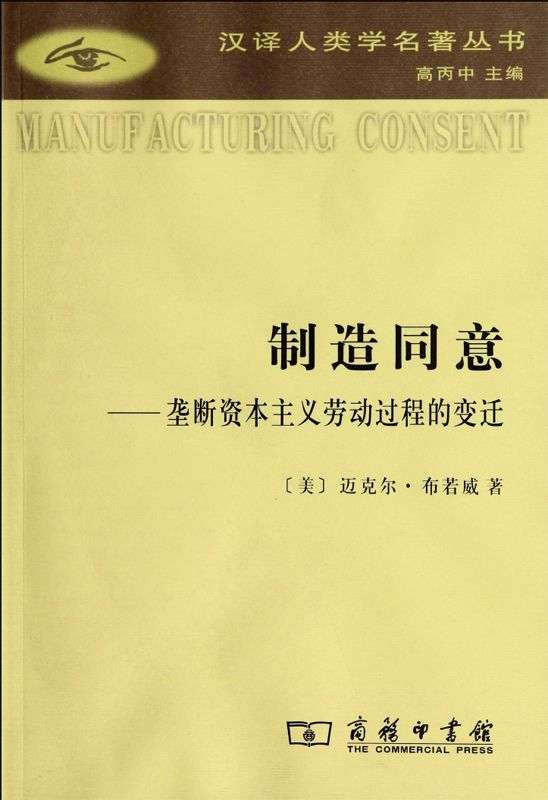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九章 劳动过程与工人意识—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九章 劳动过程与工人意识
马克思将劳动力(labor power)定义为劳动过程中脑力及体力的结合。这些能力具有客观性。脑力是指习得的技能,并不指诸如工作的意愿等主观倾向。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样的主观倾向与去工作及劳动力的消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的。强制力在形成人类行为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第三部分我指出,当工资开始与个人的劳动力支出无关时,同意的组织也开始越来越重要。我也提出,无论同意对于剩余价值的掩饰及赢得是否必要,同意是在生产之际产生的,而不是从外界进入工厂里的。这一立场挑战了传统观点——认为来自于家庭、学校、教堂等的态度、信念及理论——简而言之,意识——形塑了劳动过程中的关系及行动。奇怪的是,早期工业社会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工人们带到工厂的“价值”或“倾向”。工业行为在极大程度上被认定与来自外部的意识无关,或者至少它是未经考察的既定之物。在这一章里,我将要探讨,在这一问题上,工业社会学家并不像他们同时代的批评家们所宣称的那样错在其假设上,而仅仅是未能说明为什么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他们没阐述为什么 外部产生的意识没有对劳动过程产生显著的影响;他们轻易地忽略了这一问题。
来自外部的工作倾向
过去这些“封闭系统”的研究在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及他的同事的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受到了最深刻的批评。[^1] 为了强调“工作倾向”的重要性,戈德索普等人试图对工业社会学的两个主要学派——人际关系学派(“新人际关系”)与“技术决定论”及社会技术系统学派——中建立一个修正物。对于前者,他们反对这样的一个观点:工人并不以工作来满足社会需求,工作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即应付外部所担负责任的一项收入来源。对于后者,他们反对这一论点:外来的工作倾向决定了技术及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总结道: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任何 解释及理解现代工业里的态度及行为的尝试,至少必须认可这一可能性,即有必要把受雇用者共同持有的工作倾向看做是与工厂内环境相关的一个重要的自 变量……因此,对于解释及理解企业中的社会生活最终要参考企业生存其中的更广大的社会结构及过程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必要性——被唤起了,这种可能性在我们所考虑的其他途径中并不存在。[^2]
他们认为,将生产中的关系转化为行为方式是通过工人们从家里带到工厂并在那里激活的倾向进行调和的。
他们的研究提出了四类问题及其答案。第一,所谓的工具性取向是来自工作之外的生活,还是来自工厂里?第二,与前一问题相关,这个工具性取向在增加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第三,人们可以通过分析态度来考察工业行为吗?第四,态度的差异性有什么意义?我应该按顺序处理每一个问题。声称工具性取向的研究者认为工作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它不是工厂的产物,而是来自地理及社会的流动,尤其是对他们所研究的卢顿地区(Luton)工人而言。[^3] 然而,工人中工具性的差异似乎与社会及地理流动相关性较小,而与工作类型相关性较大。[^4] 此外,由多罗西·韦德伯恩(Dorothy Wedderburn)及罗斯玛丽·克朗普顿(Rosemary Crompton)所做的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生活经历与卢顿地区工人迥然不同的工人也同样有“工具性”取向的劳动力特征。[^5] 他们的研究提示了由戈德索普等人评估的取向并不是从某种特定的会生活类型中形成的。正如戈德索普他们自己所承认的,在证实他们的假设时,问题之一是他们所有的对比限定在一个单一的工人样本中。韦德伯恩及克朗普顿的结论同那些早期的研究的冲突点在于,他们强调了技术约束工人行为的重要性。
第二,戈德索普等人声称工人的工具性取向是近年来都市社会变迁的产物,因而它很可能在未来显得更加典型。他们的论点预设了所谓为工作而工作的“传统”工人的存在。但是,除非他们能够证实所谓传统工人的确存在或曾经存在,并且对工作没有显示出工具性取向,否则他们的结论是不值一提的。[^6] 此外,他们并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工具性在过去是更重要了还是不太重要了。在撒旦磨房里的工人若不是工具性取向的,那么受雇的目的是什么呢?事实上,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和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等历史学家的看法正好相反:福利国家的问题是寻找一种 19 世纪经济鞭笞的替代品。[^7] 戈德索普等人沉溺于拿 20 世纪中期工人的态度与早期资本主义工人的刻板印象做一个错误的对比。但是,即使我们同意戈德索普等人所认为的工具性、个人主义以及市场倾向在日益增加,它们既可能来自于都市生活的变迁,也可能是劳动过程的变化所造成的。戈德索普等人不仅对他们所假定的趋势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他们似乎也武断地排除了这样的趋势来源于工业环境本身的可能性。
或许,他们的研究中最明显的缺陷是未能提供有关工人实际行动的任何数据——也就是工业行为的数据,这是我要说的第三点。相反,他们完全依赖于对工人态度的调查。当他们与前后关系脱离的时候,怎么能够对所列举的一系列态度进行解释呢?这些态度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呢?他们似乎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待工作的一般态度,即人们不愿参与无意义的、枯燥的以及强制性的例行公事。他们不可避免地错过工人们为弥补他们所受剥削而做的适应性的改变。只要知道工厂是如何运作的人都会明白,戈德索普等人所衡量的内容与车间里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甚至工作当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也不必然对应于那里的行为。因此,正如我将在下一部分显示的,正是关于种族敌意的表现削弱了一种看法,即种族作为互动的一个重要范畴。罗伊的观察更加中肯,我自己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即,当工人们用赚钱——金钱关系——的“俗语”来形容超额时,他们的行为实际反映了一种生产之际组织的并且独立于外界取向的一种特殊“文化”。我毫不怀疑的是,如果戈德索普等人对联合公司及吉尔公司的工人进行过访谈的话——尽管两者具有非常不同的背景——他们也会发现同样的工具性倾向;然而,联合公司及吉尔公司的工业行为实际上都是对不同的 意识形态的一致反映。简而言之,工人们表达及合理化其行为的俗语并不必然指涉他们的实际行为模式。
最后,经过严格检验,戈德索普等人提供的表格上显示,偏离工具性规范的百分率出乎意外地高。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呢?他们反映了不同类型的工人、不同的意识水平,对其环境的一个矛盾的态度吗,或者是不同的工人撷取其经历中的不同要素来作答?迈克尔·曼假设了双重意识的概念来解释工人们所持的明显矛盾的观点。[^8] 这个概念可能对于展开解释卢顿地区工人的回应的变化是有益的。在一篇对卢顿研究的批评里,约翰·维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提出差异性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戈德索普等人遮蔽了的潜在的阶级激进主义。[^9] 此外,他显示了态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显著变化。维斯特加德还叙述了在戈德索普的访问结束后,沃克斯尔·莫托斯(Vauxhall Motors)的那些被研究的工人是如何进行了一场罢工的。维斯特加德评论道:“那种‘金钱关系’可能崩溃,正因为它仅仅 是金钱关系——它是孤立无援的;而且,如果它确实崩溃了,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迫使工人接受他们的处境。”[^10] 他总结道,“然而,‘现金取向’孤立无援的特点意味着工人的投入及其取向上潜在的不稳定性,而这在卢顿研究的解释中实质上是被忽略了的。”^11
维斯特加德的批评凸现了卢顿研究中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没有能够区分去工作(coming to work)与干活(work)——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交付(the delivery of labor power)与劳动力转化为劳动之间的区别。现金关系对于将工人引进工厂大门是一个必需因素,但即使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将现金关系呈现为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的。但是,工具或现金取向在劳动过程中并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即使是在货币回报与个人产量直接相关计件工资体系中。
在此做个结论:在修正工业行为研究的人际关系学派及社会技术系统学派这两条进路当中,戈德索普等人倾向于将两者分开来,而任务却要求将它们结合。由于劳动过程不外是“人的”,工人与资方在运用特殊的技术工具将原材料转换为产品的过程中进入了这种关系。罗特利斯伯格和迪克森(Dickson)将这一点理解得很透彻。在对霍索恩试验的解释中,他们认为并不是工作条件的改善——比如,通过改善温度,照明,通风等细节的方式——来获得产量的增加,而是改善被体验的方式,或者如葛兰西可能会说的,它们被意识形态所调和的方式。那么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是什么,它来自什么地方?它出现在生产之际?还是来自外部?这是重新阐述戈德索普等人最初的问题,他们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将劳动力的交付和转化区分开;因为他们不能区分来自工厂里以及来自外部的“取向”;还因为他们没有对工业行为进行任何估量。在这一章中,我将试图对外部引入的意识是否介入到生产中的关系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考察。但是,首先很有必要调查生产中的关系自身如何被工人们带进工厂的意识所影响。
生产之际的种族关系
为了判断生产中的关系是否独立于人们从外部带到工厂来的意识,有必要对那些外部意识进行测量。我将验证假设:工作之外的不同角色,造就了不同的经验,因而有了不同的意识。然而,在我自己的观察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外部角色都可以在工厂中辨别出来。当然,区分出不同的年龄组,性别及种族是不太费力的。尽管性别在生产中的关系的形成当中肯定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在零件部门仅有两名妇女在第二班次里,这使得我们不能够得出任何结论。第二个变量——年龄——与其他诸如家庭规模、资历这些决定职位的变量有很高的相关关系。种族是唯一的可以为区分不同意识提供基础的变量,并包括了厂内的不同职位。
有一两个关于种族差异对工作组织的影响的研究。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给出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一个占优势的白人组可以控制一个新的黑人组,强迫后者进入从属的、边缘的位置,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迫使他们辞职。同时他也指出,管理政策可能对黑人的工作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工业管理的个人主义或“下层阶级”假设——每个工人都是一个可能被诱导的个人,并且是一个应该能够为了自身的目的被引导来工作,而不必顾及其伙伴的个人——几乎在不知不觉中以两倍的力量强加在黑人工人身上。这种假设所鼓励的行为本质上是野心勃勃者的行为。白种工人的野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他抛开其伙伴,尽管这有点让人讨厌但他可能会因此而得到升迁。黑人工人明显地感觉到,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别人刻意让他们感觉到,他必须将自己与其他人分开并且成为一个“孤独者”,这仅仅是为了保住他的工作。[^12]
换句话说,并不是作为黑人本身,而是工作组织的某种种族偏见造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如果车间里没有再生产种族关系的正式管理机制,会发生什么呢?威廉·科恩布卢姆(William Kornblum)在对南芝加哥的一家钢铁工厂及其所在社区的研究中写道,“资历及技术是分配工作的主要标准,工人们终其一生在工厂里制造零件,往往超越了种族、信仰、地域团体等的区分,而这些因素在外部的社区生活里就可能把人区分开。”[^13] 他的观察显示,在钢铁厂,超越了种族与族群界限的联合是很自然的,正如在外部社会中这种结合是不自然的一样。
联合公司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以人种、年龄及共同的志趣(比如信仰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小圈子在非正式的情况下显得更加重要。不论是在第一班还是在第二班,种族是午休联盟最重要的基础。在第一班,午休联盟第二重要的标准是资历,之后是部门,然后是工作。在第二班,受雇用者相对来说是新进的员工,因此在形塑非正式的联系中,资历与部门和工作相比就不太重要。在工作间隙闲聊或喝点什么提供了非正式互动的场合,这常常是跨越了种族界线的。在车间里,工友常常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工作的人,联合的确立往往以设定程序等时候的相互协助为基础。这种互动再次跨越了种族界限,并延伸到一块儿到自动售货机那儿买饮料喝。
尽管有每天的合作,或者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种族及族群偏见依然是车间生活的口头禅。有的时候,操作工、辅助工及工头可能私下说一些诋毁种族或族群的话;下一分钟他们可能很乐意于帮助刚被他们骂过的种族或是族群的人(可能伴随着嘲弄、善意的戏谑),就像是帮助他们自己群体内的人一样。因此,态度 或偏见是从都市环境中引入的,比如住房及教育,不断地再生产“种族关系”,但在工厂里的行为 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种族区分的影响。
在这个环节中,通过使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分离得以发生,甚至再生产这种分离,戏谑关系呈现出了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拉德克利夫 - 布朗(Radcliffe-Brown)描述的这种戏谑关系:
社会分裂(social disjunction)暗示了利益的分化及随之而来的冲突及敌意产生的可能性,然而社会聚合要求避免斗争。融合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才可获得一个稳定、有序的形式?有两种方法可以实现。一种方法是,维持两人关系的高度相互尊重,并且限制两人的直接接触……替代这种高度尊重及约束的另一种方法是戏谑关系,这是一种相互不尊重及没有规矩的关系。用开玩笑般的对立嘲弄来防止任何严重的敌对与攻击,当这种关系反复出现时,常常意味着或者是提醒我们社会分裂是这种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而社会聚合的维持是靠面对冒犯时也不生气的友善态度。[^14]
在不同种族之间是持续的而不是间断的接触的地方,他们彼此之间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冒犯对方,这种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他们有继续合作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认识到在其他情况下,种族间的敌对是一种常态。因而,戏谑的关系是一个证据,它证明了种族差异与生产活动无关。并且,戏谑关系的环境及方向是基于参与者在车间“地位”系统中的相对位置,而不是基于外部社会关系。为了指明工作情境是如何决定种族间的关系,以及戏谑关系是如何将工作情境及其“文化”与外部社会关系隔绝开来,我现在将简短地讨论我自己与一些黑人员工之间的关系。
比尔,一个身体结实,大约 50 岁的黑人,负责带我干些杂活。我在第一班接受了三周的培训。然后在第二班得到了一个固定职位。因为比尔会加班两小时,我们的轮班重叠了,所以即使在我开始了第二班的工作后,我还不断地跟他接触。比尔干杂活的时间已经有 10 年了(当他第一次告诉我时,我肯定自己是听错了;但是对他及他的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才开始明白他为什么会忍受这种非常不愉快的工作而不去换个愉快些的活)。在车间里,比尔实际上是唯一知道车间一切相关工作的人。他已经培训了很多操作者,但是由于这份工作又脏又累,没人愿意在这里留下超过几个月。刚开始他对我保持谨慎的距离,只教给我一些勉强能够应付工作所需要知道的事情。他不断地报怨我笨手笨脚、动作又慢,并且说我永远也赶不上我应有的速度。“老兄,在这个工作中你没时间胡闹,你必须工作。”在早期的阶段中,我对维持生活并保住工作更感兴趣,而不是超额。在我们的关系缓和一些之后,我对这份工作更加适应了,他开始教给我一些超额的方法。比尔也开始在向别人介绍我时,称我为“我的英国佬”。我的 种族身份会唤起敌意,但被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忽视了,就像是与当前的环境无关。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中,我却不能忽视他的 种族身份。直到再后来,当我俩已经建立了更稳固的关系后,我尽力帮助他,掩饰他的错误,看管他的工具,并且最终与他分享小金库后,我才敢叫他“城市佬”。也就是,当我在工作上不再需要他的建议与帮助之后,这种对称的 戏谑关系才出现。
几个月之后,另外一个第一班的黑人操作工——霍华德,又培训我钻孔。尽管我也常常在第二班里钻孔,我从未与霍华德建立起如同和比尔般由衷的关系。他一直轻视我,要不是因为我笨手笨脚(对这机器我有恐惧心理,有两次由于我没能迅速移开齿轮,钻孔刀被拱向上,断成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差点弄死我),要不就是因为我占去了他的加班时间,或者两种原因皆有。他利用 种族来建立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敌意并非基于种族敌视——这不过是习语罢了;相反,敌意来自我们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霍华德与其他第一班白人操作工普遍友好的关系证明了我的这一结论。
与霍华德断断续续的交往是以潜在的敌意为基础。而我与第一班的黑人起重机操作工黎瑞之间断断续续的来往则是基于相互之间的尊重。黎瑞总是加班,他每周会有两三次在回家之前帮我准备好电锯用的材料。在那种时候,我们会说起政治及经济的话题。他会对我说,我们是如何的渺小,而那些大人物是如何统治世界并拥有权力。而我会对他说社会主义,谈资本主义的注定灭亡以及经济萧条是如何逼近了。我和霍华德的关系与和黎瑞的相比,关系上的不同形式是源自生产过程的不同地位。
不论是对称或是不对称的,戏谑关系的建立至少应该基于最小限度的信任之上。它们也被一种特定的情景界定,并被限定在其内。没有最低水平的亲近感,或是在不恰当的环境中,一个意在开玩笑的行为可以很快转变成敌意,有时候还能转化成暴力。正如有一次一个管理员冒犯了与他不熟的黑人,就差点儿打起来。直到有新的环境建立起来之前,外部环境衍生的敌意会依然延续下来,两个种族之间只有最低限度的合作。我与另外几个与我同班的年轻黑人之间较少出现戏谑关系,我可以同他们讨论,甚至是争吵,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没有直接的联系。与这样的黑人在一起,我们的关系的实质 就是由我们在外面的角色——我的身份是一个打工的白人学生,他们的身份是在一个种族歧视社会里的黑人工人——来决定的。当无法消除的种族敌意持续存在时,我们关系的形式 是由我们在车间里相似的位置来决定的。很快地,他们忘怀了我是一个白人;用他们的话说,我只是“凑合”罢了。但是我和他们一起去喝酒只有一次;换句话说,我只有在车间里才是“凑合”。^15
总而言之:戏谑关系承认:(1)各种族间的种族偏见及日常合作的共存,(2)工作时利益趋同,而工作之外则利益趋散。戏谑关系的方向及内容都反映了生产关系的结构,但没反映都市社区中敌对的种族关系。外来意识存在于戏谑关系中,但仅仅作为一种习惯用语,所表达的依然是没有改变的生产关系。^16 如果带入工厂的意识没有影响生产中的关系的话,它是否介入这些关系转换为行动的过程中呢?
意识与劳动力转化为劳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对机器厂房的早期研究指出,社会背景在决定产量时具有重要性。^17 因此,多尔顿(Dalton)这样刻画破坏工作速率者(the rate-buster):
与工作组的其他成员相比,来自一个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或者,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正努力达到这种地位……成为一个名义上的新教徒,……成为一个有英国血统的美国人或是来自西北欧的移民,……成为一个共和党人并且……阅读保守派的报纸……。成为一个顾家的男人,[所有这些]再加上普遍地对社区相对冷淡的态度,……[而且]尽管他的社交生活有限,行为上极端地个人主义,就他们本身而言,破坏速率者并不是没有组织性的。[^18]
对此,我有两点评论。第一,多尔顿似乎遗漏了他所关注的这九个“破坏速率者”最有意义的特征——年龄。只有一个小于 45 岁,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51 岁。^19 与年龄本身相比,资历可能与破坏速率更密切相关。资历越深的雇员,破坏团体规则时越无后顾之忧:
显然,一个在群体中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女孩可以时常轻微地破坏一下速率,作为惩罚,她只会受到小小的奚落。但是一个外人如果破坏了速率,就会受到叱责或嘲讽等严厉的惩罚;如果他们不知错,那么他们就只会是外人,如果关系对他们而言是很重要的,那么他们可能会被迫辞职。[^20]
第二,随着产业工作霸权组织的出现,速率破坏者越来越 可能是技术及资历把他们置于一种相对强势地位上的雇员。只有这样的工人才能避免受到工友们及工厂管理部门的制裁。我们已经指出了车间经理反对速率被破坏。只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操作工,比如一个地区工会的前任会长,可以始终超过最高限度,又让管理部门——尤其是方法部门——对他无计可施。
为了进一步指出在劳动力向劳动转化的过程中外界输入意识的重要作用,我对外部角色在个人产量水平上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我在样本中纳入了联合公司引擎分部的小零件组中所有的操作者(185 人),他们在 1975 年前 11 个月中,计件工作的记录超过了 40 小时。
为了解释这些图表,我提出了四种假设。第一种假设认为工厂中的行动不受外部生产意识的影响,生产中的关系介入 种族、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年龄与产量水平之间。换言之,外部因素可能决定了一个人在工厂里所做的工作,因而也就决定了加入什么样的特定关系中,但这种关系随后决定了生产活动。第二个假设认为,外来的意识确实 对工厂中的活动有直接影响——种族,受教育程度等等,独立于生产关系而形塑工厂里的活动。例如,在午餐休息时间里的非正式活动中,这种假设看上去是正确的。
后面的两个假设并不关注外部因素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影响,而关注外部因素影响或是介入关系转化为活动的方式。[^21] 因而第三个假设断言从外部引入的意识没有扮演中介的角色,然而第四个假设正好相反,外部因素决定了社会关系影响产量的方式。
这些模型或是假设可以通过两组变量进行测量。第一组对应于社会关系的外部系统,包括了家庭、学校及社区。我只能收集到四种可靠的数据,即种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年龄。我排除了性别,原因是在样本中只有 6 名女性。我排除了家庭规模,原因是在个人的记录中很少对这条信息进行更新。第二组变量对应于生产中 的关系。因为不同的工作种类太多了,而样本又相对较少,就不可能用操作的特定机器作为社会关系的变量。据此,我采用了资历(以月为单位,从开始雇佣到 1975 年 11 月)作为生产中的关系的指标。这个决定是基于三种假设。第一,我假定机械车间中存在一个大家认可的计件工作的威望等级。第二,我假定操作工会通过竞标系统尝试着追求较高威望等级的工作。结果是,操作工的资历会反映出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重要性。第三,我假定有同样重要性的机器会被嵌入相似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因此,资历将成为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指标。^22 第二个内部变量是经验,同样也是用从 1975 年前 11 个月以来在计件工作上所用工时数来衡量的。经验衡量的不仅是操作机器时所掌握的技术,也衡量了控制社会关系时所掌握的技巧,这些关系是与工头、叉车驾驶员、检验员及程序制定者等等的关系。因此,在有同样工作的操作工中,随着经验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生产中的关系。由于资历及经验对车间社会关系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少,我决定将这些变量转化为对数(以 10 为底)来进行实际的分析。
六个变量中的每一个变量(资历的对数,经验的对数,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产量(1975 年前 11 个月的平均产量)百分比的相对影响可以用结合这六个变量的简单多元回归来计算。表 2 总结了多元回归的结果。资历解释了 24.4%的产量变化,经验解释了 12.7%,而种族、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加起来解释了仅仅 3.5%。[^23] 这些结果似乎支持第一个假设而不是第二个。外部角色对产量的直接影响是可以忽视的。[^24]
表 2“内部”及“外部”变化对联合公司工人产量* 的回归分析(N 185)
| 自变量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决定系数(R2) |
|---|---|---|---|
| 资历的对数 | 18.62 | 0.43 | 0.244 |
| (3.49)+ | |||
| 经验的对数 | 12.87 | 0.26 | 0.127 |
| (2.94) | |||
| 种族(白人=1;黑人=2) | -1.70 | -0.03 | 0.003 |
| (3.05) | |||
| 年龄 | 0.22 | 0.12 | 0.009 |
| (0.15) | 0.012 | ||
| 婚姻状况(已婚=1;独身=0) | 5.54 | 0.12 | 0.011 |
| (2.84) | |||
| 教育(<中学=1;≥中学=2) | 5.35 | 0.11 | |
| (2.95) | |||
| 常数项 | 51.20 | ||
| (14.69) | |||
| R2=0.406 |
*“产量”在这里及之后的表格中是指 1975 年 1 月到 11 月操作者平均完成的计件数占产业工程部门所规定的速率的百分比。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然而,在产量中我们仍旧有 60%的变化是无法解释的。我们该如何解释呢?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某些策略对产量并不起决定作用。操作工可能试图超额,但是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这是因为 工作被构建成游戏,其产量水平显示随机波动;吸引工人进入这个游戏的特点是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结果。不确定性嵌入在劳动过程中——挑剔的检验员,有缺陷的铸件,磨钝了的钻孔机等等,都造成了不确定的结果。虽然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可能是决定产量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决定因素常常显示出某种变动性——它既不会大到让游戏充满失败感,也不会小到让游戏乏味。相应地,用六个自变量,尤其是内部变量对任何一周内的平均产量百分比做回归分析,其解释程度不如用全部 11 个月平均产量做回归分析的解释程度。比如,针对 1975 年 11 月的最后一周再下一周的回归分析中,只解释了产量变化的 21.1%。[^25]
嵌入在超额游戏中的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是变量无法解释的根源之一。另一个根源是我们用于测量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时所使用的不精细算法。资历较长的雇员不愿意冒风险去竞争一些声望更高的工作,而仍然继续他们原来就很熟悉的工作,这是常常发生的。可以有一堆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我的白班搭档比尔说自己太老了,不想重新开始。然而,更重要的是,杂项工作中产生的挑战与权力带给他的满足感。阿尔·麦卡恩,罗伊的工友,因为熟练地操作旋臂钻床,精通超额的窍门,给他带来了声望,颇让他有满足感。在联合公司里,最有声望的工作在超额方面是没有吸引力的,比如操作自动化车床。这是因为一旦掌握了设置程序,工作就没有挑战性或不确定性了。资历指标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声望更高的机器操作空职可能会由外面的人来填补。当管理人员觉得在一些更复杂的机器上没有令人满意的竞标时,他们可能会从外面找人来。在这种情况下,资历并不能衡量一项工作的声望。第三个问题,涉及社会关系与资历之间缺乏对应,与将有难度的计件率分配在有声望的工作上有关,正如发生在一些车床上的情形。由于计件工资率本身表达了社会关系,资历及简单计件工资率之间缺乏任何对应,就会导致第一次回归分析中无法解释的变异。然而,另外的误差来源可能是把经验看做是生产中的关系的“工作之内”的变异的一种尺度。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名操作工对某一机器有先在的经验,但这无法在我们对经验的测定中显示出来,因为我们的测定只限定在 1975 年。如果生产之际的社会关系想要解释超过 37%的变异,那么这些只是必须要引入的因素的部分罢了。
工人群体的异质性可能明确限制了可以被生产中的关系所解释的变异。至今,我假定工人对机械车间的社会关系的反应方式独立于他们的背景。这个假设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三个假设,它认为工人可能被看做是特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支持者或行动者。这些社会关系先于“承载”或“支持”它们的个人,个人根据源于它们的合理性采取行为。填补“空职”的工人(车床操作工、库房值班员、计划员、工头等等)受到劳动过程的限制。生产中的关系导致了鲜活的经验,它与填补空职的特定 个体无关,但却形塑他们的行动。超额先于加入这一游戏的工人个体,由空缺位置的组织而产生。结果依赖于在玩超额游戏时所掌握的技能,也依赖于界定了特定工作的社会关系。也许有人认为,“外部”因素以某种方式决定了技术,但是我们的假设更进一步地认为,技术是在生产之际通过工作经验及培训发展起来的。
与之相对的第四个假设,把工人设想为他们的脑袋里承载了一种由不同的“内化”及“社会化”过程所塑造的意识。在一个环境中获得的意识,介入另一种环境中关系对行动的影响。家庭、学校及社区中习得的社会化方式在工作中被激活,并且决定了操作工对计件工资率系统的反应——他们是否玩超额游戏或是其他的一些游戏,或是根本就不玩。
为了研究外界引入意识的中介影响作用,我把 185 个操作工分为亚组:白人与黑人;青年与老年;已婚与未婚;小学毕业与中学毕业。在表 3 及表 4 中,我比较了不同亚组中,资历的对数及经验的对数对产量的影响。尽管要由一个回归系数及常数都不同的回归等式给出任何明确的实质性结论是很困难的,然而,仍然有一些有趣的结果。第一,除去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工人之外,把人群分为亚组并不能增加产量中被解释的变异数目,对年青的操作工而言,被解释的变异数目显著下降。第二,除去黑人、年轻人或者未婚的操作工之外,这一亚组中,测量资历的对数及经验的对数对产量影响的标准化系数接近于整个人群的系数,也就是说,操作工的不同背景仅有有限的中介效应。[^26]
无疑,例外可以提供有趣的资料,来推测已经存在的中介效应的来源所在。让我们依次看一看吧。最有趣的偏离组是那些 1946 年以后出生的人。这个亚组中用生产关系解释的产量变量,点整个总体的一半,同时回归方程的系数表明资历在决定产量多少上,并不比经验重要。或许是与其他群体很相似,年轻的操作工从经验中学习,倾向于尝试不同工作,而不是立即寻求那些更容易达成速率的工作。换言之,年轻工人与其他人一样玩超额游戏,但是他们不必去竞争一些速率更易达成的工作。而且,他们试图尽可能地接触更多的机器来积累他们的技术。
对教育程度低的人恰恰相反。几乎 50%的产量变异可以由生产中的关系来解释。对于小学毕业者而言,经验比资历对被解释的变异更有作用,然而,对总体而言,资历的重要性是经验的两倍。这表明,小学毕业者比起中学毕业者来说,更有可能在生产中习得技术,通过工作经验来学习。尽管黑人与白人的产量同等地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但是资历对产量的解释力比起经验来,黑人几乎是白人的 5 倍。我们可以推测黑人操作工中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有的是在公司工作了较长时间的,是“好”工人;另外一些是最近才到的,并且对工作的霸权组织显示出极大的敌意。因此,年轻白人和年轻黑人对机械车间有不同方式的反应,这反映在存在于两个群体之间的敌意中,并明白地显现在整个年轻操作工群体中关系与产量之间的微弱关联上。
显然,从这些结论可以看到,在关系转化为行动方面,劳动过程并不是自主的。工厂外面的实践所塑造的意识确实影响了操作工回应生产关系的方式,尽管这种影响很有限。然而,如果劳动过程并不是自主的,它却有可能是相对自主 的。也就是说,劳动过程本身可能决定了外界引入意识的作用。或者,更具体地说,种族、受教育程度、年龄及婚姻状况对关系转变为产量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在劳动过程中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幸的是,我的样本量太小了,劳动过程中的位置很类似,而且我的测量对于就此问题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来说又不够精细。亚组人数使得根据劳动过程中的位置(如通过资历测量)对其进行再次分组是不可行的。我把样本分成两组:资历大于三年的为一组,资历小于或等于三年的为一组。接着,控制了经验的对数之后,考察外部因素对产量的影响。结果总结为表 5。这些数据显示出,严格的限制下,引入的意识是有作用的,其影响的确根据劳动过程中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27] 显然,这并不能证明联合公司劳动过程中具有相对自主性。最多只可作参考。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试图表明,第一,引入意识的变化并不会导致生产中的不同关系;第二,引入意识介入了生产中的关系向行动的转化,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第三,这种意识的介入作用随着劳动过程中位置的不同而变化,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通过劳动过程本身形成的。这些基于一些不坚实的数据得出的尝试性结论与第八章有相通之处。在第八章中,我试图表明 1974 年经济萧条引发的市场变化是如何通过工作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以及内部国家来影响劳动过程的。从所有的这些发现中我总结出,联合公司的劳动过程是相对自主的——即,它自主的形成了外部变化的结果,并且,正如我们可以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它创造了自身特殊的动力。
然而,引入意识的变化没有显著地影响生产中的关系或是劳动力消耗,但以此为由下结论认为工人在工厂之外发生的事情对他们在厂内的行为影响很小的话则是错误的。在黑人与白人,年轻人与老年人,小学毕业者与中学毕业者,已婚者及独身者之间意识的差异,比起资本主义对其所有臣民反复灌输的一般的意识来,可能仅仅是微小的差异。[^28] 一个对外部产生的意识之重要性的更充分的评估,必须以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反应的比较为基础。我将在附录里讨论这个问题,在附录中,我提出工作组织可能随着社会,政治及经济背景的不同而变化,但是工人行为与劳动过程的组织相一致,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们身上所带有的任何一种前资本主义意识。
我们将工人在工作以外的经验与在工作中的反应分开得越多,我们就越加不得不去假定人类不变的特性——即,我们就越多地倾向于去勾画一个关于人类本性的理论。我已经说了很多关于工人是如何通过游戏的建构、控制的“天性”等等,逐渐普遍适应资本主义的工作的迫切需要的。这些是人类共通的吗?最终,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回避提出一个有关人类本性的理论——一套马克思所说的类本质(species essence),也就是说人类内在潜能的理论。这样的一种理论对于理解解放了的社会之性质及其可能性,是不可或缺的。
除去共通性外,对于为什么发生在工作之外的事对发生在车间里的事很重要,还有第二个原因。在正常情况下,教育、家庭及大众媒体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化,并不会对工人从属于劳动过程产生影响。然而,在危机时刻——当生活经验不断地受到质疑,当存在的一切似乎不再那么自然与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理论可以成为有效的力量,即,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学校里所教的、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在家庭里所经历的,在那时都会对组织集体意志及形塑工人对资本主义的反应显得非常关键。
表 3 联合公司工人产量与资历的对数及经验的对数作回归分析,按种族、年龄及总体分组
| 分组 | 自变量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决定系数 | R2 |
|---|---|---|---|---|---|
| 白人(N=147) | 资历的对数 | 20.81 | 0.48 | 0.22 | 0.373 |
| (2.92)* | |||||
| 经验的对数 | 13.36 | 0.27 | 0.15 | ||
| (3.31) | |||||
| 常数项 | 48.28 | ||||
| (9.46) | |||||
| 黑人(N=38) | 资历的对数 | 26.45 | 0.59 | 0.34 | 0.391 |
| (5.94) | |||||
| 经验的对数 | 8.55 | 0.16 | 0.05 | ||
| (7.04) | |||||
| 常数项 | 53.55 | ||||
| (21.49) | |||||
| 1947年以前出生者(N=85) | 资历的对数 | 18.37 | 0.52 | 0.25 | 0.396 |
| (3.18) | |||||
| 经验的对数 | 10.87 | 0.23 | 0.15 | ||
| (4.17) | |||||
| 常数项 | 62.12 | ||||
| (11.81) | |||||
| 1946年以后出生者(N=100) | 资历的对数 | 24.19 | 0.30 | 0.09 | 0.191 |
| (7.37) | |||||
| 经验的对数 | 14.18 | 0.31 | 0.10 | ||
| (4.19) | |||||
| 常数项 | 39.85 | ||||
| (14.66) | |||||
| 总体(N=185) | 资历的对数 | 21.96 | 0.51 | 0.25 | 0.375 |
| (2.59) | |||||
| 经验的对数 | 12.37 | 0.25 | 0.13 | ||
| (2.97) | |||||
| 常数项 | 49.50 | ||||
| (8.60) |
*括号内的是标准误差。
表 4 联合公司工人产量与资历的对数及经验的对数作回归分析,按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及总体分组
| 分组 | 自变量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决定系数 | R2 |
|---|---|---|---|---|---|
| 已婚(N=130) | 资历的对数 | 19.69 | 0.50 | 0.24 | 0.375 |
| (2.80)* | |||||
| 经验的对数 | 11.10 | 0.26 | 0.13 | ||
| (3.12) | |||||
| 常数项 | 58.23 | ||||
| (9.12) | |||||
| 独身(N=55) | 资历的对数 | 23.92 | 0.43 | 0.18 | 0.329 |
| (6.42) | |||||
| 经验的对数 | 18.31 | 0.29 | 0.15 | ||
| (7.29) | |||||
| 常数项 | 26.19 | ||||
| (20.69) | |||||
| 不到中学毕业(N=39) | 资历的对数 | 19.79 | 0.53 | 0.21 | 0.495 |
| (5.12) | |||||
| 经验的对数 | 15.84 | 0.26 | 0.29 | ||
| (8.29) | |||||
| 常数项 | 39.59 | ||||
| (21.34) | |||||
| 中学毕业或更高(N=146) | 资历的对数 | 24.25 | 0.50 | 0.24 | 0.340 |
| (3.37) | |||||
| 经验的对数 | 12.40 | 0.26 | 0.10 | ||
| (3.23) | |||||
| 常数项 | 47.38 | ||||
| (9.91) | |||||
| 总体(N=185) | 资历的对数 | 21.96 | 0.51 | 0.25 | 0.375 |
| (2.59) | |||||
| 经验的对数 | 12.37 | 0.25 | 0.13 | ||
| (2.97) | |||||
| 常数项 | 49.50 | ||||
| (8.60) |
*括号内的是标准误差。
表 5 联合公司工人产量与资历的对数、经验的对数、教育、年龄及婚姻状况作回归分析,按资历分组
*括号内的是标准误差。
| 分组 | 自变量 |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 标准化回归系数 | 决定系数 |
|---|---|---|---|---|
| 资历小于(3.96)等于3年(N=137) | 经验的对数 | 14.69 | 0.31 | 0.101 |
| (3.74) | ||||
| 种族 | -3.96 | -0.08 | 0.003 | |
| (4.13) | ||||
| 教育 | 3.81 | 0.08 | 0.003 | |
| 年龄 | 0.37 | 0.15 | 0.018 | |
| (0.22) | ||||
| 婚烟状况 | 7.54 | 0.19 | 0.048 | |
| (3.59) | ||||
| 常数项 78.78 | ||||
| (17.54) | ||||
| R2=0.173 | ||||
| 资历大(3.76)于3年(N=48) | 经验的对数 | 13.90 | 0.48 | 0.178 |
| (4.11) | ||||
| 种族 | 2.35 | 0.08 | 0.007 | |
| (3.79) | ||||
| 教育 | 5.72 | 0.23 | 0.042 | |
| 年龄 | 0.22 | 0.19 | 0.012 | |
| (0.17) | ||||
| 婚烟状况 | -0.80 | 0.00 | 0.000 | |
| (4.57) | ||||
| 常数项 | 87.8 | |||
| (16.95) | ||||
| R2=0.239 |
[^1]: 约翰·戈德索普、戴维·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弗兰克·贝克雷弗(Frank Bechhofer)和詹尼弗·普拉特(Jannifer Platt),《富裕的工人:工业态度与行为》(The Affluent Worker: Industr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New York: Camh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较早的一篇重要论文是罗伯特·迪宾的“工业工人的世界:对工业工人主要生活兴趣的研究”(“Industrial workers’ worlds: A study of the Central Life Interests of lndustrial Workers”), Social problems 3(1956):第 131—142 页,它以一次态度调查为基础,宣称工作是满足工厂之外主要的生活兴趣的一种方式。对戈德索普等人作品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迪宾的结论。
[^2]: 戈德索普等人,第 185 页。
[^3]: 同前书,第 179 页。
[^4]: 同前书,第 164—165 页的图表 73 和图表 74。
[^5]: 《工人的态度与技术》(Workers’ Attitude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Eng.: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2)。
[^6]: 关于传统工人存在的探讨,参见洛克伍德的“寻找传统工人”(“In Search of the Traditional worker”),收录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印象》(Working Class Images of Society),马丁·布尔默(Martin Bulmer)编(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第 239—251 页。
[^7]: 参见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的《新社会》(The New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51)。
[^8]: “自由民主的社会团结”(“The Social Cohesion of Liberal Democra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1970):第 423—439 页。
[^9]: 约翰·维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交易关系的重新发现”(“The Rediscovery of the Cash Nexus”),收录于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970,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与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编(London: Merlin Press, 1970),第 111—138 页。
[^10]: 同前书,第 120 页。
[^12]: 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编织工业中的种族团体”(“The Knitting of Racial Groups in Indus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1(1946):第 512—519 页。
[^13]: 威廉·科恩布卢姆,《蓝领社区》,第 36 页。
[^14]: A. R. 拉德克利夫 - 布朗(R. Radcliffe-Brown),《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Cohen & West, 1952),第 92 页。
[^18]: 梅尔维尔·多尔顿(Melville Dalton),“工业速率破坏者”(“The Industrial Rate Buster”), Applied Anthropology 7(1948):第 5—18 页。
[^20]: 休斯,“编织工业中的种族团体”,第 517 页。
[^21]: 使用“干预”(intervention)和“调解”(mediation)概念时,我遵循的是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其《阶级、危机与国家》中所界定的定义。(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第一章)
[^23]: 联合公司引擎分部小零件部的 185 名操作员,构成了一个分散、独特的统计总体。尽管任何个案研究的结论都是启发性的和例证性的,我并非要提出我的统计分析的结果可以归纳到所用的行业中。由于我处理的是总体而非真正的样本,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没有太大意义。然而,我还是决定把显著性测验的结果当作一种可供讨论的设计包括进来:如果这是样本的话,我们会有信心将其推广到整个总体上。从而,在第一个回归分析上,资历与经验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是 0.001,而其他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甚至在 0.05。
[^24]: 当 1975 年前 11 个月的平均产量作为单独的外部变量作回归分析时,可以解释 21.5%的变化,与之比较,有 37.5%的变量可以由整个工作量来解释。可以被外部变量解释的大部分的变异都来源于年龄(20%),原因是年龄与资历的对数有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69)。既然只有两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大于 0.5,就没有造成多元共线性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结果也对在工作中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所谓的“现金关系”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如果金钱有很重要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期望一个需要维持一个大的家庭的人,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回归分析显示,婚姻状况、年龄这两个自变量对产量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
[^25]: 就回归系数而言,只有资历的对数,在 0.01 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包括经验在内的其余变量,在 0.05 的水平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26]: 尽管在一些回归系数之间的差异,看上去非常值得考虑,但是在统计学里,甚至在 0.1 的水平上,它们都没有显著性差异,这提示了不必把它们看得很重要。
[^27]: 又一次地,在产量中相对小的变异是通过外部变量来解释的;在一种情况下,解释的变异有 7.1%,在另一种情况下,解释了 6.1%。在外部变量中,对产量的作用有统计学意义的唯一的一个变量是婚姻状况,并且只有对于资历有三年或是不足三年的亚组而言。有人可能注意到,尽管它的影响是轻微的,种族对两个亚组的作用方向却是相反的:对于资历较长的一组而言,是黑人而不是白人降低了产量。
[^28]: 事实上,许多理论家都认为,这样的控制及规训的共同经验产生于社会的所有领域。可见于,比如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启蒙辩证法》(The Dialectic Enlightenment,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及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Pantheon, 1977)。特别相关的是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著作《在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他们认为在教室里与在工场里的社会关系之间是有相关性,这并不是意外,而是统治阶级有意地试图使用学校作为工具的结果:
消除政治对潜在的易爆发的阶级关系的影响……。通过提出这些方式来保留经济生活的社会关系,推动年轻人稳定地融合到劳动力当中,……通过他们奖赏及促进学生表面上的精英性格来使不平等合法化,……在学生中创造并强化社会阶级,种族的及性别的认同,[并且]在经济领域内,鼓励个人的发展方式与支配及受支配的关系协调一致。[第 11 页]
所有的这些都包括了——除了传授技术、社会技巧及以恰当的动机参与进入劳动力。他们总结到:
经济系统保持稳定的条件是,社会阶层与阶级的意识的组成与社会关系保持一致,这种社会关系是以生产模式为特征的。阶级结构的永久性要求,在劳动参与者的意识中再生产劳动阶层的分配方式。教育系统的再生产机制之一,是通过控制精英以寻求统治目的……。教育系统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的再生产,部分的是通过使自身内部社会关系及工场中的社会关系之间相对应来进行的。[第 147 页]
同时,鲍尔斯及金蒂斯确实认识到“必须对工作进行组织,这样才能让公司的权威关系显得是最公平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上下级及同事之间必须不能违反社会常规”(第 82 页)。在工场里,种族、年龄或是性别之间的关系颠倒可能只会引起冲突及不稳定。由于他们没有意识到劳动过程中的相对自主性,它的再生产能力及使它自己的关系“合法化”的能力,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鲍尔斯和金蒂斯总的看法中,每一个部分都是对资本主义的表述,因此,必须与资本主义关系相一致。对他们而言,重点不仅是不同的学校系统或是不同的家庭生活将产生与工作关系不一致的意识,因而增加了不稳定性;重点也在于,不经过劳动过程的第一步转变,这些学校及家庭永远不会实现。“不平等的方式、镇压及阶级控制的形式不能受限于一个单独的生活领域内,而会在所有的领域内,尽管以不同的本质来再现,但结构是可比的”(第 148 页)。尽管鲍尔斯和金蒂斯关于工作关系与学校教育之间对应的观点,将会预见到这一章的结论,他们很有可能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工人这一贡献加以强调。并且可能减少对教育系统与资本主义关系相一致的范围的限制。同时,我明显已经不再否认,教育及家庭在把一个人安置到阶级结构中的位置与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能诸如文学、计算能力等的重要性。然而,甚至在这个水平下,正如我对赞比亚铜工业的调查中显示的,当工人和监督者的语言背景不同时,会在生产中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语言。最后,正如我将在第十二章中提出的,劳动过程与他们的引入的意识与外部环境变化无关时,劳动过程确实发生着变化。这些因素在经济的竞争部门可能更加重要,这些部门的劳动过程很少通过精心的隔离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而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