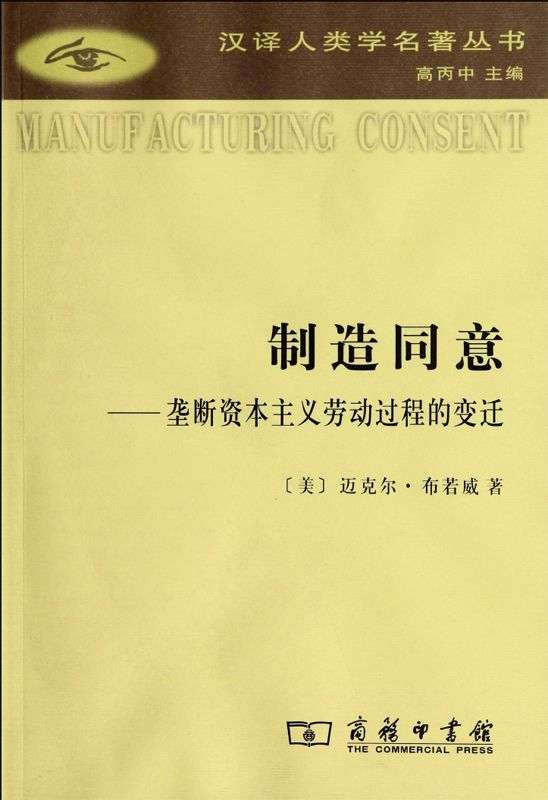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十章 车间里的斗争—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五部分 变迁的动力
第十章 车间里的斗争
在第二部分我描述了工作组织的变化,在第三部分描述了这些变化对于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的作用。在第四部分讨论了劳动过程不受外界变化以及工人从工厂之外带来的意识影响的程度。现在我转向最后一项任务:解释 1945 年至 1975 年间,发生在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的劳动过程中的变化。本章的讨论聚焦于车间的斗争,而下一章的讨论则超越了车间范围。
经济斗争
车间里经济斗争的目标是对工作表现的讨价还价,也就是说,劳动消耗的经济报酬或业绩的奖励。资方通过计件工资制来决定劳力的报酬。因此,1945 年时,每一件产品都被赋予了“价格”。每小时的工资由生产出来的件数乘以每件的价格而计算出来。此外,当工人们未能生产出预期的数目时还有基本时薪保证。1975 年时,工资制从基于价格转变到了基于“速率”,也就是说,对于给定产品而言,每一项作业都有规定的标准速率,它指出每小时要生产多少件。如果操作工超过了这个标准,他或她就能得到一笔根据各自每小时基本收入的比例计算出的奖金。当他们未能达到标准速率时,则获得基本收入。(关于“价格”、“速率”的进一步讨论参见第四章。)然而,在这两种机制中我们都可以建立一个“业绩 - 报酬曲线图”(见图 1),它显示出操作工因每小时生产出的产品数量而获得的报酬,即根据特定的业绩水准而获得的报酬。对任何一项操作而言,我们也能建立一个“业绩曲线图”,它显示了根据业绩水准而得出的资本与劳动(根据件数或相当的价值来衡量)的回报(见图 2)。业绩曲线的上升相当于超额。

图 1 报酬 - 业绩程度曲线

图 2 资本和劳动的收益
在这两个图中,A 对应的是产量等于或小于 100%的“基本收入”。A 到 B 这一部分是 140%的产量得到的奖金。“业绩”根据产量衡量。标准产量是 100%。工人产量超出 100%开始挣激励性奖金。(“预期的”产量比例是 125%。参见第四章。)
我们已经提到(第四章)等级冲突会伴随着超额的压力和挫折,以及这些冲突是如何被重新分布到工人中间。这种等级冲突不是 斗争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是超额的重要部分。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竞争 形式,它认为经济报酬的分配、游戏规则,结果等级等是理所应当的。另一方面,经济斗争 并不指业绩曲线的上扬,而是指业绩曲线的移植或重新塑形,从而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相关回报发生变化。资方寻求降低价格(1945 年)或是提高速率(1975 年),而工人们则力图反向行动。在劳动过程中,这种性质的斗争通常是由其职责在于确立业绩曲线图的形状和位置的方法部门引发的。然而,正如我们在下文将会发现的,自 1945 年以来,方法部门已渐渐地从车间撤出,围绕业绩讨价还价的日常斗争也相应地减少了。
1945年的工时研究
吉尔公司的方法部门雇了一组工时计划员作为效率的监督人员——以此象征科学的管理。他们秒表在手,不停地在车间巡视,一边寻觅那些为操作工提供“有油水的工作”的“好价格”,一边按表计时。操作工唯有始终保持警惕才不至于使他们逼近。
如果操作工们厌恶象征着“更多工作”的“大亨们”,工时计划员们则更夸张,要求“做更多工作,给更少报酬”。工人们对上层管理者的敌意被一种幽默感的展示而缓和了;与工时计划员的关系则自始至终都是件“严酷的事”。[^1]
工时计划员是“加速”的代理人,他们总是试图压低计件工作的价格。他们甚至被怀疑从他们为公司所节约的那笔钱当中得到了佣金或奖金。虽然这并不是真的,正如罗伊后来所发现的,但重要的是多数操作工相信这一点。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们为何要坚持试图廉价化操作工呢?[^2] 工时计划员的伎俩遭遇到了绝对的抵抗。
作者被进一步告诫,不论是否超过了配额,都要“提防”工时计划员。这意味着工时计划员不仅仅依靠记录当中的“线索”,而是在车间执行着“私家侦探”的任务去侦查“有油水的”工作。
“你要提防的人是工时计划员。不论何时你一旦看到有人拿着纸板,上面还连着表的人站在你周围就要当心了!慢一点!轻松些!”
斯特拉,一个熟练的研磨机操作工,描述了一些时间侦探“侦查工作”的狡猾之处。
“前几天埃迪背对着我偷偷计算我的工作时间。他听着机器的声音来判断我何时完成一件活。正如我所想的那样,过后他走过来看进度表,得到工作的数目,记住它,回去将它写下来。
他会走过来以那种方式对老工作计时。你不会想到他在监测你,但他却在听你的机器声。”[^3]
方法部门持续在场的后果并不难设想。[^4] 显而易见的,操作工们小心翼翼地不去上交多出他们限额的量,也不在工时计划员面前超额生产。任何完成了比他或她的限额多的人都会感受到相当大的社会压力和烦扰。操作工、工时员、工头以及其他人都在监视着那些有可能上交比限额更多的操作工,不论他们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
然而,支架车间的“社会风气”明显与限额破坏者不相契。要不在萌芽状态就被消灭了,要不根本就未萌芽;因为在 11 个月的时段内,作者只注意到几个超过限额的孤立的小个案。这些隐晦的行为发生在特殊的情形下,犯罪者并非“惯犯”。[^5]
实际上,罗伊仅能提供三个关于速率破坏的微不足道的、单独的例子。
如果没有速率破坏者 ^① 的话,那么哪来的削价?方法部门只要引入一些小变化就可“合法地”降低任何计件工作的价格:
大家理解并且同意,公司可以在任何时候因为机器的改进、规格的变化或工程的改变而调整计件工作的速率。[^6]
如果资方想要改变价格,就可轻易做到。尽管罗伊听到许多人说起削价,他自己在吉尔的 11 个月期间从未经历过。他自己的白班搭档乔·穆察经历过两次削价以及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罗伊也记录了发生在其他机器上的四个削价个案,但并不清楚罗伊是否还知道别的个案。方法部门经常采用的一个技巧是取消某一工作的价格,然后将那个工作置于“工时研究”的范畴中。这是一个公认的重新计时和重新定价的惯例。“无论何时价格被取消,操作工都有理由设想削价是早晚的事。”[^7]
计时本身是一场没有明晰规则的游戏:
对于操作工来说,工作计时是一场“游戏”,一场“才智的竞赛”,其中,公平比赛的严格规范并不明显。(游戏的)目标是“好价格”,这一目的正当化了所有有效的老伎俩。[^8]
操作工们一般通过增加额外的动作以及低速工作来抵抗;然而,工时计划员当然熟知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策略,因而不能靠它们来获得“好价格”,罗伊付出了一些代价才发现这一点。罗伊自己有三件新工作被计时。他承认他对于“诈骗工时计划员”的艺术依然没有经验,他从未获得一次完全的胜利。斗争使得工人们团结起来抵抗方法部门。每个人都会告诉别人自己怎样最有效地欺骗工时计划员的技巧。在计时和谈妥价钱之后,操作工、检验员、计划员等等还要做事后分析,为今后如何做出谋划策。如同前面描述的那样,即使是工头也在操作工能否得到一个好价格中有利害关系,偶尔他们也会介入进来代表操作工:
今晚,乔说我做蜗轮的价格不高。他期望的价格是 10 或 12 美分,而不是我所得到的 6 或 5 美分。他问我是否在计时的时候加快了进料速度,我告诉他我以 11 级的进料速度进料,他顿时备感失望。
根据乔所说,不到 3 点他们就来给他计时,而且试图让他以 610 的速度操作、11 级的速度进料(当时他采用的分别是 445 和 7)。他以 610 和 11 的速度干了一件活,但是罗西(白班工头)和工时计划员说,那样的速度不能令人满意。工时计划员在速度分别为 445 与 7 时没有给工作计时,在速度分别为 445 与 11 时又回来计时(我在工时调查时操作的速度)。[^9]
另一方面,操作工们也持续警惕那些可能与方法部门共谋的工头或其他管理层的官员。“虽然第二班生产线的工头从未被控为严重过错——与方法部门的勾结,也从未被取‘公司的人’这样的绰号,但是机器操作工对他们的看法绝不会是完全肯定。”[^10] 正如文献中经常指出的,工头是中间层,处于一个含混的位置,这使得他们倾向于在不同的情形下支持企业中的不同位置。
暂且不论工头,工时计划员无孔不入的影响以及对压低价格的持续担心促成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与资方的斗争会削弱伴随着超额的冲突,即等级压力会扩散到工人们的敌对与竞争中。对白班搭档、检查员,别的操作工及其他人的憎恶,因为对抗以方法部门为代表的资方所持续产生的共同利益而被减轻了。
1975年的产业工程学
在过去的 30 年里情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将在下一章探究其原因。今天,工时计划员已经被产业工程师所取代,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是拿着纸笔和便携式计算机在某个遥远的办公室里度过。工时研究被专业化了并变得更加“科学”。产业工程师明显地不愿意拿着一个手表出现在车间。即使有时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也会注意通过设法赢得操作工的配合并抑制其敌意来开始工作。他们肯定不会在过道上来回巡视松散的工作速率,或是在产量记录中搜索偶然出现的速率破坏者。现在很难在车间里见到一个产业工程师,更别说是见到重新给工作定时的人了。比尔,我那班的白班搭档,试图要找到一个产业工程师给我们其中一项工作定个固定速率(来取代概算的速率)。当我在那的时候,这一特殊的工作肯定被提了多次,但比尔却从未设法使工作得到计时。实际上,在我在引擎分部的整整 10 个月期间,比尔和我都未曾让人给我们的工作计时。
然而,对于速率上升的担心依然是车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而它依旧是持续执行“配额限制”的基础。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但正如下面要说的,速率的提升并非来自怪癖的、贪婪的工时计划员在巡视过程中的决定;相反,他们遵循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据我所知,我在车间的 10 个月期间,小零件部门有三次速率提升的事例。在每一个例子中,使用同一机器的许多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在其中一个事例中,速率首先急剧上升,但在几周之后又恢复到最初的水平——其原因还不清楚。
第二个事例涉及一台自动车床。埃德,一名操作工,提交了提高他的机器上几项速率的“建议”——一个不寻常的但却并非没有前例的事件。实际上,这不是埃德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如果建议是可行的,并因此节约了公司资金的话,操作工就会得到一笔奖金。奖金当然只发给提建议的工人,操作同一台机器的其他工人是得不到的。一旦这一步迈出了,操作工很少能说服资方相信新速率是不公平的。不出意料,强烈的敌意指向了提建议的工人,他几乎在车间里被完全排斥了;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激怒了受到直接影响的操作工,还是对整个群体的直接冒犯。埃德是个资深雇员,在联合公司和吉尔公司已经待了 30 多年,看上去他并不在意他所引起的敌意。无奈之下,他那班的夜班工人只好以申请调职来显示自己的反对。然而,由于现存的高失业率,资方要找到一个熟练的替代者一点也不困难。工会干部们袖手旁观。他们声称无法改变情形,但一个干事表示如果他曾在那台机器上干活,他会让埃德掂量掂量再行动。
工头也被埃德的行为所困扰,因为这打乱了将“松散的”速率分配给技术活的政策。如同我在前文提到的那样,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难以达成的速率会导致工作之间的高流动性;当涉及自动车床的时候,就培训、废品和有效操作机器而言,流动性是花费颇多的。就车间里的简单工作而言,如多数新手一开始干的高速钻孔,只需些许培训;速率难以达成,人员流动程度为此相当高,但这花费不大。那些想要操作更复杂的机器的操作工往往会一接手新工作就不愿调离。因此,如果某一自动车床的速率提高了,这一工作的吸引力就下降了,工头也随之面临稳定性的问题。然而,方法部门——其运转是以通过“工序修正”和“工时研究”省下的钱为基础来评价的——非常满意埃德的建议,将其付诸实施。
第三个速率提高的事例更有争议性。它涉及齿轮生产的最后工序之一:“修剪”齿轮。这项工作的程序设定需要具备不少专门技能,干这件工作的那两个操作工都是资深雇员。阿特(Art)在公司已经干了 20 多年,他干的是白班;布鲁斯(Bruce)则干了 11 年,他干的是夜班。阿特去年上交了 150%的完成量,以致公司最终决定介入。为了提高既有速率,方法部门不得不引入技术变革。它决定减少在齿轮上的“完整循环”的数目。由于阿特和布鲁斯都是熟练操作工,并且齿轮是引擎最基本的部分(缺了它们装配就无法进行),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强势的位置来抵制变革。他们采用了两种策略。首先,他们都申请调到自动螺旋机工作;其次,他们上演了“怠工”。两周来,管理层干部站在刨削器旁监测通过的齿轮质量,毫无疑问,他们也在防止阿特和布鲁斯别磨蹭。斗争以其他怠工形式继续着,例如旷工和临时请假。这产生了预期中的效果:齿轮没有足够快地下线。最终妥协达成了:如果操作工努力完成订单,资方就只会在小齿轮上提高速率。几周后,布鲁斯离开了齿轮机器转到一个自动螺旋机器那干活去了。阿特依旧在原来的岗位,一个新的操作工代替了布鲁斯的位置。在整个与资方的斗争过程中,阿特与布鲁斯之间充满了敌意,这源于他们与工会的不同关系(布鲁斯是工会干事,阿特曾是前任主席),也源于布鲁斯对阿特的高产的怨恨。这对于他们对抗变化并无助益。布鲁斯,一个可靠的、勤勉的操作工,得到了人们最多的同情。阿特担任工会主席期间就不为人喜欢,现在的高产无非让他更不受欢迎。
因此,除了神秘的第一个例子外,操作工在与资方的斗争中都失败了。正如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其对相似的速率提高个案的描述中所清晰论证的那样,公司凭借它更为强大的力量最终可以迫使操作工屈服,仅只因为它可以利用内部以及外部劳动力市场而轻易地替换操作工。[^11] 速率提高的确产生了经济斗争,但这些斗争既增强了超额规则又强化了工人间的冲突。通过“依据规则游戏”,也就是说,通过只提高那些操作工一贯地并且公开地承认的“松散的”速率,资方避免了与对它有敌意并且凝结在一起的工人群体的正面冲突。工人的敌意并没有直接指向方法部门,而主要指向了破坏速率的工人或提建议的工人。部门里的每个人都听到速率提高一事,此后几年车间里的闲言碎语总围绕着犯错的操作工。一些操作工威胁要痛打埃德;也有人则想弄乱他的设备或把他的工具藏起来。工头则对其下属说速率提高只能怪他们自己。破坏规则及其惩罚——速率提高——修复或复兴了被违背的规则的约束力。速率的提高是一种仪式性的重要事件,它肯定了超额规则以及它们所象征的资方与工人的利益一致性。只要资方只提高那些 140%的最高限度总被蔑视的速率,那么它的行动远远不会产生一致团结的抵抗,反倒是强化了对其支配地位的同意。
1945 年时,工时计划员是操作工与资方之间出现的冲突的焦点。工时计划员并没有促成对超额规则的承诺,反而是因促成经济斗争而破坏了游戏规则。换句话说,经济斗争预示了斗争的升级,并且的确发展成为了政治斗争——即关于超额规则的斗争,关于生产中的关系的斗争。1975 年时,情形与之相反,由产业工程师造成的经济斗争不仅数量少而且增强了超额的规则——也就是说,经济斗争没有促进具有政治性质的斗争。
政治斗争
为了完成某人的配额,而设法逃避、跳过甚至破坏某些规则是超额的内在性质。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一个策略就是把某件工作上节约的时间转移到另外一件工作上——称作“使诈”的伎俩。1945 年时,这导致了操作工顺从并重新塑造界定了超额规则的某些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使诈需要工时职员的合作,他们告诉操作工接下来干什么活;需要库房值班员的合作,他们分发夹具,并且在操作工给前一件工作打卡时就打上印记;需要仓库搬运工的合作,他们早早的就把原料备好而无需一个工作指令;需要检验员的合作,他们在操作工已经开始一件新活计之后才记下他前一个活计的下工纪录;还需要工头的合作,他们默许所有这些。这些与“正式的”规则背道而驰的“非正式的”伎俩,罗伊称之为“搞定”。[^12] 在前面的章节当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其他“谋略”——包括使社会关系服从于操作工在超额中的利益——是如何谋取到工头的合作,例如,工头可以“搞定”时间卡;或是如何谋取到检验员的合作,他们可以改变下工程序的打卡时间,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1945 年 3 月到 1945 年 5 月间,高层公布了一套新的规则来恢复和增强吉尔公司“正式的”生产中的关系。[^13] 第一条新规则关乎库房值班员,除非操作工出示一张表示已经完成前一件任务的黄色卡片,库房值班员不可以让任何图纸和设备出库。这只是增加了库房值班员的工作而已,因为操作工不再能自己取设备,还得在换班时归还。然而,设定工依然可以溜进库房拿下一件任务所需设备。后一个干预从而更加激进:除了主管和库房雇员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库房。这带来了库房之外的混乱和瓶颈,挫伤了操作工、库房值班员以及工头:
下班时我发现吉尔[工头]与沃尔特[库房值班员]在库房窗口那儿谈话。吉尔看上去很严肃;沃尔特挥动着他的手臂,还以其他的姿势在某种意义上表示拒绝负责。我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但我猜吉尔不同意或是在警告,吉尔走后我对沃尔特说:“看上去你现在处境不妙!”
我注意到沃尔特发型混乱,看上去有点疯狂。无论如何他否认他陷入了任何麻烦之中;他也不担心任何事。
“我只是在这干活!”他大声说道,“我只是依照卡片行事,就此我没有任何责任!”[^14]
汉克斯显然见惯了这样的“新规章”,预计这不会持续一个星期。^15 在另外一个减少操作工自主性的步骤中,材料搬运工收到指令,在得到工作命令之前不可以把原料搬到机器那。这意味着操作工首先必须得打卡结束前一件工作,然后打卡开始另一件工作。工时职员不再传递下面的工作信息。当设定工约翰尼试图从计划室那获知罗伊的下一件工作是什么时被粗暴地逐开。检验员不得不引入“红色标签系统”,把那些产出废品的机器贴上标签,每小时都检查数目,把检查内容记录在工作本上。[^16] 但这对于检验员而言是个劳累活。
萨姆今晚在忙着检查,他并不喜欢这样。
“这个见鬼的系统!”在一次几乎晚了四分之三小时的例行检查时他说到。他把自己的检查从八点十五往前定为七点半。
我从未见过萨姆感到如此厌恶,我禁不住挖苦了他一下。
“今后在你应该早一点来做第一轮检查”,当他五点二十检查我的第一件活时我严肃地说道。他以脏话回应了我。
好几次我近距离地看着萨姆,实际上我在想他是辛苦的。[^17]
此外,检验员现在必须在一个班次结束时数清操作工干活的件数,他们要在使诈过程中发挥默许的才干也变得更难了。即使是工头也得屈从于限制。“在‘苛政’期间,吉尔说他在班次结束时‘搞定’卡片的日子结束了。”[^18] 这些变化是在两个多月的期间里引入的,但这只是事态恢复到常态之前几周的事而已。
我经历了一些相似的事件。检验员接到指示引入一种“绿色标签系统”。印着日期、作业以及检验员号的绿色标签贴在检验员检查合格了的第一件产品上。如果假定操作工没有把标签转到另外一件产品上,废品的责任就可准确地追究到操作工或检验员。同时还引入了新的检验卡;这为操作工记录他所生产的产品的周期性检查提供了空间。工头会来检查操作工是否恰当地填写了卡片。对于那些过于自由地分发“双份红卡”或为了驯服新操作工而给他们过多的按照设定员薪酬标准计算的小时数。工时职员接到命令,他们必须保管好计划室里的产品和设定卡,不使它们在车间流传。这可能是用来对付像我一样用铅笔填时间,而不是打卡的操作工。但是当库房只对总工头和库房值班员开放时,1975 年的这一大举动失败了,如同 1945 年那样。如此举动把第二班的工作搅得一塌糊涂,在那仅有一名库房值班员。例如,我时常操作的一台机器是钻孔机。机器上有一根长钢轴,带有利齿的锥形钻矛水平地从皮带轮缘或齿轮内缘穿过,钻出一个规定尺寸的销孔。设定程序最讲究诀窍的一部分是找到正确的钻矛。钻矛保管在库房里,不过库房值班员几乎不懂如何区分开每个钻矛,我就总是径直走进库房自己拿了用。在无人能够进出库房的情形下,钻孔工作难以进行。我必须要得到特殊的允许才能进去找我所需要的东西。与 1945 年时一样,1975 年的所有这些变化最后证明是不可行的,没过多久事情就恢复到了正常。
政治斗争的资源
1945 年和 1975 年的苛政并非孤立的或非同寻常的事件。根据罗伊与我的调查,它们是车间动力的构成要素,从而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件。汉克斯知道新规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的白班搭档比尔也这样想;正如比尔所说:“他们总是引入这样一些狗屎。”等级控制产生了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但这反过来为规避资方统治的非正式联盟的合作铺了路。这一过程迟早会导致高层重新施加严格控制的新企图。但为什么在罗伊开始研究之前,这就已经是车间生活持续存在的一个特征?
罗伊对此这样解释:在特定的情形下,效率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维持;效率并非资方的特权;非正式工作群体并不一定是妨碍物,实际上却有可能促进对资方目标的追求。罗伊对霍索恩试验 [^②] 做了有力地批评,并对那些站在资方角度只看到非正式群体的危害和阻碍的人提出了重要的纠正。但是,如果规则妨碍了生产,如同罗伊和我的观察所表明的那样,为什么资方还要坚持强加规则呢?罗伊看起来似乎没有解答。如果说资方并不理解效率的必要性,或忽视了车间层面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话,也就是犯了与埃尔顿·梅奥同样的错误——他指责工人不懂资方的效率。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循环的动力呢?
首先,动力嵌入在生产中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操作工面对机器的自主性,与他们对辅助工的依赖共存。部门的特殊化意味着辅助工对他们自己的管理层负责,该管理层的关注不同于生产管理层。例如,我在联合公司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发现“物资控制”管理层在分配材料给生产部门时施加了压力。在那之前,工头可能已经把车间所制定的材料数量膨胀至两倍或是三倍。以这样的方式自动机器频繁设定所需的高额开支就节约了,操作工可以在其工作上获得长期补给。现在,材料的分发限制在车间具体制定的数额上。这一行动是驱动削减库存量的一部分,但这里的节约被其他地方增加了的成本所抵消了。此外,变化一方面刺激了操作工与工头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刺激了操作工与材料分配员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质量控制管理方,他们总与生厂方不一致。新的质量控制经理上任伊始常常对检验员施加更加严格的控制,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操作工与检验员之间的对抗。只有工人联合起来,在可以互惠的地方打破规则,冲突才会给继续生产让道,即使更高管理层重新启用最初的规则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换句话说,动力源自于生产工人与辅助工人的相互依赖以及相关部门的相对自主的并置。
然而那些从车间晋升上去的经理,一定知道强加限制性规则的后果——尤其是它们不可避免的消亡。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这些明显徒劳的努力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周期性地强化“过时的”规则,构成了对资方支配地位的仪式性确认。在日常的超额游戏中,工人们在相当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活动;偶尔地引入规则是用于提醒他们,或是具有提醒他们的后果,即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下属,自主是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换句话说,它是用于规训劳动力。传统的规训资源是失业劳力的后备军,企业创造出了种种机制使自身免受它的影响或者去补充它。然而,当内部劳动市场以及内部国家的兴起造成了工人就业更大的保障时,资方必须要寻找规训的替代方式。但这个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工作组织是用来消除对规训的需要,并具体地调整工人与资方利益的。通过强加规则的仪式性惩罚只会导致重新引入等级对抗,并削弱车间里的霸权组织。
这使得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考虑动力——也就是说,车间管理层与更高层的资方之间的斗争。车间管理层负责赢得剩余价值,同时又要掩饰它。由于车间管理层不能在赢得剩余价值中监控自己的成效,他们允许劳动过程根据超额的指示而变动,这增加了成本但降低了质量。操作工不断地与他们的工头互动,并迫使他们在分配双份红卡时慷慨大方。他们迫使检验员批准几乎不能通过可接受标准的产品合格。操作工还向库房值班员施加压力,而如果操作工们进入库房自己拿东西,或他们把工作用具一直留在他们的机器上而别人又找不到的话,这就会导致组织解体。而计时员身上的压力则会导致使诈盛行。因为辅助工与操作工在打破规则和重塑关系中通常利益一致,这些趋势如果不扭转的话就会导致利润危机。然而,车间管理层虽然没有鼓励,也对这些伎俩睁只眼,闭只眼。
正是更高的 管理层引入了旨在保护利润的“新规则”。更高管理层较少涉入到劳动过程的指导中——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他们更多的是以利润的形式实现剩余价值。因此,由他们来施行关于成本和质量的限定。然而,因为他们远离车间,只能通过强加规则——结果证明与机械车间劳动过程的组织相矛盾——来执行对这些因素的控制。^19 剩余价值的持续掩饰和赢得有赖于放松这些规则,而一旦放松最终又会导致另外一种利润危机。
简而言之,对生产中的关系的斗争及其引起的循环动力是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的具体表现。在劳动过程中掩饰剩余价值致使关注实现剩余价值的更高管理层强加规则来消除削弱赢得(生产)剩余价值的倾向。这些作为疗法的规则比疾病更糟糕,这正是在机械车间劳动过程的本质。规则不得不被放松。然后循环重新开始。
结论
在这一章我区分了车间斗争的两种类型:经济斗争,其目标是对业绩的讨价还价;政治斗争,其目标是生产中的关系。1945 年时,经济斗争能够,至少是潜在地,为政治斗争铺垫基础;1975 年时,经济斗争具有强化对现存的生产中的关系的同意的效果。然而,在这两个时期,政治斗争都引起了循环式地强加和放松由更高管理层创造的规则——违背车间管理层利益的规则。循环的动力可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主要特征的具体表达,这一过程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相分离的结果的不同管理层之间的斗争,并不总会导致循环动力。更高管理层有时会成功地在生产关系中施加一些持久的变化,^20 有时也会通过经济斗争——例如,通过加速装配线——对实现剩余价值的压力做出反应。
尽管罗伊与我都经历了车间里的经济斗争和一定程度的政治斗争,我们却很少观察到关于生产目标、优选成果排序,或者是否参与超额或其他游戏的斗争。如此这般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孤立的例子被认为是“偏离正规的”,也因此重申了对超额目标的承诺,而非破坏这一目标。然而,只有当斗争进展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也就是说,但政治与经济斗争的领域变成斗争的对象时——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才会受到直接威胁。意识形态斗争带领我们超越资本主义、超越需求的专政。它们是斗争,但不是针对业绩讨价还价的形式的斗争,而是针对业绩的报酬这一概念的斗争;不是针对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的斗争,而是针对生产关系的基础的(basis i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区分了存在之物,与自然的和不可避免之物。
注释
[^②]: 霍索恩效应(Hawthorne effect)(指工人、学生等因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而增加产量或提高成绩)受人关注带来的提高(或进步)。——译者
[^1]: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238 页。
[^2]: 同前注,第 252—253 页。
[^3]: 同前注,第 239—240 页。
[^4]: 时效调查人员的工作时间是上午 8 点到下午 5 点。由于罗伊是在第二班,与他们重合的上班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
[^5]: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113 页。
[^6]: 吉尔公司 1945 年的合同,条款Ⅸ,第四部分。
[^7]: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111 页。
[^8]: 同前注,第 242 页。
[^9]: 同前注,第 245 页。
[^10]: 同前注,第 322—323 页。
[^11]: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第 79—85 页。
[^12]: 罗伊,“效率与拉拢:一家计件机械厂的非正式群体间关系”,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0(1954):第 255—266 页。
[^13]: 罗伊对新规定的引进并未做出解释。与解释最接近的是他对装置设定员的评论:“第二天,约翰尼‘解释’了新规定,他说那是资方在不满之前的‘自助’政策放慢了而非加快生产速度后企图找出‘什么阻碍了生产’。”(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416 页)。为何在那时引进新规定罗伊并没有探讨。
[^14]: 罗伊,“一家计件机械厂的产量限制研究”,第 415 页。
[^16]: 同前注,第 373—375 页。
[^17]: 同前注,第 374 页。
[^18]: 同前注,第 43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