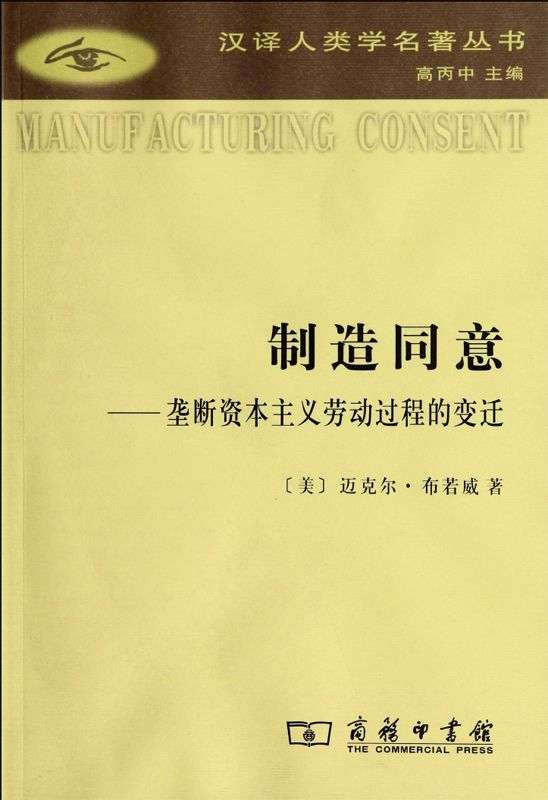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十一章 阶级斗争与资本家的竞争—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十一章 阶级斗争与资本家的竞争
在第十章里,我们看到车间里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方内不同等级间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这些斗争导致了循环式的变化,这又成为在劳动过程中引入长期的单向度变化的媒介。[^1] 也就是说,霸权性工作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以及内部国家的兴起,重叠施加在机械车间特有的循环动力上。但是 1945 年至 1975 年间,那些循环动力介入其中而非产生的变化,其源泉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超越车间层面,并以一种我们在第八章讨论短期变化未曾尝试的方式去探究“外部”与“内部”因素的互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时间跨度越长,研究者可以确定的变量越少,寻找变化的起源也要走得越远。
超越了车间层面的力量往往通过两种渠道使其被感知,即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的竞争,二者反过来又以一种被机械车间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方式影响劳动过程的动力。从而,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的竞争被组织起来,以此阻止车间斗争变为劳动过程变化——已经描述过的循环方式除外——的源泉。
在正常的车间日常生活里,工人们并没有组织成一个阶级。出于这个原因我避免将车间里的斗争称为阶级斗争。相反,迄今,我一直用斗争的目标 来区分不同的斗争。另一方面,阶级斗争指涉及阶级之间的斗争。阶级斗争既预设了工人与资本家的组织,同时又使之形成具有共同利益的自觉集体。我将在本章设法展示资本与劳动者的有组织的代表——即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如何促成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的劳动过程的变化的。只要工会与资方致力于重塑或维持经济报酬的分配(经济的阶级斗争)以及生产中的关系(政治的阶级斗争),它们就是各自阶级的有组织的代表。^2 这些斗争将资本主义的秩序视为给定的、天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这些斗争不是意识形态的,甚至几乎不是政治的——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阶级斗争。
变化的第二个动力是资本家的竞争。在探究萧条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中,我从资本家相互依赖的视角审视他们之间的关系。每个企业都要依赖于其他的资本家为它提供生产工具和原材料,以及购买它的产品。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实现利润的条件,而利润率又是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形成的。竞争可能在劳动过程的人力与非人力投入之上进行,可能在生产组织本身之上进行,或者在销路之上进行。换句话说,从商品使用价值的角度而言,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角度而言,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则是竞争关系。1945 年至 1975 年间,引擎分部的竞争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下面我将探究其后果。
因而,在这一章里我将指出,过去 30 年来,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的劳动过程变化是阶级斗争与资本家的竞争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二者又是被更加宽阔的力量所形塑,对此我将在结论部分作简略讨论。但首先我要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假设——暗含在很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作组织的著述中——即劳动过程的变化是朝向合理化的内在动力的一部分,或者是由管理者的远见所培育的、管理策略深思熟虑的产物,并且在参与竞争和斗争中被促进,或者仅仅是追求效率的结果。
资方策动的变化
因为 1945 年至 1975 年间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引擎分部变迁的所有结果都促成了霸权性工作组织的巩固,一个显而易见的假设就是资方心怀这个目标发动了变化。根据这种“让步”的理论,资方为了预防未来的冲突以及保护企业和谐,发起变化并分配利益。也就是说,资方引入变化,不是作为斗争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斗争的预期,并试图获得工人积极的同意。在美国历史上的确有过一段时期,统治阶级的“开明”派颇具影响力,并设法引入这样性质的有限让步。[^3] 然而,充足的证据表明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的管理层不能在这个意义上划分为“开明”。所发生的多数变化是工会与资方斗争的结果,而并非如此造成的那些变化,正如我将要展示的,是引擎分部的竞争位置改变或资方内部竞争的结果。
让步理论预言,在斗争暂时沉寂的时期,组织性的变化仍将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的时期。但对工会与资方之间所签契约的考察则表明,吉尔公司几乎很少发生变化。固然,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公司实行了工资冻结制度,但为何不能实现工作条件的变化是没有理由的。相反,正是在战后,面对席卷全美国的更新了的劳动冲突,变迁被引进了。1947 年的协议第一次包括了工会干部“超资深”条款,此外,还有公布空职的规定、工作分类计划以及合理化的工资结构。随后,资方激烈抵制降低操作工能够行使工厂范围内的资历之前必需的持续受雇的时长,从五年到两年然后又变为一年。
另外一个观察对让步命题提出了质疑。根据“企业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解释,工作组织内让步的分布是大企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然而,考察协议与访谈工会干部表明多数主要的组织性变化发生在战后到联合公司接管以前。据一名任期跨越了两个时期的地方工会主席所言,联合公司在分配福利上比较慷慨,并且相应地不愿意协商工作组织的改变。与之相反,吉尔公司资金较少,并且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市场里运行,较少会同意直接的经济让步,从而,作为讨价还价的结果更乐意引入组织变化。所有这些并不是要说在美国工业中没有一个“开明的”企业经理群体;然而,在吉尔公司或联合公司的引擎分部没有他们的身影,并且,他们不是促成巩固霸权性工作组织的那些变化的执行者。
在质疑让步理论中,我强调了资方所抵制的改变——作为资方与工会冲突结果的改变。然而,还有另外一些改变,它们看上去 是无需斗争就被准予的“让步”——尤其是,那些涉及了工时计划员、检验员和工头的改变。产业工程师以许多方式解释了他们自身在车间的消失。首先,他们说,1945 年时泰勒制依然非常流行,资方保留着对秒表的信任;其后,管理哲学发生了一次变化。其次,方法已经专业化了;产业工程师现在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计算速率。第三,变革技术比改变速率变得更加重要和有利可图。美国产业工程师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的一名官员说,产业工程师考虑到他们现身车间可能会引起的敌意而不愿意去车间给工作计时。他也抱怨产业工程师现在如此的不熟悉工作与操作,以至于他们都不能够准确地计时。他们还不能察觉操作工蒙蔽他们。[^4]
一些类似的理由被用于解释车间质量控制的放松。质量控制哲学的变化导致了责任从检验员转移到操作工。此外,低质量的根源现在较少在手艺上而更多在设计上被发现。不是坚持在车间提高质量,更多的是坚持供应商——例如,铸件供应商——使其产品达到特定的质量要求。一名质量控制经理也向我证明,他正在设法削减更多的检验员数量,因为可以通过使用精细的统计技术而轻易地测定品质不良的问题所在。附加说明一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检验员在公司的会计体系内被归属为经常性开支,在可能的情形下要削减。并不令人吃惊,一个好的质量控制经理并不容易坐稳位子,这职位的人员调换率非常之高。
根据人事经理所说,管理风格从权力主义到服务取向的变化反映了工人责任增长的转向。这一看法认为,人们不能再以过去的方式对待他人,因为雇员现在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更不愿意容忍专制的权威。现在必须劝说而非命令,或者,就像莫里斯·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所说的那样,操纵而非支配。[^5] 哲学中的这一变化反映在了与麦格雷戈(McGrego)、利克特(Likert)、阿吉里斯(Argyris)和杜克尔(Durcker)等名字相联系的人际关系著作中。这些作者认为,遍布政治舞台的民主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企业环境中。车间变化是社会远离威压趋向劝说的普遍趋势的表现。
这些产业工程、质量控制以及职员管理的变化看上去是开明管理层的主动行动。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为霸权性工作组织的兴起提供必要条件,也没有为之提供充分条件。从而,资方及其学术代表所认为的具有因果效应的哲学变化,主要是由其他力量所带来的变化的合理化。关于企业组织的人际关系视点的延续,方法部门从车间撤出以及检验员的减少,反映了斗争与竞争带来的生产中的关系以及技术的真实转变。然而,如果把管理哲学的变化视为没有它们自身因果效应的而仅仅是劳动过程变化的反映,那将是错误的。它们也是不同管理部门的冲突性利益的反映。资方内部各种各样的利益有与之对应的职业协会,其目标在于维护、促进某些部门的利益,对抗其他部门的利益。人事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产业工程等全国性协会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和革新的资源,将他们各自的特殊利益当作为资方整体利益来促进和呈现。然而,这些不同部门增加各自不相协调的利益的能力被企业能否存活的共同的利益所限制了,也就是说,被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的竞争所限制了。[^6]
竞争
公司能以后果迥异的方式来应对竞争。在此,我将讨论四种可能的应对方式:第一种,引入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第二种,通过降低工资与资本置换率(rates of capital replacement)来削减成本;第三种,加速,即强化劳动消耗;第四种,专门化和/或扩张,从而带来因经营规模扩大而得到的经济节约。我将首先考察吉尔公司对竞争的回应,接着考察联合公司的回应。
较小的公司在应对竞争上选择也较少。因此,吉尔公司无法获得大笔资金投入到新机器、工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上。当罗伊离开时,他的确注意到了吉尔公司在装配一些新的自动机床,但当联合公司 1953 年接管时,固定设备处于一个需要维修的不良状态。此外,吉尔公司除加工大范围的产品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加工车间,按照购买者的特殊要求生产,依赖一些小额订单维持生计。它的规模既不够大,也缺乏有充分把握的市场来专门生产某一产品。只有当战争带来大量的坦克与救生艇引擎的政府订单时,它才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扩张。战后,它不得不缩减产量,再次变得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入一个更大的企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吉尔公司依赖维持相对低的工资和福利,以及低资本置换率来应对竞争。因此,罗伊和他的同事总是抱怨工具和设备不充足。当然,加速生产也是吉尔公司应对竞争的另一种方式,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一方式采取了削减价格的形式。在吉尔公司的管理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竞争导致了斗争的加剧。
联合公司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了竞争,反映出受其支配的资源较多及其占有的引擎垄断市场。联合公司没有加速生产和降低工资,而是引进了新机器,取消了没有利润的生产线,并且最终将产品限制在柴油机上。1957 年时,联合公司让自己人担任原吉尔总经理。工具、机器和设备都升了级。库房也被重组。原有生产线被取消,1961 年时部门一分为二,引擎车间搬到距吉尔公司旧的四层建筑一英里之外的一栋新的单层建筑中。作为上述多方面合理化的结果,有的或许促进了机器工具产业的发展,某些辅助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因此,装置工(layout men)的数量有所减少,他们的职责是在没有标准化设备时负责细致的程序设定。由于需要计时的工作减少,以及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标准化就意味着操作能够被同步计时,工时计划员的职能也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方法部门则越来越专注于方法的修正中,也就是说,改善技术和组织而不是给工作制定速率。一旦给定了一个速率,操作工很少再被计时。当雇员自己都有能力购买的经过改进的检验设备可任意使用时,质量控制的更大的责任就转移到了操作工身上。与吉尔公司相反,在联合公司,竞争带来的改变,致使车间斗争减少。
此外,工厂整合进一个大企业缓和了竞争本身。乍看起来,引擎分部现在有了一个垄断市场,从而不直接遭受开放市场严酷性的影响。每年年底,基于从联合公司其他部门接到的引擎订单以及产品的预计成本,引擎分部会起草一个来年计划。引擎价格是年度固定的,利润率不高。如果引擎分部实现了体现在计划中的各种目标,在理论上而言,高级经理就会获得分红。未能实现目标以及招致经济损失的事情常常发生,但不会产生当工厂在一个开放市场自主运作那样的破坏性后果。企业会承担损失,尽管部门经理会受到处罚。(当我被雇用时,引擎分部的总经理由于工厂的不良业绩被解雇了。)[^7] 因此,创造利润的失败并不会以削减工资、加速等形式直接报应到劳动者身上,从而并不一定加剧斗争。在企业层面上,比起较小的公司,竞争也受制于更大的控制。第一,存在有各种形式的非正式价格控制(联合公司牵涉到了一件有名的反托拉斯讼案中)。第二,一条生产线的损失可被另一条获利生产线抵消。第三,无论如何,大企业有隐藏或勾销损失的各种会计策略。总而言之,联合公司接管吉尔公司导致了斗争的减少,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产品的合理化直接减少了车间层面的斗争。第二,引擎分部在一个更大企业内的角色,加上企业自身寡头卖主垄断的位置,促进通过外在化成本来消化斗争。
斗争
我们已经说明,吉尔时期竞争是如何在车间层面产生斗争,而在联合公司时期却又具有减少斗争的效果。但是,斗争既发生在谈判桌前也发生在车间里。什么决定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这种斗争对进一步的斗争和竞争产生什么后果?正如我所指出的,因为无力负担工资增长和附加福利,吉尔公司显得更愿意协商工作条件和组织的改变。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以及内部国家的合理化从而开始了——发生在战后至联合公司接管之前。1954 年时——在吉尔公司的管理之下,但当时已经是联合公司的一个部分——相当多的冲突之后,一个巩固内部劳动市场的突破达到了:裁员时可在全厂范围利用资历挤掉别人所需要的持续受雇时间从五年减到了两年。其后,在联合公司的管理下,竞标体系改进了,工作空缺必须张贴在布告牌上。值得注意的是,内部劳动市场的运行同样受到了技术变革的促进。由于改进了的机器并不像比较不可靠的老机器那样要求同样的技术和经验,它们提供了增加工作之间流动的机会。尽管联合公司的确对工作组织的几个变化做出了让步,但这样的变化大体上在吉尔时期就已启动并确立了。然而,联合公司引进了新的附加福利,例如补充失业福利和养老金计划,其他一些诸如假期工资的福利也得到了改进。在联合公司接管后,工资相对于制造业的均数也提高了,见表 6。
表 6 吉尔公司/联合公司工人收入从 1937 到 1975 年的变化
| 激励工的基本工资 | 3级操作工的预期速率 | |||
|---|---|---|---|---|
| 年度 | 小时工资 | 美国制造业平均百分比 | 小时工资 | 占美国制造业平均百分比 |
| 1937 | $0.621/2 | …… | …… | …… |
| 1942 | 0.75 | 95% | …… | \ |
| 1945 | 0.79 | 83 | …… | …… |
| 1947 | 1.09 | 92$2.06 | 175% | |
| 1949 | 1.15 | 86 | 2.14 | 160 |
| 1951 | 1.26 | 83 | 2.28 | 151 |
| 1952 | 1.35 | 85 | 2.39 | 150 |
| 1954+ | 1.471/2 | 85 | 2.54 | 147 |
| 1956 | 1.741/2 | 92 | 2.79 | 148 |
| 1959 | 1.94 | 92 | 3.04 | 143 |
| 1962 | 2.26 | 98 | 3.38 | 146 |
| 1965 | 2.52 | 100 | 3.68 | 146 |
| 1968 | 2.83 | 98 | 4.22 | 147 |
| 1971 | 3.49 | 102 | 5.151/2 | 150 |
| 1974 | 4.40 | 104 | 6.13 | 145 |
来源:吉尔公司/联合公司收入数字来自工会合同。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数据(不包括加班)来自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手册》(1974),表 96,第 21 页。
*预期速率=125%。3 级是激励工人的最高级。
+1954 年合同是第一份与联合公司签订的合同。
谈判桌上的这些斗争的后果是什么?正如我在第三部分表明的,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的兴起,以及将工资和附加福利与资历相联系有助于减少车间的斗争。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减少了工头的权力,减少了工时计划员与操作工的斗争,提高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内部国家的巩固以及工业公民(其权利在申诉机制中得到规定)的建构进一步调整了斗争。简而言之,谈判桌上的斗争具有吸收车间斗争的某些形式以及减少另外一些形式的效果。从而,在联合公司的管理下,斗争的后果既增强了竞争减少斗争的效果,又与之相结合。
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尽管其解决之道超出了本书的论述范围,即谈判桌上斗争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斗争部分地反映了车间的动力以及特定企业的资源,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斗争也部分地回应了遍及美国工业界的谈判模式的普遍运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United Auto Workers)与主要的汽车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以及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与美国钢铁(United States Steel)之间签订的协议提供了并在继续提供——先是为吉尔公司,接着为联合公司——协议范本与谈判的条款议程。工作分类方案、竞标体系、附加福利以及诸如此类的制度,是跟随着钢铁等基础工业采用之后引进的。为何协议遵循这些领头行业(汽车和钢铁)的方向有待进一步探究。[^8]
然而,后果是有趣的。一旦内部劳动市场被引进它就变成了进一步阶级斗争的领域。工会为了延伸竞标新职位与替代资历浅者的权利而斗争,以使这些权利不只在个别部门而且还在整个的工厂实行。接着他们为了降低可以利用资历挤掉资历浅者所必需的年资以及诸如此类的事而斗争。从而,尽管资方可能最初支持引入一个内部劳动市场来作为合理化工作结构的方式,但此后关于竞标新职位与替代资历浅者的斗争遭遇了来自资方的强力反对,他们感兴趣的是灵活地部署劳动力。相似地,福利体系和系统化工资谈判的出现意味着增产鼓励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自 1945 年里就已大幅减少了。换句话说,超额的金钱诱因已经衰落了。从而,集体议价不仅是向资方保证工会支持履行协议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此外,集体议价的内容 通过促成同意的组织所需条件,促使减弱了车间的战斗水准,至少在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产生了 1930 年代地方工会的推动力来自好战的普通会员。在吉尔公司,工会面对资方无情的反对必须暗中组织。[^9] 早期的战斗性在战后被阶级斗争的组织在谈判桌上吸收了。正是 1930 年代工会斗争的成功带来了从成员那取得工会控制权的变化。接下来我将提出,美国现有工会的保守性部分源于车间经验,它允许一种对普通成员不做回应的工会官僚体系的出现。^10 工会领导是否意识到了他们与资方之间就“企业民主”进行斗争的自利的后果,有待进一步调查。
在英国,存在着强劲的工会干事运动和好战的普通成员,为何美国经验与英国经验竟然如此不一样?在相似的工业里,比起美国工人,英国工人设法握有对车间更多的控制权,[^11] 并且,那里的内部劳动市场主要是由工会而不是资方组织。例如,在一个类似于联合公司机械车间的某车间里,关于谁来完成工作是英国工会说了算。但为何会有这些差异?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工会化和机械化的相对发生时间。在英国,工会在 20 世纪机械化的强力推进之前就已确立了,然而,美国的情形则相反。从而,在它们形成之时,美国企业工会不得不把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剥夺作为既成事实,然而,在企业工会主义出现较早的英国有可能抵抗这种权利剥夺,从而以这种方式奠定了更激烈的工会运动的基础。近来,一些大型英国企业正在设法朝向更加美国化的工作组织、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的模式转变。[^12]
结论
1945 年至 1975 年间劳动过程的变迁是三个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产物,即资方不同层面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争斗、企业之间的竞争与阶级斗争。为了在企业内增强其力量,不同的管理集团利用全国性协会来获得支持。这些外部的实体的确对资方内部斗争的后果施加了间接影响,但对此探究会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我们只需要这样说就足够了,即作为各部之间的对抗的结果,改变会发生在劳动过程当中。或许在产业工程师取代工时计划员这一点上体现得特别清楚。
资方内的冲突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发生在对车间工人回应的期待中。相互争斗的资方各层面所共享的利益——赢得与掩饰剩余价值——对任何层面可以采取的改变作了限制。然而,资方内部的冲突不仅是被预期的工人回应所限制——一种约束性力量;阶级斗争更直接的压力以及与其他企业的竞争同样起了限制作用。进行集体议价时,资方代表了与工会相对的共同利益。与之相似,当与其他企业竞争时,资方代表了一个统一的战线。在联合公司引擎分部,高级经理在完成年度计划目标时享有共同利益,这是由于分红与计划完成挂钩。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个别部门会将其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来表达。
正如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的竞争限制了资方内部的冲突,它们也彼此限制。一方面,吉尔公司的竞争位置限制了它分配经济让步的能力,并迫使它就工作条件而讨价还价;而联合公司的垄断位置以及引擎分部相对于公司其他部门的服务性角色不仅允许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并且还是保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的必要代价。另一方面,斗争获取了资方各式各样的让步,从而影响了公司的竞争位置。
虽然斗争和竞争限制了它们的相互变化,二者都在这些限制之内由另外一种力量所形成。吉尔公司的竞争位置在战后政府停止订单合约后发生了变化,当联合公司接管时又再一次发生了变化。第三章粗略地探究了联合公司在其多样化的产品市场上变动的位置,这些波动影响了引擎分部在母公司之外进入市场的门槛。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重要的是(指出):企业之间的竞争带来了新技术的引进,这可以重新形塑劳动过程。如果它不是被一个垄断市场所保护,而是处于直接竞争之中,比如说与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竞争,联合公司的引擎分部将不得不扩张或专门化,或者二者并行,以便能够引进更多的自动化设备。如果这样的技术变化可以改变劳动过程,什么力量决定新机械的形式呢?戴维·诺布尔指出,自动(数字控制的)设备的发展和生产的驱动力来自大型企业所关注的两件事,即将小机器车间挤出生意场以及增强对劳动过程的资方控制。[^13] 如果技术事实上并非中立的,并且其发展是一个政治的也是一个经济的过程的话,那么探究为什么研发与销售某一机器而不是另一机器就变得重要了。
阶级斗争同样被超出车间范围的力量所影响。首先,正是大企业谈判的契约确立了小公司斗争的领域。第二,斗争自身被公司在无需危及其存在的情形下能够做出让步的能力,以及由普通会员带给工会领导的压力所形成。我已经尝试呈现了斗争与竞争所带来的车间里生活经验的变化在过去 30 多年来是如何降低了工会成员的战斗力。
车间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对于美国劳工运动理论具有启发性。它表明在正统的美国工人阶级历史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工会作用若不参照劳动过程的变化就不能被充分理解。只有植根于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当中,企业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才可在协调资本和劳动利益中成为有效力量。在这项研究中我已提到了可能与这种霸权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劳动过程的变化。出于同样的原因,宣称仅仅是腐败的工会领导和贪污的文化,阻碍了工人阶级迈向阶级斗争的自发与内在的趋势不会令人满意。领导者部分地反映了被领导者的要求,文化的力量是与其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中相联系的。[^14]
要揭示劳动过程变化的根源,必须超越单个企业。同时,这些更加遥远的变化通过它们对阶级斗争和资本家的竞争的影响传达到劳动过程中。此外,斗争和竞争对于劳动过程没有产生什么独特的后果,诸如减少不确定性、分离概念与执行、强化车间斗争等等。相反,模式性的劳资谈判、竞争结构与产业工程等的改变,其效果是被已经存在的生产中的关系——也就是说,被掩饰和赢得剩余价值的需要——所形塑。本书的范围并不允许我探究这些遥远变迁的具体动力。相反,我将在下一章和最后一章呈现一幅更加一般的图像,它描绘了所有上述变迁得以发生的政治和经济语境的转型。
[^1]: 我假设第三部分中所描述的变迁以一种单线性的方式进展。尽管我们会看到吉尔公司的变迁与联合公司的变迁属于不同类型,但所有来自资方 - 工会合同内容的证据都指向那个方向。
[^3]: 这种行为与进步年代国家公民联盟有关,并且可能为 20 年代的“福利资本主义”提供了基础。参见: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美国历史的轮廓》(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 1961);詹姆斯·温斯坦,《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司理念,1900—1918》;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保守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斯蒂芬·沙因伯格(Stephen Scheinberg),“公司劳动政策的发展,1900—1940”(“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 Labor Policy, 1900—1940”,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6)。
[^4]: 米切尔·费恩(Mitchell Fein),一名杰出的专业工程师,在一封给我的私人信件(1976 年 8 月 16 号)中写道:
一般而言,我猜想目前工厂里的时效调查人员数目并不比 1944 年时少;这依赖于公司的政策、生产的类型、实施的业务、是否有激励机制等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同样地,通过运用经细致的实践研究而获得的标准数据,只要工程师们对业务将会如何实行有充分细致地把握的话,他们不必到工作现场去冒险就可在办公桌那制定标准。例行的现场工作在大多数公司已被取消,到目前为止它们有充足的数据而无需花很多时间在车间制定标准……强硬的经理尚未仔细考虑撤回时效调查人员以此作为减少工业冲突的一种方式。与之相反,只要增派更多的时效调查人员可以达到他增产的目标,他就毫不在乎,他不会关心冲突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
[^5]: “组织权威的模式变化:军事组织”(“Changing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959):第 473—493 页。
[^6]: 虽然从不同的经理那里以及在车间的所见使得我对部门间的各种斗争与联盟的确有所洞察,但它们过于零碎以至于不能证明我的分析。然而,不幸的是,关于资方内部政治的研究太少。不过可以参见,梅尔维尔·多尔顿,《管理者》(Men Who Manage, New York: John Wiley, 1966)以及汤姆·伯恩斯(Tom Burns)和斯托克(G. M. Stalker),《创新的管理》(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61)。
[^7]: 新的总经理于 1975 年 1 月上任,随即着手重组引擎分部,造成一些我在第八章叙述过的影响。随后的两年里,引擎分部每个季度都创造利润——一个几乎未预料到的功绩。然而,快到 1976 年底的时候,质量控制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令人头疼,因而,引擎分部面临着失去一个来自公司内部的大客户的危险。尽管 1953 年后引擎分部就已被联合公司接管,但它依然面临着诸多困扰吉尔公司的问题。工厂太小了,引擎种类又多种多样,以至于它无法具有竞争优势地销售其产品。除非扩张或是减少制造的引擎种类,否则这些是没有哪个经理可以解决的结构问题。
[^8]: 关于最大型的公司与最强大的工会之间的谈判,威廉·塞林(William Serrin)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视角,见《公司与工会》(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9]: 根据我所听到的各种解释,吉尔所在地的钢铁工人的组织是根据彼得·弗里德兰德(Peter Friedlander)在其《一个地方联合汽车工会的出现,1936—1939》(The Emergence of a UAW Locale, 1936—193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5)中所描述的模式而组织的。
[^11]: 例见贝农对利物浦的一家福特组装厂的描述(《为福特工作》[Working for Ford, London: Allen Lane, 1973])以及罗纳德·多尔对机械厂的描述(《英国的工厂——日本的工厂》第五章、第六章);勒普顿(Tom Lupton),《在车间》(On the Shop Floor,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63)。
[^12]: 见西奥·尼科尔斯(Theo Nichols)和贝农的《与资本主义共存》(Living with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13]: 诺布尔(David Noble),“事实之前:机械设计的社会选择”(“Before the Fact: Social Choice in Machine Design”),论文提交于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1978 年 4 月。
[^14]: 对工人阶级具体经验重要性的认识的增长在近年来的美国劳动史成果中也可见到,这些成果受到两位英国史学家著作的影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劳动者》(Labouring Men,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4)和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63)。例见,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十九世纪工人对机械生产的控制”(“Worker’ Control of Machine Produc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bor History 17 (Fall 1976): 484—509;同一作者,“‘新工会主义’与工人意识的转变”(“The ‘New Union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in Workers’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7 (Summer 1974): 509—529;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美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作、文化与社会》(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