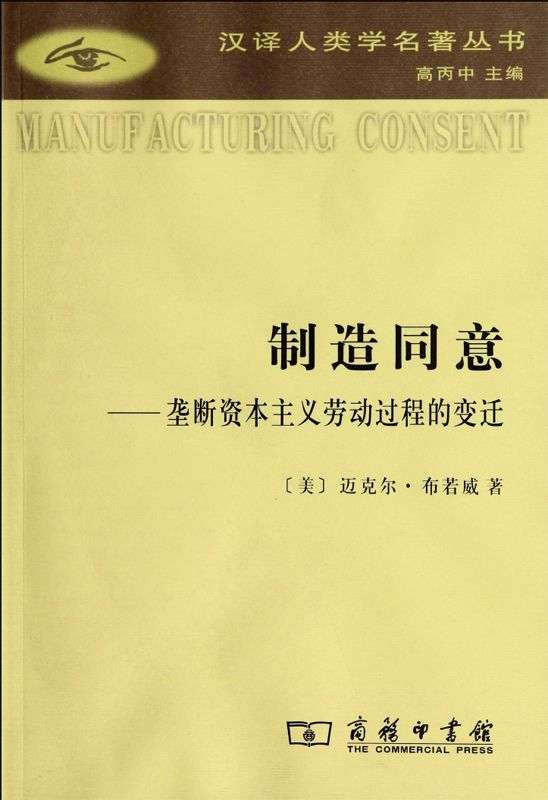第十二章 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第十二章 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通过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模式,我开始了本项研究,以此方式获知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独特性:同时掩饰和赢得剩余劳动。我们探究了促成掩饰和赢得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即工资劳动体系、工人从属于劳动过程以及市场的神秘效果。此外,尚有各种不同机制殊途同归,促成了相同的结果。
从而,在对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的劳动过程的先后考察中,我关注的是强制和同意的变迁模式,这是由相对自主的内部国家的发展、内部劳动市场的出现,以及工作组织和计件工资体系的变化所带来的。所有这些促成了个体主义的成长、等级冲突的散布以及资本家与劳动者、经理与工人之间利益的具体调整,从而也就促成了掩饰并赢得剩余劳动。我们可以把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之间的差异推断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两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专制的工作组织,威压明显地胜过了同意。在这种类型中,车间里的劳动的支出是决定生存——不只是劳动者的生存还是企业自身的生存——的关键。工人无法抵御那些凭自己心意雇用和解雇他们的经理或工头专断的怪念头,正如企业家和经理也没什么方法来使自己免受市场变化多端的侵袭。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工厂的专制主义。劳动过程的第二种类型——霸权的工作组织——基于同意压倒了威压。在这种类型中,工资或者说劳动者的生存与劳动的支出只有微弱联系,企业能够使自己隔离于市场,或是直接控制市场。市场的从属地位导致了工厂里的霸权。
这两种劳动过程的类型与资本主义的变迁如何联系呢?在这项研究中我走出了车间,转而考察市场、职业协会、学校、家庭、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工会与企业之间的斗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要理解劳动过程中变迁更宽广的意义,尤其是就我们所建构的这两种类型而言,必须颠倒顺序,首先大致地勾勒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只有这样才可能回归劳动过程,并将其转型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整体的一部分。
首先,我会回顾马克思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要点。正如我在第十一章中所述,资本主义发展有两个动力:斗争和竞争。资本家为了存活于一个完全市场之中,必须为了获取利润而相互竞争。按照马克思所说,他们通过增加无酬劳动——要不就是通过延伸工作日,要不就是当前者不再可行时(例如工厂法案[Factory Acts]实施后),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即降低用于生产工资等价物的工作日——来做到这一点。这种“必要劳动”的降低可以经由降低实际工资来实现,或是提高生产力和工资品(wage-goods),如此一来可使生产工资等价物的必要劳动数量下降。虽然这两种方法对于个体资本家而言都产生了持续的利润,增加无酬劳动的更常见的方式是通过暂时性竞争的收益来实现。透过强化或机械化工作过程,个体资本家可以增加其利润——但只能在其竞争者赶上之前。这种个体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性创新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三个后果。第一,强化了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第二,当某一资本家率先采用新机器继而所有资本家都采用时,那么在无酬劳动方面,所有的资本家又回到了他们的起点;但是利润率——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占工资、生产工具以及所耗原材料的比例——已经下降。第三,生产的持续扩张,伴随着工资的下跌或不变,导致过量生产的危机,这迫使资本家削减产量并闲置资金。简言之,市场迫使个体资本家创新并追逐竞争优势,但是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通过强化阶级斗争、降低利润率和造成过量生产的危机而威胁了他们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说,资本家为了生存不得不追逐个体利益,由此,他们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生存之中资本家的共同利益。
马克思分析的逻辑导致他去预期竞争资本主义的颠覆。当然,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正确的。然而,在将竞争资本主义的颠覆与资本主义的颠覆和社会主义的确立等同起来上,马克思是错误的。正如已经出现的那样,竞争资本主义孕育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斗争与竞争模式在其中已经变形。马克思忽视了完全不破坏竞争本身而缓和其最糟后果的可能性,他还忽视了阶级斗争不仅可能被资本主义决定变数范围的要素所遏制,还可能被利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如果工人设法获得了可以使资本主义更能让人忍受一些的让步的话。阶级斗争不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是其救世主。[^1]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了股份公司、托拉斯、卡特尔甚至国有化的出现取代市场的趋势。他们也意识到斗争被压制以及工人阶级状况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这种最后防线般的自我拯救的企图有着明确的局限。这种重构资本主义的反弹机制,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挣扎,注定要粉碎在革命的颠覆中。[^2]
如果竞争资本主义孕育了垄断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那么这绝非预先注定的,其分娩既不短暂也不容易。在 20 世纪的前 30 年里,尤其是在欧洲,的确有资本主义大厦将倾的时刻。[^3] 法西斯主义的登台既是资本主义强势的一种符号也是其式微的一种符号。即使是从 50 年后一个有利的位置来看,为何马克思错误地预计了资本主义的颠覆,或确切地说,它如何挽救自身仍然不清楚。的确,这已成为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各种形式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并且也假定了诸多解答。马克思分析竞争资本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灭亡的敏锐性,使我们有必要去修正他的理论,以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发展。马克思分析所基于的一些预设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不再成立。简而言之,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历史迫使马克思主义超越了马克思。[^4]
考虑到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国家保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20 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也就不足为奇了。它们都持有一个共同观点:首先在处理竞争资本主义的冲突上,接着在引导资本主义走进一个新时代上,国家都是关键的行动者(key agency)。一方面,国家接管了市场的功能并弥补了其他机制的不足。它通过计划、国有化以及诸如道路和邮电业等基础设施的提供来调整资本家之间竞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也通过反托拉斯立法、金融政策以及吸收“剩余”来防止过量生产的危机来调整上述关系。[^5] 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到组织斗争之中——使之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或是压制它们——如此一来,斗争便不至于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家通过瓦解被支配阶级来做到这一点,而这又是通过将生产行动者(资本家、经理、工人等)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个体(作为法律上、教育上、选举体系上权利平等的公民而被建构出来)之间的关系来实现;或是转变为政党、种族、宗教群体或语言群体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凭借这一方式,国家机器看似超然于阶级之上,或是具有相对于阶级的自主性。因为它们根据自身的逻辑来运行,不因任何阶级的意愿而被任意地改变。此外,这种自主性构成了保护资本家的政治利益——也就是他们在维护资本主义秩序上的阶级利益——的真实与必要的基础。因为要保护这些政治利益的话,国家必须时常同意对其他阶级的让步,从而违背资本家经济利益。正常情形下,国家不是在统治阶级的直接要求下,而是以一种或多或少地法律规定的方式运用威压;但在危机时期,国家可能会丧失其相对自主性,变成统治阶级恣意镇压斗争的工具。[^6]
在超越马克思,发展更加精致复杂的国家理论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很少关注到发生在企业里同样根本的变化。[^7] 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不仅涉及国家介入市场运作;资本家自身也设法征服市场并使之从属于他们的利益。这既包括了集中化——生产相似产品的企业合并到大公司中——又包括了中心化或垂直整合——单个企业同时扩张到产品和供应市场。显而易见,联合公司取代吉尔包括了这两个过程。吉尔在一个竞争市场中生产升降卡车和引擎,而联合公司是实际上控制了农用机械生产的少数几个公司之一。吉尔受限于它所生产的产品,并因此依赖于供应方和买方;联合公司通过兼并吉尔寻求再占据一个市场,即引擎市场,从而降低它对外部供应的需求。
集中化与中心化具有明显的工作组织的意味。如果处于竞争状态下,则供应与产品市场受控制的影响;于是,控制劳动市场也变得必要。控制某些市场而不控制别的一些市场将不啻为一个弄巧成拙的过程。正如联合公司使得引擎生产处于其管理之下,因此它也寻求通过内部劳动市场的发展而使劳动的供应和分配处于其控制之下。此外,它还寻求通过内部国家的申诉和集体谈判机制调整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
正如内部劳动市场那样,内部国家与总体国家都牵涉到对市场的驯服中,故三者也都涉及抑制威胁推翻竞争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如总体国家涉入更广阔的政治领域内的斗争组织中,因此,一个调整工厂内部斗争的内部国家也显现出来。与其说内部国家是公司的一个威压工具,不如说它是一套制度,它组织关于生产中的关系的斗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层面上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培育了企业顺畅运作的方式。[^8] 从而,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市场限制了管理层的任意决定,制度化了对让步的承认,并因而具体地协调了管理层与工人的利益及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益;(它们)将工人建构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并且培育了竞争、个体主义和流动性。不过,内部国家不只能组织斗争,还能把斗争分散在各企业之间。它还能防止斗争超出企业层面而联合起来指向总体国家。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考虑了生产过程中人员分配,以及组织各方关系斗争的各种机制的变化。但我们如何解释关系本身以及它们所引致的行为呢?伴随着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它们有变化吗?哈里·布雷弗曼宣称,垄断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是技术的毁灭,或用他的话说是概念与执行的分离(separation of conception and execution)。实际上这一技艺破坏的过程是不均匀的,它既发生在竞争资本主义之下,也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此外,如果我们要去理解劳动过程中的变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注意一旦技术被剥夺劳动过程以何方式重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注意一旦概念与执行相分离,前者得以支配后者的特殊机制。只要生产中的这些关系是由技术所形成的,我们就几乎无法做出一般化的推论,因为机器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多样。^9 然而,关于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影响生产中的关系及相应行为的方式,我们仍可得出一些大致结论。二者都为适应劳动过程的工人提供了非常有限但却关键的自由。规则的出现及其对资方干预的限制,开启了一个选择的空间,工人们在其中可以把工作建构为一场游戏。工人被吸纳进入游戏,以此作为一种减轻剥夺水准的方式。但是参与却具有形成对规则的同意的效果,这既界定了选择的条件又界定了资方任意决定的范围。从而,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它们所限定的行为产生了同意。[^10] 当然,选择空间的范围受到技术需要的影响,然而不论多么狭窄,其存在却是至关重要的。
工作的霸权性组织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并不普遍。先进资本主义的不同部门采用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形式,绝非全都制造出像联合公司发展出的那种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市场。就像农业综合企业的工作组织清楚显示的那样,甚至并不是所有最大的企业都建立了霸权体系。因为竞争部门中的劳动过程没有很好地与市场相隔绝,有人可能会争辩:一般而言,竞争部门较少从引进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中获利。这些制度的成本也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提高价格而消化掉,而在垄断部门则可以这样。另一方面,将垄断资本主义竞争部门里的劳动过程等同于竞争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是错误的。即使在它们没有组成工会的地方,竞争性产业也发展出了初步的内部劳动市场、申诉程序以及集体讨价还价。简而言之,竞争部门所见到的劳动过程既展示了专制体系又展示了霸权体系的特征。正如劳动过程的形式在整个垄断资本主义里不是一致的,甚至于没有趋向一致的趋势,在所有先进国家中它也是不一致的。从而,即使是在其垄断部门里,英国的内部国家与内部劳动市场所采用的形式,与日本的形式差异较大;美国所采取的形式则介于两者之间。^11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论述中得到了灵感,但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出现则代表了一个更根本的新出发点。对于马克思而言,在所有前共产主义社会中,男人与女人涉入其中的社会关系是“必不可少且又独立于他们的意愿”,也就是说,它们强迫人们以某种特定方式行动。从而,资本家想要以资本家的身份生存下去,除了竞争和积累之外别无选择,就像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以换取工资之外别无选择。此外,工人们被迫按照劳动过程的指令而尽可能地既快又卖力的干活。这里没有选择的空间,理性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并独立于承载这些关系的人们,就像商品拜物教的经验独立于心理结构(psychic makeup)。并非对物质私利的追求激励了个体,而是资本主义特殊的理性和它所生产的特殊需求导致了人们以特定方式行动。封建主义关系所产生的理性和需求则导致了迥然不同的行动类型。
诉诸心理学是解释为何马克思的预期没有实现的另外一种方法。关系与实践之间的连接并不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因而有必要去考察心理机制的运作以此解释:第一,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参与到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第二,为什么它拥护资本主义的更新。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以其最简单的形式指出,正是人们在各种生活领域中,尤其是在家庭和学校潜移默化而来的意识,形塑着他们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回应。一种更加深奥的陈述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的借鉴中可以找到,其旨趣特别指向法西斯主义及其诉求。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使马克思的观点成为现实,即个体只不过是执行资本主义关系逻辑。不过,马克思视之为生存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则以明显的心理学术语来表述,即视之为具有自主性的自我的毁灭。这与马克思的分析并不矛盾,不过却反映了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竞争资本主义保留了抵抗和阶级斗争的舞台,但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个体精神中抵抗资本主义支配结构的能力却被剥夺了。家庭不再培养早期资本主义中具有反抗性和独立性的个体。相反,人们直接被更宽泛的制度——大众媒介、文化产业等等——形塑,并屈从于它们。主体性以及有意识地反抗统治的舞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当做操纵的纯粹客体的个人。垄断资本主义试图按照它的理性形塑我们真正的性格。[^12]
就像诉诸国家一样,诉诸心理学中,劳动过程的转型被遗弃了。在本项研究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我设法回到马克思最初的关注,为此我提出劳动力到劳动的转换独立于工人们带到车间的各种心理结构——性格或意识。工作中的行为大致可以根据劳动过程的组织、内部国家以及内部劳动市场来说明。同意是在车间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它并不依赖于学校反复灌输到人们头脑中的合法性或家庭里的性格形成。即使是在外来意识的确形塑行为的边缘情形下,其具体影响也是由工人再生产过程中的位置决定的。
当然,生产行为以及同意的再生产的确依赖于工作之外所形成的,并且为所有工人所共有的某些最小限度的人类特质,诸如通过语言而沟通的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建构机制(例如游戏,它补偿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的损失)的倾向。我并不认为工作之外所发生的事对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认为个体是车间用来塑造劳动男女的不成形的陶土块。更确切地说,工人们带到车间的性格与意识的差异性只是略微解释了车间行为的差异性。人们在工作组织中的位置则对这些行为作了最充分的解释。但至少有两个限制性条件需要指出:第一,在此我所谈论的是霸权性和专制性工作组织。在那些既非专制也非霸权盛行的,不怎么与外界分离的劳动过程中,外部因素对工作行为施加影响的空间则比较大。第二,在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危机爆发时期,一旦霸权体系崩溃,人们头脑中的意识以及他们所形成的性格就会在塑成他们的行为中变得至关紧要。
总而言之,为了解释采取垄断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复辟,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聚焦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没有展开的那些领域。与此同时,它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观点,从而漏掉了其变化的重要性,尤其是工厂抑制斗争以及制造同意的能力。国家、学校、家庭、文化以及个性并非不重要,但唯有通过把劳动过程的转变作为起点,它们的重要性才能被评估。
这对于研究危机尤为重要。突出某些矛盾与想象某种危机是非常时尚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话语里一个兴盛的领域。的确,似乎资本主义显得越稳固,我们就越悲叹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鸿沟,我们对新危机的寻求就越拼命。然而,在本项研究中我抵制住了这种诱惑。相反,我提出局部危机——即生产之际出现的——确实是前景黯淡。别人能言善辩地主张,资本家只有以外化斗争或是把斗争转移到更广的政治领域——在那它们变成财政危机或合法化危机——为代价,才能换得经济上的和平。不幸的是,这些是抽象的危机,如同真实世界的产物,只是马克思主义者想象的产物。[^13] 此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危机既为被统治阶级又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机会。它们是资本主义恢复稳定性和拯救自身的方式。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危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悲观把我们带到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第三次超越,这再次由 20 世纪的事件所引起,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马克思有时谨慎地预期,社会主义会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以竞争资本主义的崩溃为前提的。然而,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不仅是延迟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反而,可以令人信服地提出,这使得社会主义更可能先出现在不发达国家。[^14] 透过重构经济与国家,也透过将世界的“边缘”地带吸纳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垄断资本主义赢得了稳定。对于先进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不均衡的发展;而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更严重的不发达。与此同时,后殖民国家压制性国家机器的扩张,反映了对被持续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的不断抵抗,以及对其他出路的寻求。从而,正是在第三世界,或许包括某些欧洲国家,进行了最重要的实验,并且社会主义正在日程之上。
[^1]: 卡斯托里亚蒂斯,“论工人运动的历史”,Telos no. 30 (Winter 1976—1977): 35—36。
[^2]: 因此,恩格斯在 1880 年写道:
在托拉斯中,竞争的自由转向了它的反面——转为了垄断;没有任何明确计划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变为了社会主义社会有明确计划的生产。当然,到目前为止这都符合资本家的利益与优势。但在这里,剥削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它必会崩溃。没有哪个国家会忍受由托拉斯进行的生产,忍受一小帮股东对社会的厚颜无耻的剥削……生产与分配的宏大机构转变为股份公司、托拉斯与国有财产表明了资产阶级对于那个目的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它(国家)越是通过接受生产力来推展,它实际上就越来越变成是国家性的资本家,它所剥削的公民也越多。工人们还是工资劳动者——无产者。资本主义关系并未瓦解。它的确濒临危机。但危机终会导致颠覆。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方案,但其中所隐藏的却是构成解决因素的技术条件。见“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与科学的”(“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The Marx-Engels Reader),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编,New York: W. W. Norton, 1972,第 632—634 页。
[^3]: 当然,关于这一时期有无数的解释,尤其可参见: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重铸资产阶级的欧洲》(Recasting Bourgeois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尼克斯·普兰扎斯,《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治》(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至于美国的例子,见詹姆斯·温斯坦,《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司理念:1900—1918》;加布里埃尔·科尔科,《保守主义的胜利》;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美国历史的轮廓》。
[^4]: 不能过多地重复这一点,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简单的是马克思著作机械刻板的重复,而是对于马克思著作对资本主义及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的理解的不充分的回应。美国社会学家仍未普遍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像其他人一样可以从历史中学习,他们继续忽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系统进程的预测在多数先进工业社会已经被证实是无效的”,以及他的“教条,无论在他那个时代有多重要,已经被理论经济学中的技术发展所抛弃了”。从而,马克思主义降为了“想要为他们各自社会的贫困大众代言,并且在最近阶段要为整个贫困社会代言的那部分知识分子的”教条(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卡尔·马克思社会学的几点评论”(“Some Comments on the Sociology of Karl Marx”),载于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7,第 127 页,第 109—110 页,第 128 页)。这些来自于美国社会学理论大师的评论,明显忽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异同。正如卢卡奇(Lukács)所写那样:如果研究表明马克思所有的“预测”是错误的,“每一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会没有保留的接受这些现代事物,从而将马克思的所有论点全然抛弃——一刻也不需放弃他的正统地位。”《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8),第 1 页。
[^5]: 关于国家干预的当前理论,参见: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国家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克劳斯·奥费(Claus Offe),“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及政策形成问题”(“The Theory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and the Problem of Policy Formation”),收录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压力与冲突》(Stress and Contradiction in Modern Capitalism),利昂·利德贝里(Leon Lidberg)、罗伯特·奥尔福德(Robert Alford)、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与克劳斯·奥费编(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D. C. Heath, 1975),第 125—144 页。
[^6]: 关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压制与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尼克斯·普兰扎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3)。所有这些著作的灵感皆来自于马克思的政治作品,尤其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和《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7]: 当然,也有显著的例外,例如保罗·巴兰(Paul Baran)与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66)。
[^8]: 关于美国早年试图调解劳资关系的情况,参见:詹姆斯·温斯坦,《自由主义国家的公司理念》,斯图尔特·布兰德斯(Stuart Brandes),《美国的福利资本主义,1880—1940》(American Welfare Capitalism, 1880—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戴维·布罗迪(David Brody)就此提出了有趣的看法:如果没有大萧条,1920 年代达到其高峰的福利资本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美国的工业关系也会保持其家长制路线。(“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衰”(“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lfare Capitalism”),收录于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The 1920’s,约翰·布雷曼(John Braema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戴维·布罗迪(David Brody)编(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 147—178 页。直到二战之后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才恢复了它们的优势地位,这次有了组织化劳动的推波助澜。
[^10]: 同往常一样,阿尔文·古尔德纳找到了扳机,他写道:
因此,对于韦伯而言,权威因其是合法的而获得同意,而不是由于它唤起了同意而成为合法的。因此,对于韦伯而言,同意总是视为理所应当的已知数,而不是一个其来源应当追查的未知数。从而,他从未系统地分析那些促成或阻碍了同意的出现的真实的社会过程。[《工业科层制的模式》(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54),第 223 页]
不幸的是,古尔德纳临阵退缩,没有扣动扳机。
[^12]: 参见第八章注释 4。
[^13]: 这并非要表明资本主义已经以各种方式解决了它所有的主要问题——1950 年代有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就曾那样假设——而只是认为,像奥康纳和哈贝马斯那样的理论家,未能论证随着先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所强调的问题必然会变得更加糟糕,危机也会加重。此外,虽然他们意识到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系统危机与社会危机有所区别,他们并未表明一种危机如何导致另一种危机——人们如何意识到这些假定的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
[^14]: 葛兰西或许是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认识到,生产的前资本主义模式的缺席对于美国相对平稳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他似乎忽视了奴隶制这个显著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他提出,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这样被封建主义的寄生余孽所阻碍的国家里只会不均衡地发展。迈克尔·曼近来尝试将更具革命性的工人阶级的出现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持续存在或近来的解体联系起来。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关于世界范围的累积以及不平等发展的理论,或许是整合他们的主要理念——即社会主义的开端出现在低度发展的世界——最全面的。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迈克尔·曼,《西方工人阶级间的意识与行动》(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among the Western Working Class, Cambridge, Eng.: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3);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