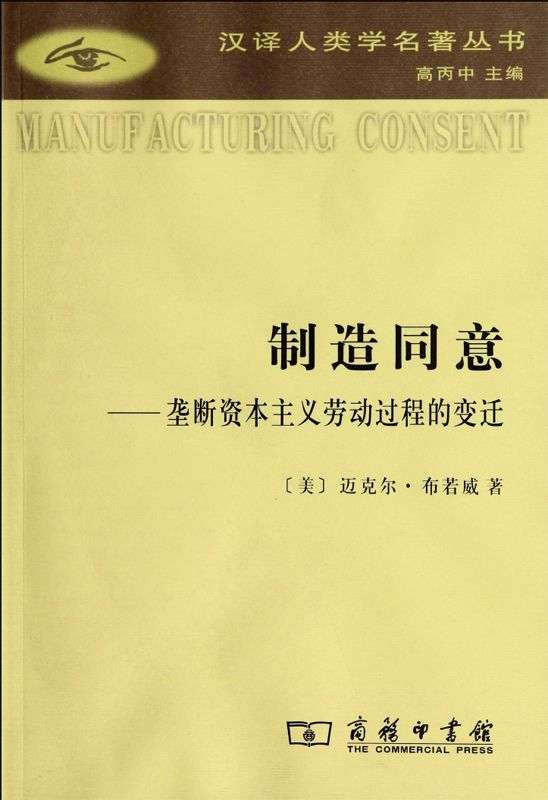附录—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附录
比较的视角:赞比亚矿业的变迁与延续
工业行为的变迁主要根源于工作组织的变迁。这是第四和第五部分的主题。通过考察市场短期波动的影响(第八章)、外部变化对工人意识的影响(第九章)、车间斗争的动力学(第十章)以及过去 30 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竞争变化的效果(第十一章),我阐明了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这些章节中所展开的论述应该可以适用于工业行为的国际性变化,及其在单一国家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根据那一论述,不同国家机械操作工行为的差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机械车间组织的差异来解释。那些更加传统的观点认为,国民工作的特性是劳动者脑袋里就带有的以及在工作场所之外形成的态度、观点、倾向等的作用。个体是民族文化的容器与执行者。发展理论的基础是:不发达国家的工人是“传统”取向的,或者是被限制在一套原始忠诚内,从而他们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工业秩序的要求。更加复杂的观点则认为,民族文化不仅通过社会化机构影响个体意识,而且还塑造工业企业的形态。^1 后面这一折中主义的立场并未试图去理解关于人类行为的两种不同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它也没有发展出一种理论,以此理解工业组织与政治和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在其他文章中已经展示了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如何塑成机械车间的组织,以及这些组织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车间里工人的行为。[^2] 早先的这一研究可以支持我在这里详细阐述的理论,不过,若比较不同国家中造成工业行为形式具有很大差异的产业将会更加有用。因而,我在这里援引了赞比亚铜矿业发展的历史,因为这提供了一个与世界其他地方矿业对比非常鲜明的例子。我将力图展示工作组织如何透过殖民政治秩序所塑造的斗争形式在历史上发展出来。只有当劳动过程发展出了与殖民地政治经济的兼容性时它才具有相对自主性。据此,殖民地的秩序在独立后发生了变化,劳动过程相对的自主性就陷入困境。但即使是在这样相对动荡的局势下,矿工在矿场内的行为依然继续回应工作组织,而不是回应变动中的政治秩序。
相对自主性的创造与再生产
矿业组织鲜明的特征起源于地下矿藏不可避免的环境不确定性。工作组织无法控制地质环境,便采取了两种相反的方式适应不确定性。一方面,工作群体可以被当作自身行为的决策者,独立于资方的监管。一个自我调整的群体可以对紧急事件、危险和地下矿藏的不可预知性做出必要的快速调整。[^3] 另一方面,地下采掘面的迅速调整也可以由一个严格的、强制的与训练有素的工作等级组织完成,其中,下属不加疑问地听从上司指令,而上司则单方面地决定组织如何应对不确定性。这样一种组织通常与资方完全缺乏对下属高效工作的意愿与能力的信任相联系。[^4] 在他们对英国煤矿业的研究中,特里斯特(Trist)等人断定:
长距系统(long wall systems)因其很大程度的分化,从而比单点系统(single place systems)要求更多的整合;但是组织的惯例模式已经把传统的、自我调整的周转团队分解为一些各管各的单一任务群。这些群体为了要完成整个工作循环中不可分割的初级任务,就要完全依赖于外部控制。现有的通过工资体系来管理的模式只能部分地提供这种控制。全面控制要不就需要一种既不可行又难以接受的高度强制,要不就需要一种意味着不同组织模式的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5]
尽管有机械化,由工资体系控制的自主的自我调整的团体依然是工作组织最有效的形式。
与之相反,南部非洲矿业(南非的黄金和钻石矿业、津巴布韦的煤矿以及赞比亚的铜矿)的组织形式可以用英国的“不可行也难以接受的高度强制”来形容。为什么矿业在南部非洲会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组织形式?在此没有篇幅以深入到南部非洲矿业的历史发展细节中去;一个简略的概论就足够了。[^6]
黄金和钻石矿业的组织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作为一种转包体系始于南非。非洲人被成群地集中起来,使用采掘的初级技术,为一小群白人“企业家”干活。当这种原始的运作不再提供红利,采矿公司就诞生了,它运用外国资本来建立大规模的工业组织,其工资劳力有两种来源:技术工人和督工来自英国,非技术工人从邻近的非洲土地上招募。严格的“肤色障碍”区分了为白人保留的工作和留给黑人的工作。成群的非洲劳工听从于白人“组头”(section boss)的独裁命令。
工业组织内缺乏节制的强制(通常包括专横的身体暴力和言辞辱骂)是将劳动力驱离土地的强制机制的一种延续。在南非,对非洲人既征土地又征税收的制度迫使他们进入现金经济中。这样一种复合体——一个总体制度,其建立用于控制雇佣于矿山的工人在工作之外的行为——确保了对殖民地政治经济漫无节制的权力的屈从。当没有被矿场雇用的时候,一系列通行法律的执行会强迫非洲工人回到那个所谓“保留地”的逐渐缩小的土地上,那些法律曾经控制(并且依然控制)他们的迁移。尽管英国圈地运动永久地把劳力驱逐出土地,然而在南非,土地征收未能形成完全没有土地的无产阶级。所谓“保留地”是作为外化和消化的城市社会控制问题,以及降低采矿公司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的一种方式而被建立的。黑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从属地位与白人工人的力量形成了一目了然的对比,后者一贯以作为非洲人为代价而获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强制性的科层化工作组织的起源就相当清楚易见。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意味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外部劳动市场以及一种独特形式的政治和经济支配。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从而将其特性铭刻于工作组织之上。
南非的金矿为南部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化工作组织提供了模型。这种矿业强制形式的广泛性对任何技术决定论都提出了严肃质疑。这表明劳动过程的形式反映了殖民地秩序的要求及可能性。赞比亚的证据表明工作组织,或许甚至是技术本身,都有可能出于强制性控制与规训劳动力的目的而被相当有意识地采用。[^7]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概述一下 1971 年——赞比亚独立 5 年后——所作的一项关于被称作是“粗工”(lashing)工作的研究。[^8] 所有具有生产能力而进入矿业的赞比亚人必须经历一段“粗工”的最初阶段。流程包括把上一班工人在矿面采掘到的矿石铲进推车,并运送到顶端。这是最艰苦、最令人疲惫不堪的活。尽管工作评估体系将它置于一个较高的报酬级别,实际上它所获得的却是最低级别的报酬。除去搬矿石,粗工工种还有两个功能。第一,作为内部劳动力储备,它为组织中其他地方的空缺供应工人。第二,作为加入仪式,它准备并且规训劳力,清除“不能用的”和“犹豫不决的”,为殖民地劳动过程残酷的现实准备库藏。管理层的说法,以及从外国来的(白人)轮班工头不需要干“粗工”活而黑人轮班工头却需要的事实,这些方面都清晰体现了我所要说的。然而要找到证据表明矿业运作是故意组织的,以使得矿面无法采用机械的矿石搬运机器,从而要求人力来做粗工是比较困难的。尽管如此,在独立之后,两家矿业公司的其中一家成功地抛弃了粗工这一工种,但另外一家公司未能如此。即使尚不清楚采矿技术以及采掘方式的选择是否是由殖民地政治秩序所塑造而成的,有一点是无需质疑的,即技术一旦被选择就会被用于殖民地工作组织。
回应政治变迁
当组织产生于其中并适应于它的外部关系转变——如在殖民主义让位于“民主的”政治秩序时——会发生什么?阿瑟·史汀区孔考察了组织形式不顾原先形塑它们的环境发生变化而坚持不变的倾向。这种坚持的一个条件是组织可以使自己隔离于环境变化之外的能力,尽管他实际上没有讨论这一点。[^9] 但这并不可能总会发生,尤其当变化是如同政治革命一样激烈的时候。我在前文提到的某些矿场粗工工种的取消,这可能反映了政治秩序的变迁。
一个更加重要的变迁涉及工业内的流动模式及其导致的组织变迁和冲突。同样,我只能简略地概述我在别的地方做过详尽阐述的讨论。[^10] 只要非洲人在工业内部或是在政治体系中只有一丁点儿权利(如果有的话),并且白人工人既拥有经济权利又拥有政治权利,那么双重的工资结构与肤色障碍就会难以攻破。当非洲工会出现并且在 1950 年代获得力量,以及移民劳工的重要性减小时,肤色障碍便受到了持续的攻击,白人工人也被迫放弃他们对某些工作的垄断。然而,肤色障碍的原则——没有一个白人会接受一个黑人工人的指令——本身从未被破坏,即使是在独立后也是如此;相反,它转移到了组织层级的更高领域。
从独立前缓慢的“非洲进步”,到独立后政府通盘监测的快速“赞比亚化”,这一演化提出了严重的组织问题。在此我会限制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歧视性报酬等级(与双重工资结构相联系)和殖民地工业关系的传统不能再维持。操作那些迄今为止被白人所垄断的活计的非洲人会获得类似的报酬等级。这反过来导致了矿工中间对普遍工资增长的要求——削减利润并迫使赞比亚经济其他部门工资上升。第二,继续赋予外国人员权利和威信,导致意在适应赞比亚化项目的组织变形、肤色障碍得以保留,以及为某些被撤换了的白人雇员创造新职位。第三,被提升到管理位置的赞比亚人并不像他们的前任那样掌握不容置疑的威信,也不能从他们的上级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此外,白人或黑人督工不能再强加执行具有殖民地特色的独裁的、强制的制裁。从而,矿业科层组织所倚重的强制机构以及劳动力的绝对服从不再可行。工作行为的变化反映了工业组织介入其中的政治秩序的变迁。组织形式与主流政治秩序的要求之间不相容所衍生的组织内的低效与冲突,被黑人矿工遭受的意识形态惩罚和训诫遮蔽了。现在我要探讨的正是矿工自身回应的变化。
传统工人的神话
我已经解释了南部非洲采矿业回应殖民主义方面的特质。资方和殖民地意识形态通过提出非洲工人“传统的”、“部落的”等等背景正当化了他们所屈从的暴政。非洲工人由于依恋“前现代”,是“懒惰的”、“必须接受工业纪律的教育”、“不强迫不会干活”、是“靶子”工人,没兴趣超出最低限度(向后弯曲的劳动 - 供应曲线),等等。这与早期英国企业意识形态的相似之处清晰可见。[^11]
多数关于发展的著作被韦伯式的传统所笼罩,关注的是“传统”价值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意识形态与现实极为频繁地相互混淆。诸如莱茵哈德·本迪克斯(Bendix)的《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之类的一些研究对于它们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即工业行为是被诸如村庄亲属联系和工作模式等外部社会关系所修正的——提供的证据很少。[^12] 移民和靶子工人(无论如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般的人物)通常被解释为导致工人退回到乡下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部落承诺的遗留物。非洲工人被认为比“现代”工人有更高的旷工记录,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一种“工作伦理”或不能使自己摆脱“原始忠诚”的束缚。事实则更为严酷。殖民地政府以及今天的南非政府创造了一个强制的国家机构,以此在城市与乡下之间来回驱使劳动者。此外,随着这种超经济强迫的松懈,赞比亚矿业的人员流动率迅速下降,目前,不论以什么标准看都很低。
甚至是在发展理论的神话广泛流行之前,更现实的论述也已存在。正如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所写:
一个非洲城市居民就是一个城市居民,一个非洲矿工就是一个矿工……都市化了的非洲人处于部落之外但并不超越部落的影响。相应地,当一个人从城里回到他的部落的政治领地时,他又被部落化了——去都市化——虽然也不能超越城里的影响。[^13]
格卢克曼对情景化分析的坚持奠定了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开创性作品的基础。循此,爱泼斯坦(Epstein)对非洲矿工的研究表明,当劳工以他们作为矿工的共同利益为基础组织的时候,“部落”就变得不相关。[^14] 正是作为矿工而非部落成员,非洲人罢工反抗公司。只有资方把“部落主义”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而有意地重构它时——即在复合体中——“部落主义”才重要。此外,如同克莱德·米切尔(Clyde Mitchell)所论证的,城里的“部落主义”与村庄里的“部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现象。[^15] 换句话说,非洲人同吉尔公司与联合公司的机械操作工一样,回应他们直接陷入其中并在其中完成特定行为的结构。“但从乡下到城市的行为模式转换与移居者到城里旅行一样快。”[^16] 不同和“不相关”结构的影响仅有次要的重要性。工人的行为并不来自于一种关系体系与另一种关系体系之间的文化滞后。乡村的价值与规范来自于乡村的生活组织,它们不是车间行为的基础,尽管这些行为可能会用乡村生活的方言土语 表达。
“传统的”和“懒惰的”工人的神话一直延续至赞比亚的独立时代。这不足为奇,因为尽管有政治系统的变革,资方意识形态建基其上的阶级结构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未变。^17 此外,资方正当化惩罚性制裁和严酷纪律时不再孤立。赞比亚政府在追求发展及其阶级目标的过程中接管了意识形态的鞭子,警告劳动力的“旷工”、“缺乏爱国精神”等等;政府同样宣布罢工为非法的,并且笼络曾经富有战斗精神的工会领导,在必要的情形下也强迫其顺从。从一个基于白人优越的殖民地国家转变到一个基于普选的“民族”国家,代表了一种使工人服从支配阶级的机构的巩固。在独立前的 15 年间,工会领导的罢工在铜矿具有一定程度的爆发频率;独立以来则变得日渐稀少。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罢工趋向于自发罢工,轻易地被执政党的干预所终结。
在发展理论的传统内,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观点。[^18] 他提出赞比亚政府在独立后未能从赞比亚矿工那里索取顺从。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地表明贝茨把政府意识形态当作了现实;他未能批判性地考察他用来佐证其“失败”论的公开的统计数据;而其他一些由矿业公司收集的数据并不支撑他的结论。[^19] 对于可得信息的仔细分析表明,政府与执政党甚至能够比殖民政府行使更多的控制权,并且赞比亚矿工也更加“被规训”。比起世界其他地方的矿工,他们有着更好的考勤记录、更低流动率以及更少的罢工等等。作为把意识形态与现实相混淆的结果,贝茨不加批判地相信了“懒惰的”黑人工人的神话——一个政府创造的神话(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其殖民者前任那借来的神话),并用于作为来正当化它对赞比亚矿工的独裁控制和例行性惩罚的意识形态武器。
这并不表明目前的矿业比独立之前更有效率。出于前文所略述的原因,工作场所加剧了的摩擦与冲突是工作组织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不和谐造成的:组织化结构的扩张与为调节赞比亚化造成的反弹而增长工人薪资。工人们陷入了组织的矛盾要求之中,即组织需要一种强制性的科层机构,但出于政治的原因,强制权力不再可行。造成效率低下的原因,不在于非洲矿工“原始的”忠诚,而在于后殖民时代殖民组织所面临的结构上的两难困境。
关于族群的、种族的以及其他一些外部誓约在工作结构的重要性方面我们能说些什么?我已经提出以种族划分的劳动市场形成了一个基于肤色障碍原则的工作组织。劳动者一旦被分配进劳动过程中的某一位置,其关系和行为就被那一劳动过程的结构所统治。并不是工人的种族塑造生产中的关系;相反,这些关系在生产之际再创造和再生产了种族主义。我自己对于矿山四种工作情形的研究,以及布鲁斯·卡普费雷(Bruce Kapferer)对卡布韦(Kabwe)的一个制衣厂的研究都表明:赞比亚工人之间的关系,尽管常常用诸如族群性等其他誓约措辞来表达,却是被工作组织所规定的。[^20] 卡普费雷主要关注的是群体构成的基础以及领导在车间动员支持的能力。他的结论表明,资历和生产过程中的位置,是决定工人中间派别活动以及工人与资方之间冲突结果最重要的因素。
结论
管理意识形态、政治训诫以及发展理论全都汇聚起来,创造出赞比亚矿工因其原始依恋和传统价值从而没有能力也不愿意适应工业秩序的歪曲了的肖像。实际上,早在 1935 年,矿工们成功地在铜带组织了第一次重要的和平罢工的时候,就证明了他们已经被吸纳进入资本主义。正如吉尔公司和联合公司的机械操作工一样,粗工也擅长于偷懒和配额限制。赞比亚工人并不是较少受到规训,证据表明,比起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工友,赞比亚矿工接受了更多的规训,但这仅仅是矿业组织的一个后果。简而言之,赞比亚工人在车间、矿山和办公室的行为是被生产中的关系在狭小范围内所决定的。正如我们在联合公司所发现的那样,族群和种族范畴仅在被劳动过程本身再生产的时候才重要。否则的话,它们只能作为偏见、态度,并且最重要的是表达生产关系的用语而存在。与此同时,这些生产中的关系是殖民地秩序的产物。通过在反映了现有政治与市场布局的自身结构条件内进行再创造,矿业设法保持劳动过程的相对自主性。随着政治秩序的转变,变迁随之发生,但这只是通过生产中既有关系的介入。
[^2]: 布若威,“生产的政治与政治的生产:对美国与匈牙利的机械工厂的比较分析”,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1(1979)。
[^3]: 例见:阿尔文·古尔德纳,《工业科层制的模式》;诺曼·丹尼斯(Norman Dennis)、亨里克斯(F. Henriques)、斯劳特(C. Slaughter),《煤是我们的生活》(Coal is Our Life, London: Eyre Spottiswoode, 1956),第二章。
[^4]: 采矿业的工作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适应的两种形态类型,在军队单位的组织里也有相似物。见莫里斯·贾诺维茨的“组织权威的模式变化:军事组织”,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959): 473—493。
[^5]: 埃里克·特里斯特、希金、默里和波洛克,《组织的选择》,第 66—67 页。
[^6]: 更多的细节见:弗雷德里克·约翰斯顿(Frederick Johnstone),《阶级、种族与黄金》(Class, Race and Gol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H. J. 西蒙斯(H. J. Simons)和 R. E. 西蒙斯(R. E. Simons),《南非的阶级与肤色,1850—1950》(Class and Colour in South Africa, 1850—1950,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Books, 1969),特别是第二章与第三章;查尔斯·范·翁塞伦(Charles van Onselen), Chibaro(London: Pluto Press, 1976);以及哈罗德·沃尔普(Harold Wolpe),“南非的资本主义与廉价劳动力:从分隔到种族隔离”(“Capitalism and Cheap Labor Power in South Arica: From Segregation to Apartheid”), Economy and Society 1(1972): 425—456。
[^7]: 当然,这并非南非所特有。见: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编《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1976);凯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钢铁工业中工作结构的起源”(“The Origins of Job Structures in the Steel Industr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6(1974): 113—173;以及哈里·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
[^8]: 迈克尔·布若威,《工业冲突中的限制与操纵》(Constraint and Manipulation in Industrial Conflict, Lusaka: Institute for African Studies, Communication no. 10, 1974),第二章与第三章。粗工似乎起源于南非金矿,后来被赞比亚铜矿采用。
[^9]: 阿瑟·史汀区孔,“社会结构与组织”,载于詹姆斯·马奇编的《组织手册》第 142—169 页。有趣的是,史汀区孔的确这样写道:“‘机械制造’产业是归纳的主要例外。无论是造船、火车头、有轨电车、机床、汽车、飞机、电机,这些产业都有现代形式的组织,不论其历史有多久。”(第 159 页)——这与产业的年龄与组织形式之间的更正规的联系有别。然而,悖论的是,机械厂的技术和工作组织自工业革命以来基本上保持未变。但是,根据史汀区孔所说,这些产业的“结构特质”总是现代的。显而易见,史汀区孔所评估的不同于工作的组织(实际上,他据以评估“结构”的是无薪家庭的比例、自我雇用和家庭工人的比例,职员占行政人员的比例以及专业人员占有权者的比例。)看起来他是在衡量使生产过程与环境相隔离的组织的特定“减震”成分的大小。因而,当减震成分弱时,如同农业中那样,生产过程最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从而也受制于转型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减震成分相对强之处,如同机械产业那样,工作组织免于遭受环境偶然性的影响从而倾向于维持现状。外在变化被科层制机器吸收了。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一方面解释科层制因素的成长,另一方面又能解释工作结构的持续性。换句话说,史汀区孔所论述的组织特性与产业发展时间之间的正相关性趋向于掩饰工作结构与产业发展时间之间关系的缺乏。我所提出的替代性假设是,某些组织会发展出阻碍工作过程发生转型的辅助性制度(或许可以根据史汀区孔的组织特性来衡量)。此外,产业历史越悠久,这些制度的发展越不完整(根据史汀区孔的资料),工作过程经历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再者,组织越现代——也就是说减震制度越发达——技术与工作过程要转型也就越困难。
[^10]: 布若威,《铜矿中阶级的肤色:从非洲进步到赞比亚化》(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 From African Advancement to Zambianiz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ambian Papers no. 7, 1972)。
[^11]: 例见莱茵哈德·本迪克斯的《工业中的工作与权威》,第 34—73 页。
[^12]: 莫里斯·贾诺维茨恰当地描述了这些发展学者的努力:
尤其是在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编的《旧社会与新国家》(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一书中,他们寻求确定那些严重阻碍了“现代化”的社会与文化分层的模式。他们探究了各种类型的原始情感——族群、血缘群体、语言、种族以及宗教——在“文明的”或世俗的政治发展上的后果。(《政治冲突》[Political Conflict ],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第 24 页)
这种探究发展的途径应当受到像弗兰克(Gundar Frank)这样的作者的攻击(《拉丁美洲:低度发展或革命》[Latin America: Underdevelopment or Revolution ],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第二章)。
[^13]: “非洲工业革命引起的人类学问题”,收录于艾丹·索撒尔(Aidan Southall)编《现代非洲的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 in Modern Afric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Internal African Institute, 1961),第 69—70 页。
[^14]: 爱泼斯坦(A. L. Epstein),《一个非洲都市社区里的政治》(Politics in an Urban African Commun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15]: 克莱德·米切尔(Clyde Mitchell),《凯莱拉舞蹈》(The Kalela D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 Rhodes-Livingstone Paper no. 27, 1956)。
[^16]: 索撒尔,《现代非洲的社会变迁》,第 19 页。
[^18]: 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工会、政党与政治发展》(Unions,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 布若威,“另眼看矿工”(“Another Look at Mineworker”), African Social Research no. 14(1972):第 239—287 页。
[^20]: 布若威,《工业冲突中的限制与操纵》以及《铜矿中阶级的肤色:从非洲进步到赞比亚化》;布鲁斯·卡普费雷(Bruce Kapferer),《一个非洲工厂里的策略与交易》(Strategy and Transaction in an African Fac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