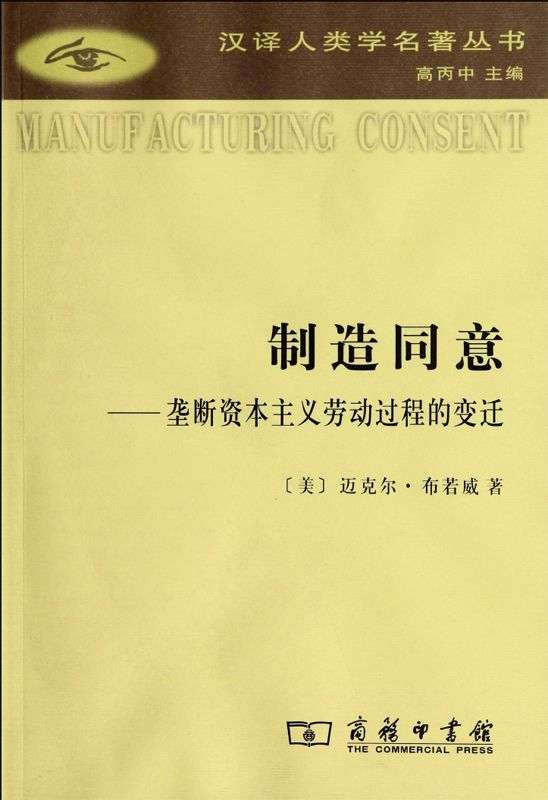转载 | 争夺的地带: 劳工团结、制度空间与代工厂企业工会转型
本号不拥有转载文章的任何权利,文章不代表本号观点
若侵犯了您的资产阶级法权,请通知号主删文跑路~
争夺的地带: 劳工团结、制度空间与代工厂企业工会转型
汪建华,石文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南京商业学校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家日资汽车厂企业工会长期实践过程的分析认为, 工人的团结行动、意识发展以及经验增长将与自上而下的控制构成持续的互动与张力。转型时期, 工人生活经历的变化为其团结的形成和意识的提升提供资源, 而制度空间也在反复的工会实践中逐渐拓展, 对企业工会的考察不可忽略劳工的团结与实践。文章最后评估了代工厂企业工会转型的总体前景。
关键词:企业工会转型; 社会转型; 劳工团结; 制度空间
一、转变中的工会与工会研究
在社会主义时期, 中国工会曾作为国家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长期存在。①这种角色定位既便于党和国家对整个社会实施垂直控制, 防止横向阶级利益形成, 还能协助国家进行生产动员; 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传递工人诉求, 保护工人权益 (Chan, 1993; Chen, 2003; 冯钢, 2006)。因为父爱主义的劳动体制能够大体上满足工人的经济需求, 这种二重性的角色在改革前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挑战 (Chen, 2003)。但是市场化改革既伴随着国家父爱主义的撤退, 又带来国家、资本、工人之间利益的分化和冲突 (Lee, 1999; Chen, 2003; 李静君, 2006)。工会作为国家工具和工人组织的矛盾存在, 在多元的利益格局面前也不得不有所调整。陈峰分析了工会在不同类型的劳资冲突下分别采取的三种相应策略: 在法律争端中有限度地代表工人争取权利, 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代表国家在劳资之间进行斡旋调解, 垄断工会组织空间并限制工人组建独立工会的诉求 (Chen, 2003)。尽管工会工作方式有所调整, 但是“国家统合主义”的劳资关系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工会大部分时候仍然扮演着国家控制的工具, 其存在和运作依赖的是国家赋予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 而非工人自下而上的结社权力。工会这种一边倒的选择, 既来源于国家控制社会的需要, 也与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导向密不可分。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利益中, 工会内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 比如推动基层工会直选, 都会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下寸步难行 (Chan, 1993; Chen, 2003, 2009, 2010; Howell, 2008)。相比其上级政府工会, 企业工会还进一步依附于外来资本或企业高层, 对国家和资本的双重依附导致企业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碌碌无为。而政府工会至少还可以利用其行政上的优势, 推动劳动立法、工会组建, 并参与调解劳资争端 (Chen, 2009; Liu, 2010; 冯钢, 2006)。
另有一些研究注意到全球化背景下推动劳资关系转变的其他力量。其中, 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被认为能在推动工人自组织和利益表达、工会民主实践方面开启新的空间和渠道。这些外来力量的介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工权益的改善和民主意识的提升。但是企业工会角色的转型却是非常有限的, 其根本症结在于工会转型缺乏深层次、可持续的动力。跨国公司并不愿意看到真正的独立工会出现和常规议价机制建立, 而公民社会组织对工厂政治的影响也流于表面 (Chan, 2009; 黄岩, 2008; 岳经纶、庄文嘉, 2010)。和“国家统合主义”一样, 这种自上而下的企业工会实践模式并没有以工人的团结和抗争行动为基础。工人对工会可能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在上述视角中是缺失的。
当然, 研究中国劳工抗争政治的文献也很少分析其在推动工会转型方面所具有的潜力。这种倾向与劳工抗议长期以来的组织化程度有限 (多以非正式抵抗、个体法律维权和野猫式罢工为主)、诉求低 (长期以来争取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 的现状不无关联 (Pun, 2005; Lee, 1995, 1999b, 2007; Chan, 2011; 黄岩, 2010)。近年来, 劳工抗议政治的升级带动了研究视角的转变。官方工会的角色在工人的抗议中遭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 在相当一部分集体抗争案例中, 强烈要求组建独立工会是工人的核心诉求和集体共识。一些劳工研究者由此也开始分析工人自下而上的集体行动压力对工会角色转变的影响。在大连, 2005年和2010年的罢工潮不断迫使工会进行制度改良。在劳资博弈中初步形成了“说和人”的工会运作模式: 企业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聚集工人意见并凝结力量, 然后以中间人的姿态在劳资双方进行沟通。这样, 企业工会一定程度上从既要代表工人又要被企业管理层整合的双重压力中解脱了出来 (Chen, 2010; 孟泉, 2013)。而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工人的罢工也迫使部分企业重组了工会, 这种趋势在汽车零部件业尤其明显 (Chan&Hui, 2012, 2013; 吴同、文军, 2010; 汪建华, 2011, 2013; 汪建华、孟泉, 2013)。
但是, 当涉及到企业工会重组和工资集体谈判等主要的实践时, 已有的研究文献又持有一种悲观论调: 工人很难通过自身的团结行动进一步影响企业工会的日常实践和组织架构。因为国家并没有真正赋予工人罢工权和自由结社权, 所以很难有西方意义上的集体谈判。工会仍然没有摆脱对地方政府和资本的依附, 推动工会民主选举和工资协商的公民社会力量也非常缺乏。政府及其代理人、地方工会仍然主导了企业工会的选举和集体谈判。政府之所以有兴趣来重组工会、推行集体谈判, 与其说是为了迫使资本对工人让利, 不如说是为了消除潜在的集体抗议行动, 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政治上的有效控制。陈敬慈和许少英认为, 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党政主导的集体谈判”将与以前盛行的“形式化的集体协商”、“抗议引领的集体谈判”并行, 西方国家意义上“工人主导的集体谈判”在近期很难实现 (Chan&Hui, 2012, 2013)。考虑到陈敬慈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前景的乐观预期 (Chan&Pun, 2009; Chan, 2010), 其对企业工会转型的悲观论调或许更具代表性。
笔者并不反对这一判断, 现阶段企业工会及其集体谈判实践总体上是被国家掌控的。但是, 诚如陈敬慈以往研究所分析的那样, 工人可以绕过官方工会进行集体罢工, 并迫使国家默许工人罢工权和重组工会诉求的合理性 (Chan, 2010; Chan&Hui, 2012, 2013)。工人也可以在后续的企业工会选举和集体谈判中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冲击现有的制度壁垒, 他们的集体行动同样可以绕过依附性的企业工会, 甚至借此进一步推动建立独立工会。因此, 笔者认为, 现有研究文献可能太过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规制力量的牢固性、正式性和静态性。这种强调一方面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转型时期制度本身变迁的可能性及其变通和运作的空间, 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底层实践的经验、策略和团结形成的可能 (Lee, 2007; 孙立平, 2000, 2002; 吴同、文军, 2010)。如李静君指出的那样, 底层的实践和官方启动的改革一样, 都是“摸石头过河”的过程 (Lee, 2007)。国家与民众、统治精英与底层的互动, 共同塑造了社会转型的方向。因此, 笔者更倡导将企业工会及其集体谈判视作国家、资本、工人反复“争夺的地带”, 而非“党政主导”抑或“工人主导”的性质分明的场域。这种争夺虽然在短期内显示出党政控制的总体性优势, 但是这也不妨碍我们从现有案例中挖掘工会转型的其他可能性。对中国农村上访、征粮等事件过程的分析, 体现了基层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运作 (孙立平、郭于华, 2000; 应星、晋军, 2000)。类似的分析也体现在对工人抗争行动 (Lee, 2007) 和企业工会实践 (吴同、文军, 2010) 的研究中。
不过, 瓦解行政和资本设置的各种制度、程序障碍光有工人的实践策略还不够, 笔者同样强调工人的集体团结在推动企业工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劳资博弈 (很多时候也少不了政府的介入) 不同于分散的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单个的工人只能争取有限的法定权益, 要通过集体谈判实现合理的市场利益还需以工人的集体行动做支撑。社会转型时期工人生活经历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与他们长期的工业化经历, 同样为工人集体团结的形成与集体倾向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Pun&Lu, 2010; 汪建华, 2011, 2013; 汪建华、孟泉, 2013)。因此, 社会转型为工人推动企业工会转型提供了双重机遇: 既带来工人生活形态的变化和集体团结的资源, 又为突破政府和资本对工会的控制提供了可运作的制度空间。
二、资料与案例
笔者将通过对一家企业工会从成立至今历时5年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 展示工人与资本、政府对企业工会控制权和集体谈判②的反复争夺, 并从中挖掘企业工会转型的可能性。发生在该企业的罢工、工会改组、集体谈判曾一度引起媒体和学界的广泛关注。‘陈敬慈和许少英“党政主导”的论断也主要以该企业的工会实践的田野材料为基础 (Chan&Hui, 2012, 2013), 这样就比较方便笔者与其直接对话。他们的材料中并没有包括2012年以后的几次集体谈判, 而正是这几次谈判中工人显示了自身影响企业工会运作的潜力, 这也构成笔者反思其研究论断的主要基础。本文还将借助经验材料剖析工人团结形成和策略发展背后生活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基础, 并借此进一步评估企业工会转型的可能前景。遵照学术惯例, 本文中出现的企业、人物和区县级以下地区一律以化名来替代。延续笔者以往研究中的提法, 本文将该企业命名为“汽新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本文对企业工会主要限定在改革后兴起的代工厂, 这些工厂主要由外来资本或国内私有资本投资建成, 有别于国有企业。
笔者于2011年1月份开始进入到汽新厂员工的居住社区进行访谈, 此后又多次进行回访。最重要的是, 通过与该企业高层沟通, 笔者得以在2012年4-5月以实习员工的身份进入到汽新厂进行参与式观察。这使得笔者有机会接触并访谈公司各级别的员工, 包括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工会领导, 并可以对工会的日常运作、公司的日常生产和员工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笔者还收集了工人在罢工时留下的长达几十万字的聊天记录、相关的文献材料、报告、媒体报道等, 这些材料可以与笔者的访谈、田野观察资料, 相互补充、参照。
汽新厂于2007年正式量产, 主要生产变速箱、传动轴、曲轴、连杆等汽车零部件, 是日本某著名汽车企业在佛山汽配园区投资的独资公司。目前共有员工2000多名, 以男工为主。公司的普通生产工人基本都从中专职校成批招聘。
汽新厂企业工会角色转换的脉络大致是: 在2008年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徒具形式, 导致在两年后的罢工中被迫改组, 并开始转而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一年两次的集体谈判 (分别商谈工资增长和年终奖额度); 但政府和资本随后也逐渐加强了对工会的控制; 其后, 工人在发现企业工会的依附性质后也以自身的团结行动做出了回应, 迫使公司两次对工人的福利待遇做出让步; 随后, 公司的报复行动也接踵而至。
(一) 以行动重组空壳工会
公司按照政府的要求在2008年4月成立了工会, 但工会的主要作用只限于给员工发福利或者组织年会、旅游等集体活动。对于大部分工人来说, 加入工会也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福利, 工会的小恩小惠并不能缓解实质性矛盾的积累。自公司成立以来, 工人的薪资待遇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罢工前普工到手的收入只有1200元左右, 扣除房租、通讯、上网、外出聚餐、娱乐、购物等方面的花费, 很多年轻工人都入不敷出。多个车间的小型罢工、高离职率、故意违纪、墙壁门窗涂鸦、工人在各个场合的交谈 (如QQ群、公司通勤车) 等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工人的不满情绪。但是工会对这些几乎都没有察觉, 两位工会专职人员承认他们和现场工人交流很少。
变速箱组装科的工人在2010年5月中旬发起了罢工。工人从罢工伊始就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媒体, 并在内部启用QQ群进行沟通。不过在公司管理层的劝说下, 工人暂时复工, 但他们提出了上百条诉求, 主要集中在工资/补贴、工时/休假、实习生待遇等问题上。关于工会的诉求只有一条:
诉求67: 工会没有发挥作用, 员工无法享有福利。③
工人对于工会的角色颇有不满, 但是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有重组工会的权利, 也不知道工会真正可以履行什么样的职责。
很快工人就感觉到公司并没有诚意, 于是4天后变速箱组装科的工人再次发起罢工, 这一次的行动很快得到全厂同仁的响应。通过QQ群和论坛等平台, 工人频繁地沟通信息、协调行动, 并相互鼓励。在高昂的士气中, 工人抵挡住了公司各种分化、瓦解、恐吓、利诱的举措, 在酷热的环境中坚持了12天。他们的诉求也在互动中不断提升, 工人提出加薪800元的经济诉求, 并且强烈要求重组工会。
非常具有戏剧意味的是, 在资方律师指责工人行动违法的压力下, 工人频繁在网上查找各种法律给予面对, 最后他们发现了《工会法》, 工人也由此开始重新思考工会的角色和作用。公司工会在整个罢工过程中协助资方控制分化工人的做法让工人非常反感。5月31日工人与镇工会的冲突更将“黄色工会”的面目表露无疑。④
罢工事件最后在某全国人大代表的斡旋下以和平的集体谈判收场。由于年轻的工人代表缺乏经验, 谈判一度进行得比较艰难, 后来在某知名学者的协助下, 劳资双方达成了加薪500元的方案。
广东省总工会随后也回应了工人重组工会的诉求。在省总工会的指导下, 汽新厂重新进行了工会选举。新选出的工会保留了原来的工会主席和7名工会委员, 不过工会其他职位的选举程序还是比较民主的。工会小组长、分会委员、分会主席由工人直接选举, 新增选的工会委员在小组长提名的基础上由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两位工会副主席也是在工会委员内部互相投票产生的。
(二) 收回工会的控制权
尽管上级工会对最主要的职位严格把关, 但新一届工会的表现大大出乎劳资政三方的意料。工会和工会主席主要通过他们在两次集体谈判中的表现逐渐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在年终奖和工资集体谈判前, 工会先充分征求普通员工的意见, 然后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工会的谈判方案。这无疑与公司年终奖和工资增长方案形成了巨大落差。 加上工会掌握的信息有限, 缺乏谈判经验, 两次集体谈判都曾陷入互不妥协的僵局, 在省总工会领导人的调停下才达成协议。
上级工会很快在新一届的工会选举中扩大了对关键人选的控制。工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分会主席皆由上级提名。工会主席重新由公司高层管理者兼任。在集体谈判方面, 新一届工会在意见征集、信息收集、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对员工意见表达进行了一定的控制和引导。劳资双方在2011年的年终奖谈判和2012年的工资谈判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其后有少数员工质疑工会的独立性, 但工会领导人认为, 大部分员工对他们的工作是认可的。
(三) 工人的回应
在 2012年的年终奖谈判, 劳资双方出现了一点不愉快的小插曲, 但这只是新一轮冲突的开始。公司坚持拿3个半月年终奖的方案, 但这明显低于工人的期望, 因为上一年他们就拿到了4个月的年终奖。变速箱组装科的工会小组长集体商议好, 如果公司不让步, 就发动罢工。他们同时和其他科的工会干部进行了联络。当工人的想法通过工会传达到谈判桌上后, 公司只好答应将年终奖提升到3.9个月。
随后的工资集体谈判中, 公司提出的方案又远低于工人的期望。⑤在公司的方案中, 一至五级员工的工资增幅分别为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⑥公司分化员工内部的意图非常明显, 因为公司和工会的中高层管理者级别基本都在三级以上。公司针对工人可能的罢工行为也做好了预案。因此, 在连续4天的谈判过程中, 公司始终坚持其最先的方案。最后, 工会只好选择接受这一方案。
但就在当天晚上, 工人却再次绕开工会发动了罢工。抗议行动仍然由变速箱组装科发起, 因为他们工作辛苦、加班少, 而且内部团结、占据关键位置。我们不清楚工会小组长在这次行动中的角色, 但是他们后来大多都遭到了管理层的报复。可以肯定的是, 和3年前的罢工一样, 一些将要离职的工人在行动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汽新厂这几年的待遇虽然有所改善, 但是很多工人还是看不到发展的前景, 升职基本无望, 而长期枯燥、重复性的流水线工作也让他们感到非常压抑。罢工既是他们为工友争取权益的机会, 也是宣泄不满的方式。齿轮加工科和铝加工科的工人在犹豫一段时间之后也跟着停工。不过这次工人彼此之间的沟通并不是很多, 全厂范围的QQ群自从上次被相关部门严厉封锁之后再没有建起来。公司和工会也很快做出了反应, 他们将变速箱组装科的工人单独拉到会议室, 避免与其他科相互呼应。工人提出18%的增长幅度, 并表达了对工会的不满。虽然考虑过罢免工会主席, 但由于无法从员工内部找到合适人选, 工人并没有明确表达这一诉求。
公司本以为罢工就此平息, 并打算重启谈判。但是次日清晨, 部分情绪激动的工人再次罢工。公司和工会只好再次召集工人开会、写诉求, 并提前结清了将要离职的员工工资, 以免他们再生事端。下午公司和工会再次谈判, 最终达成方案: 一级普工月工资上涨310元 (14.4%), 并加50元房补。
公司随后展开了报复行动。公司决心彻查罢工带头者和谣言传播者, ⑦并将变速箱组装科的10余名工会小组长调到其他科, 让他们做最繁重的工作。工人猜测这可能是一种变相逼走他们的方式。对工会新一轮的控制由此又将开始, 企业工会的转型看来注定是一个艰难、漫长、反复的过程。
三、企业工会转型的动力与制度空间
汽新厂工会的转型过程充满反复, 至今尚未摆脱对政府和资本的依附。但是, 我们不难从该案例观察到企业工会转型的动力和制度空间。
汽新厂的工人虽然普遍来自农村, 但其社会特征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去甚远。他们普遍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 这种教育经历改变了他们的生产体验、信息视野、发展期望、身份认同, 并赋予其全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开放的交往方式。过往的学校教育促进了年轻工人对信息技术的熟练掌握, 这对于他们开阔视野和集体行动动员能力的提升都大有裨益。随着其工业化经历的不断增长和生命周期的变化, 工人也在不断刷新其诉求、视野与经验。
考虑到现阶段正式组织动员力量的缺乏, 工人非正式的网络资源、动员工具的存在和意识诉求的提升能为集体谈判的落实和工会的转型提供了自下而上的动力。而面对政府和资本自上而下的规制力量, 工人同样可以在制度中寻找空间。他们既可以要求政府和企业落实正式制度赋予他们的权利, 比如重组工会、落实集体谈判制度等, 又可以在国家既没明确规定也不禁止的制度模糊地带拓展行动的空间, 如反复发起的罢工行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一) 生活经历变迁与劳工团结的形成
有工人集体行动作为潜在支持力量的谈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劳资谈判, 否则只能是看资方脸色的“协商”。但问题是企业工会现阶段在行政上依附于上级工会, 在经济上依附于资本, 这使得企业工会不可能承担领导工人罢工的重任。工人的行动依然只能依靠其非正式的组织力量和意识诉求的提升。汽新厂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劳工团结产生的土壤。
笔者将劳工团结产生的基础首先追溯至社会转型时期工人生活经历的变迁中。中等教育经历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他们在消费休闲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交往方式、 信息视野、身份认同、发展期望等方面与老一代工人相区别。生活机遇、生活方式、集体倾向的代际差异在大样本的调查数据中得到了确认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2013), 且在汽新厂工人的行为方式中也得到印证。他们基本都毕业于中专、职校, 除了将学校的同学关系网络带到工厂之外, 他们也带来了开放的交往方式。在2010年罢工前, 工厂离职率一直都比较高, 工人流动性比较大, 但是年轻工人还是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地发展了自己的同事关系网络。而在笔者过去观察到的老一代工人的工厂中, 工人只有在长达10多年的稳定的工作关系中才能建立起这样广泛的网络。关系网络的维系和构建与他们频繁参与各种集体消费活动密不可分:
其他科肯定也有啊。都是年轻人肯定都有, 就是经常聚会。各种聚会, 各种类型的聚会, 或者是生日啊。生日只要认识的人, 啊, 大家过来一起吃一顿吧, 经常。每年的年末, 喔,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饭局。(为什么?) 因为生日啊, 生日每天都有人请客啊。每天晚上蹭饭吃 (笑), 就是他会叫你。虽然大家住的比较分散, 但是如果这个人过生日, 大家肯定会一起到他那里去。(clcp0112)
除了生日聚会, 还有周末聚餐、唱K、打牌、逛街等各种形式的集体娱乐活动。当然, 工人这种关系网络的建立也得益于公司的管理文化。公司允许工人有自己的社会生活空间, 并且在平时的管理中也会有各种集体活动, 如年会、旅游、体育比赛等, 以帮助年轻工人进一步拓宽交往渠道。工人的团结确实有其工厂政体的基础, 否则年轻工人的生活方式也很容易滑向个体化。但不管怎样, 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确实有助于团结纽带的建立, 这种团结纽带在汽新厂的两次罢工行动中都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同时, 这也是建立工人群体认同的过程。在每一次抗议行动中, 即将离职的工人都义无反顾地去带领罢工。
为工人的行动提供资源的还有互联网, 尤其是手机互联网这一廉价信息终端的普及。互联网从内部便利了工人群体间的沟通、协调和相互鼓舞, 从外部能够争取外界关注和专业团体的介入; 其他地方一些有影响力的个案为工人的行动提供了经验示范; 工人还可以借助互联网拓宽自己的视野, 并在行动时随时调用相关的法律信息。
汽新厂第一次罢工行动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进行内外部的沟通, 但是由于相关部门的封锁, 工人没有启用全厂范围的QQ群。又由于工人在第二次罢工时对行动的策略和政治风险都有比较明确的把握, 因此也没有很积极地争取外界的介入。但是互联网的存在将随时为工人的内外沟通和信息获取提供资源。
工人在学校教育、信息技术使用和城市打工生活中对一整套消费主义文化的接受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并加剧了他们与公司的紧张。都市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养成也是他们逐渐城市化的过程, 而城市化和工业化经历不断丰富的另一面使他们逐渐失去农业生产技能并与农村生活方式相脱离, 这些都潜在地提升了这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起来的期望。这种期望在汽新厂工人身上日益明显起来。
外在社会际遇中的一些因素也影响其与资本的关系, 例如城市的物价甚至房价也成了他们评估公司薪酬待遇合理性的主要指标之一。不可逆的城市化需求是促使工人抱团并诉诸独立工会实践的内在动力。
(二) 工会实践与不断打开的制度空间
政府和资本虽然力图将改组后的工会重新整合进政府工会和企业管理的架构中, 但这绝对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博弈过程。除了上文讨论的工人内在行动的动力外, 就企业工会本身而言, 也需要不断直面工人的集体压力和合法性质疑。工人意识越强, 抗议越频繁, 工会的合法性危机便越强烈, 这可能导致企业工会角色的摇摆。汽新厂原工会主席方宇祥便是很具代表性的案例, 罢工期间工人的质疑、嘲讽甚至辱骂使得方宇祥在极其孤立的心态下突然转向, 继而在随后的工作中尽可能地去推动工会民主和集体谈判。尽管资方和上级工会在发现这种转变后很快收回了对企业工会的控制权, 但是毫无疑问, 任何倒向资本的企业工会和工会领导人都将在其日常工作中不断面临合法性危机, 这种危机随着工人意识的觉醒和抗议的增多, 可能会被逐渐凸显。
而各种工会实践的开启, 如工会选举、集体谈判、工人意见调查、工会小组活动和职工代表大会等, 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工人在经验策略层面的学习和意识诉求层面的提升。汽新厂工人在工会实践过程中自主性的不断增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效果。在工会改组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工人只是寄希望于工会为他们争取福利。当这种期望受挫时, 他们的不满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抱怨, 日久天长, 工人最终还是不得不重新诉诸于自身的团结行动。工会的实践也在促使工人群体中的精英不断熟悉谈判策略、工会法律、日常工作开展方式、民主选举流程。实际上, 政府和上级工会开启的工会重组和集体谈判只是为了消除工人潜在的抗议和不满, 但是工人一旦参与其中, 就可能形成新的意识、诉求、策略, 并为进一步的行动提供潜在基础。
现有的国家法律和制度在文本层面充满了各种维护工人权益的条例和措辞, 工人的工会实践有助于工人不断熟悉和利用这些文本规定。如法律规定, 工会应当民主选举产生, 应当代表工人与企业民主协商, ⑧当工人从《工会法》中得知他们原来拥有如此多的权利时, 便借助罢工要求落实这些权利。当2013年工资集体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时, 工人也想过借助职工代表大会而不通过谈判协议来回应资本和工会的合谋。汽新厂工人也曾通过《工会法》了解到罢免工会主席的相关程序, 只是感觉时机不成熟, 没有付诸实施。不过, 在笔者跟进观察的另一家电子企业松电厂, 上百名工人发出了罢免工会主席的倡议, 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虽然最终企业工会委员会没有同意启动罢免提案, 但是这也向我们展示了工人影响工会核心人选的可能性。⑨可见, 以正式的法律文本为依据来推动工会的转型仍具有巨大的空间。
工人也可以在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但也没有禁止的制度模糊地带活动。当资本和工会通过了工资增长方案时, 工人通过罢工迫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实际上, 工人罢工是否合法、是否可以用行动推翻工会在谈判桌上通过的方案, 都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从“守法”到“不违法”的灵活转变, 有利于工人不断通过行动打开可能的制度空间。当然, 企业工会对上级工会和资本的依附依然是限制民主的常规的议价机制建立的最大障碍, 这需要工人对工会的选举程序、工会专职人员收入来源等问题提出挑战, 这样的挑战离不开工人的意识发育和持续性的行动。
四、争夺的地带: 重新评估企业工会转型的前景
近年来对中国工会的研究开始逐渐修正“国家统合主义”的视角, 但是国家依然被认为保留着对社会神经末梢的影响力、渗透力。对企业工会运作的分析仍然没有摆脱“国家统合主义”视角带来的悲观论调。国家对工人罢工权和自由结社权的限制妨碍了集体谈判的真正推行, 而企业工会本身也处于对地方政府和全球资本的双重依附中, 来自社会的支持也极其有限。当下的企业工会实践在总体上确实符合陈敬慈等人的判断, 但是本研究也同时提醒劳工研究者注意企业工会转型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并不缺乏工人群体内部自下而上的动力, 工人代际生活形态的变化及其自身不断深入的工业化经历一方面为工人的团结行动提供了组织动员资源,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激发部分工人城市化的需求, 并推动工人意识、诉求和集体抱团倾向的增长。而政府看似强势控制的背后也隐藏着一定的制度空间, 对工会实践的有限度开放也促进了工人经验策略的增长和追求工会民主的努力。
汽新厂工会发展转变的历程有助于促使我们重新评估工人突破政府和资本控制的可能性。首先, 国家并没有完全禁止工人的罢工权, 而工人的自由结社权也可以部分以其自身非正式的团结纽带和动员工具作为替代, 并且工人结社权的实现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被争夺和定义的过程。工人既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争取改组企业工会和建立集体谈判制度, 也可以以自己的行动重新推动企业的集体谈判。而且, 工人日益频繁的抗议行动本身也有助于为“罢工”脱敏。在笔者近几年的田野调查中, “罢工”在很多工人的观念中, 正逐渐由遥不可及的危险行动转变为常规的讨价还价行为。其次, 企业工会虽然在总体上依附于政府和资本, 但是, 工人通过与企业工会分离的自主行动仍然可以推动企业工会集体谈判的落实。工人同样有影响企业工会主席人选的能力。而企业工会在面临来自底层工人持续的压力时也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另外, 社会建设的发展及其与工人的关系也充满变数。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已观察到一些社会机构在推动工人集体谈判和行动方面所做的努力, 这种努力表现为: 为工人的集体行动提供策略建议, 介入到工人与企业的劳资谈判中, 推动工人建立工会, 对工人进行团结意识、法律知识、谈判技巧等方面的培训等等。现存的互联网平台也推动了工人与这些社会团体的互动。因此与其单纯地讨论企业工会的制度性依附逻辑, 不如通过经验个案详细挖掘企业工会在实践中的自主性和存在的制度空间。
除陈敬慈等人强调的制度困境之外, 全球资本体系也是工人团结和企业工会转型面临的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壁垒。汽新厂拥有一定的市场利润空间, 所以工人和工会有一定的议价空间。但是在中国, 大部分代工厂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 例如在电子制造业中, 企业代工竞争激烈, 利润极其有限。笔者在文中列举的松电厂虽然民主选举了工会, 但是工人反映, 工会甚至不能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形式上的工资集体协商。不是不能这样做, 而是工人、工会都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做; 另外, 上文谈到, 汽新厂管理文化中相对比较人性化的一面促进了工人的参与、交流, 并降低了工人的离职率。但是这样的管理文化只是在日本和欧美的外资企业中有存在的可能, 在港台、韩国和大陆的私企当中, 这种管理文化很少见。专制的管理文化、高强度且重复的异化劳动、低廉的薪资待遇、狭小的发展空间以及工人个体化的社会生活共同导致了工人频繁的离职行为。高度的流动使得工人群体间难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集体认同, 反而可能在紧张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制造工人同事间的横向冲突。在这样的企业中, 即便建立起企业工会, 工人在缺乏归属感和长远发展期待的情况下, 也不可能对工会有实质性的参与和兴趣。他们也难以通过集体抱团行动来推动企业工会的转型和民主运作。工人在这类企业的抗议行动未必会导致常规议价组织与机制的建立, 而是可能沿着另外一个更具紧张和冲突性的方向发展。
当然, 在世界工厂代际更新的过程中,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补充进来, 就如我们见到的汽新厂工人那样, 他们将在具备利润空间和管理弹性的企业中, 不断以自己的行动寻找制度的空间, 推动企业工会的转型。而眼下沿海代工厂不断内迁也使得工人在工厂中形成社区生活具备可能。工人稳定的社区生活和当地社群网络是否能进一步为劳工抗争和企业工会转型注入动力也值得分析。再者, 从工人纵向的无产化经历来看, 工人在运作企业工会方面的自主意识和经验也可能在其漫长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过程中进一步深化。这个过程在政府和全球资本的限制面前注定充满冲突、张力、曲折与反复, 企业工会注定是一个劳工、资本、 政府不断争夺的地带。
参考文献
冯钢, 2006, 《企业工会的“制度性弱势”及其形成背景》, 《社会》第3期。
黄岩, 2008, 《代工产业中的劳工团结: 以兴达公司员工委员会试验为例》, 《社会》第4期。
——, 2010, 《脆弱的团结: 对台兴厂连锁骚乱事件的分析》, 《社会》第2期。
李静君, 2006, 《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 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 理论与实证》,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孟泉, 2013, 《谈判游戏中的说和人——以DLDA区工会为例》, 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2013, 《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 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 2000, 《“过程一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鹭江出版社。
——, 2002, 《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孙立平、郭于华, 2000, 《软硬兼施”: 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鹭江出版社。
汪建华, 2011, 《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 《开放时代》第11期。
——, 2013, 《新工人的生活与抗争政治——基于珠三角集体抗争案例的分析》, 沈原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建华、孟泉, 2013,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开放时代》第1期。
吴同、文军, 2010,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 工人依法维权的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社会》第5期。
应星、晋军, 2000, 《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 《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 鹭江出版社。
岳经纶、庄文嘉, 2010, 《全球化时代下劳资关系网络化与中国劳工团结——来自中国沿海地区的个案研究》,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期。
Chan, Anita 1993,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Vol.29.
—— 2009, “Challeng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Democratic Grassroots Union Election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wo Factory-level Ele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 Labor Studies Journal.Vol.34.
——2011, “Strikes in China’s Export Indust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hina Journal.Vol.65.
Chan, C.K.C.2010,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Migrant Worker Strik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Vol.41.
Chan, C.K.C.&E.S.I.Hui 2012, “The Dynamics and Dilemma of Workplace Trade Union Reform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Honda Workers’Strike”,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Vol.54.
—— 2013,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China; From’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to’Party State-led Wage Bargaining’”, The China Quarterly(December); 1-22.doi.(http: //dx.doi.org/10.1017/ S0305741013001409).
Chan, C.K.C.&Pun Ngai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Vol.198.
Chen, Feng 2003,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Vol.178.
——2009, “Union Power in China Source, Operation, and Constraints”, Modern China.Vol.35.
——2010, “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 Interactions in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1.
Howell, Jude 2008,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s Unions beyond Reform?The Slow March of Direct Elec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Vol.196.
Lee, Ching Kwan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0.
—— 1999,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Vol.157.
——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iu, Ming Wei 2010, “Union Organizing in China; Still a Monolithic Labor Movement?”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Vol.64.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Durham&Hong Kong; Duke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un, Ngai&Huilin Lu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 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 Modern China.Vol.36.
注释
①中华全总及其下属各级工会曾在上世纪60、70年代一度停止活动, 可参考: Chan, 1993。
②该企业仍然沿袭“集体协商”的用法。
③资料来源: 汽新厂与莱律师事务所共同撰写的《117条员工诉求处理方案 (初案)》, 未公开发布。
④狮镇工会人员当天正好戴着黄色的帽子。
⑤工人的高期望与汽配园的周边环境有关, 德国某著名汽车集团在汽新厂旁边投产, 员工工资福利都比较好, 汽新厂高层曾经承诺到2013年员工的待遇要与其持平。不过, 2012年的钓鱼岛事件导致在华日资企业普遍受到冲击, 这也直接影响了资方在工资集体谈判中的态度。
⑥按工会的方案, 一级员工工资增长18%(388元)。
⑦在本次罢工中工人并没有很积极地联系媒体, 他们将罢工理解成公司内部讨价还价的方式, 让外界介入并不能增加他们的谈判砝码, 反而让公司有谴责他们的理由。
⑧相关的法律规定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九条、第二十条。
⑨相关的法律规定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