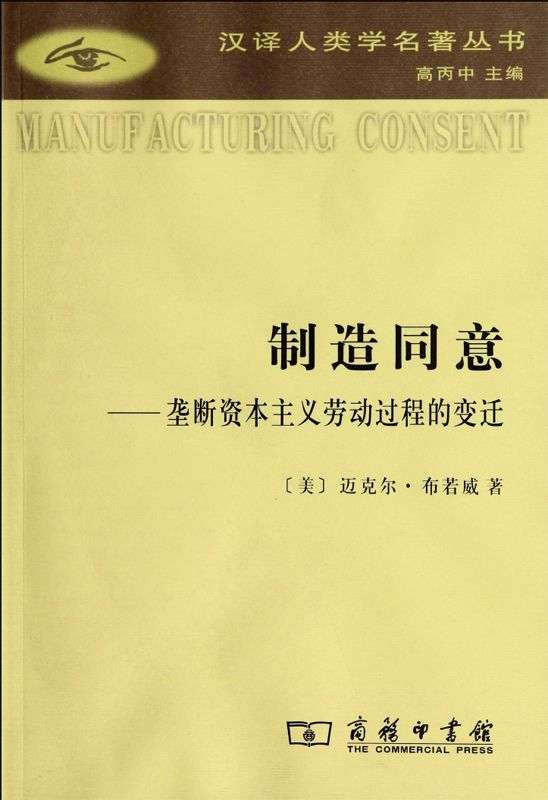转载 | 重塑中国劳工世界:30年回顾
本号不拥有转载文章的任何权利,文章不代表本号观点
若侵犯了您的资产阶级法权,请通知号主删文跑路~
重塑中国劳工世界:30年回顾
作者:Eli Friedman 和 Ching Kwan Lee
翻译:deepseek
校对:我
摘要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劳动关系以及整个工人阶级政治都因经济改革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聚焦于商品化和短工化的两个关键过程及其对工人的影响。一方面,这些过程导致了旧的社会契约的破坏和市场化的雇佣关系的出现。这意味着工人在计划经济时期享有的工作保障和丰厚福利的丧失。另一方面,商品化和短工化也引发了来自中国工人阶级的显著(但局部化)的抵抗。迄今为止,劳工非政府组织和官方工会的活动通过劳动法和仲裁机制,帮助国家将劳动冲突个体化和制度化。最后,我们简要讨论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我们得出结论,生产环节中权力的持续失衡为中国国家试图摆脱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真正的困境。
1. 引言
在过去三十年中,两个历史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就业世界:商品化和短工化。这两种趋势由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力量驱动,导致了劳动标准的急剧下降和劳动不满与骚动的明显上升,但这些骚动是分散的、局部化的且缺乏协调的。中国领导层坚持依赖高剥削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自1980年代以来,推动了社会主义就业体系的历史性改革,剥夺了工人阶级在生产环节的权力,同时在法律和行政体系中赋予了一系列“权利”。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劳工是一个由国家控制和组织的阶级,那么在改革时期,中国国家与全球及国内资本之间的强大利益联盟使其变得分散化和个体化,虽然偶尔会有反抗的火花,但缺乏可持续的集体力量。
中国劳工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在世界各地,社会契约的侵蚀、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以及工人权益的剥夺比比皆是。然而,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超过8亿,全球最大——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使得中国劳工的状况尤为引人注目。在这篇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劳工的综述中,我们希望突出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和劳动力的社会构成,这些因素塑造了商品化、短工化和分散化的独特过程和政治。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描述就业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转向市场驱动的法律合同(或无合同)劳动。文章的第二部分将这些就业的转变置于国家和资本利益及权力关系的配置,以及导致主要由农民工组成的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移民政策中。在讨论了就业的政治经济之后,我们将对中国劳工的“争议领域”进行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将看到,法律改革是国家调节和遏制劳工抵抗的策略,而工人则通过法律和非法手段进行抗争,工会和劳工非政府组织(NGO)则作为政治稳定的力量与日益不安的劳动力并存。最后,我们将考察中国劳工政治中的一些重要近期事件,即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事件表明,尽管劳工在短期内未必对政府构成政治挑战,但它确实对国家试图从依赖出口的积累模式转向依赖国内消费的模式构成了限制。
2. 就业改革:从社会契约到法律(或无)合同
劳动力的商品化
劳动力的商品化是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的核心过程。与其他商品一样,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现在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剥离并出售给他人。这一过程对中国工人来说是动荡和痛苦的,尤其是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1950年代至1980年代末)建立的就业体系是一个去商品化的体系。这一体系被中国著名的“铁饭碗”形象地捕捉到,它是一个城市工人被行政分配到城市工作单位的实际终身雇佣体系,这些单位形成了自己的层级,国有企业位于顶端,其次是各级政府经营的集体企业。工人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地位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机会(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养老金、住房、医疗和教育机会的权利)由国家保障和执行,工人则向国家宣誓政治忠诚和服从。因此,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少数临时工从农村招募到国有企业参加生产运动。但总的来说,中国的工作场所以终身雇佣和最小流动性为特征,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最基本的政治控制单位(Walder 1986)。
随着中国经济从中央计划和国家所有制转向市场竞争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就业体系也随之进行了彻底改革。随着不受铁饭碗雇佣体系束缚的私营和外资经济部门的兴起,国有企业被迫打破铁饭碗政策以保持竞争力。在长达约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劳动立法来制度化劳动法治,或通过市场导向、自愿性和个体化的“劳动合同”来规范雇佣关系。工人不仅失去了就业权,而且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养老金、住房和医疗制度改革也大幅削减了工人的福利权益。现在,大多数福利都是基于雇主和雇员对保险计划的供款来提供的,这些责任在法律上应在劳动合同中规定(Lee 2007: 第1章)。
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向劳动合同的转变被证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作为改革时期新就业体系基石的《劳动法》的执行遇到了各种阻力。《劳动法》于1995年生效,正式要求所有类型企业的所有员工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然而,从一开始,合规情况就参差不齐,尤其是在私营和外资部门,这些部门在就业方面已经超过了国有部门,占今天城市就业的50%以上(见图1)。在2007年向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负责劳动立法的官员表示,只有约50%的企业与员工签订了合同,而非国有企业的签约率仅为20%。在签订的劳动合同中,60-70%是不到一年的短期合同(东方法律文化中心 2008: 5)。国务院2006年《中国农民工研究报告》提供了一个权威的描绘,其中劳动法治明显缺失。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对40个城市的调查,在来自农村的1.2亿农民工中,只有12.5%签订了劳动合同,只有15%参加了社会保障计划,10%有医疗保险(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13)。不到一半(48%)的农民工定期获得工资,而52%的人报告称工资经常或偶尔被拖欠(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116)。68%的农民工每周没有休息日,54%的农民工从未获得法律要求的加班工资,76%的人没有获得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 2006: 214)。这些只是《劳动法》颁布十年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中的一部分。
图一,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就业的短工化
与国有部门私有化的总体趋势和社会契约的削弱并行,中国的就业在几乎所有部门都变得高度非正规化。两位经济学家通过挖掘各种统计数据发现,“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到2005年,10%的城市工人登记为个体经营者,另有36%的人未登记,既未被雇主报告也未被自我登记”(Park 和 Cai 2007)。通过分析中国内部的两个主导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就业的非正规化性质:(i)就业从制造业的重新组织;(ii)临时工和“派遣工”在所有经济部门中的日益普遍,包括国有制造业部门和重工业。
图二,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正如Evans和Staveteig(2009)所令人信服地论证的那样,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英国模式明显不同,因为该国相对较小比例的劳动力受雇于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就业比例在199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渐下降。尽管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有所回升,但显然被第三产业的增长所超越(见图2)。更重要的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增加,其占GDP的份额在2009年上半年上升至47.4%(《人民日报》在线,2009年7月27日)。随着中国开始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并越来越关注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剩余劳动力不太可能继续被制造业吸收。2008年末出口经济的崩溃加剧了这一问题。随着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从1992年的19.8%增加到2008年的33.2%(《中国统计摘要》2009: 44),最近的就业增长大部分来自服务业。毫无疑问,这些工作中相当一部分是白领办公室工作,这些工作往往伴随着较高的工资、较好的福利和更严格遵守相关劳动法律。但大部分新的服务业就业集中在食品和饮料、酒店、娱乐、清洁、医疗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工人极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以及雇主的个人指责。尽管工会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就业的更大稳定性,但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的工会直到最近才关注服务业。总的来说,法律执行和国家监督薄弱甚至不存在,大量工人仍然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受雇,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受到工资扣除、解雇等问题的困扰。由于缺乏集体或制度化的机制来执行劳动法律,服务业的就业一直是并且继续是高度非正规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受雇于这一部门,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是非正规的。
即使在相对正规化的制造业领域,就业关系日益灵活化的趋势也显而易见。在中国,这些工人被称为“派遣工”,他们由招聘公司雇佣,然后被“派遣”到需要高度灵活且高度可剥削劳动力的制造企业。据估计,2008年派遣工的数量约为2.7亿(Qiao 2009: 322)。根据2008年《劳动合同法》,派遣工只能被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岗位,并应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获得报酬(Y. Liu 2009)。尽管派遣工的出现是相对较新的现象,但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管理者(并非雇主)利用其与工人之间模糊的正式关系,经常违反现有的劳动法律(Coke Concerned Student Group 2009),而政府迄今为止对此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纠正措施(Sun 2009)。通过模糊管理者、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派遣劳动制度使工人处于极其不稳定的境地,几乎没有任何工作保障。
这种雇佣方式并未局限于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而是渗透到了高度理性化、高度机械化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中的工人过去曾享有较高的安全感和相对的物质福利。在国有企业中,过去以“铁饭碗”著称的领域,灵活的分层雇佣制度在管理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Gallagher 2004, 2005; O. Zhang 2009),派遣工甚至出现在石化、铁路和电信等关键行业(Li 2005)。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中,约有10%的员工是派遣工(Qiao 2009: 322)。像汽车行业(L. Zhang 2008)和电梯制造业等需要相对熟练劳动力的行业,也雇佣正式合同工与派遣工、临时工或“实习生”并存,后者的工资、福利和工作保障明显较低。这种分层雇佣制度的影响是,除了使非正式工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外,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也被打破(L. Zhang 2008)。因此,这种安排不仅对非正式工人来说存在问题,对正式工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将越来越难以对雇主提出集体要求。
劳动条件和权利侵犯
当商品化和短工化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得到有效法律监管时,劳动标准不可避免地下降,工人的困境加剧。尽管基于部门、所有制类型、地区和劳动力构成的工作条件存在巨大差异,但一些常见的劳动违法行为困扰着中国的工作场所。虽然政府偶尔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欢迎,但劳动权利侵犯仍然普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本应负责执行国家劳动法律——通常更关心资本积累而不是执法,中央政府对此也持容忍态度。因此,劳动和法律权利侵犯不能归因于少数“坏苹果”的活动,而是中国国家在过去30年中追求的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中国就业体系的政治经济将在下一节讨论。在这里,我们想重点介绍一些因商品化和短工化而出现的普遍问题。
中国工人面临的最常见问题包括长时间工作、低工资、雇主不支付加班费和社会保险、工资拖欠、缺乏适当的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歧视(种族、性别等)、非法解雇以及对常见工作错误的严厉罚款(A. Chan 2001)。在这些问题中,以下特定类型的权利侵犯受到了研究人员、媒体和政府的广泛关注:(i)工资拖欠和工资未支付。作为问题严重性的一个小指标,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在对已建立工会的企业进行部分调查时发现,2003年有417亿元人民币(61亿美元)的工资被拖欠(《中新网》,2004年11月7日)。这肯定只是总金额的一小部分。虽然这种现象在许多行业的工业和服务业中都很普遍,但在建筑行业中尤为突出。这主要是由于该行业内部融资和就业系统的复杂性。(ii)未支付的加班工资:尽管近年来加班工资的规定已广泛宣传,但雇主经常采用不透明的工资计算方法,导致大量加班工资被克扣。(iii)煤矿行业中的死亡: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非国有煤矿在煤炭生产中的重要性增加,导致事故频发(Wright 2004)。因此,在2000年代初的几年中,每年约有6000名矿工死亡(Liu et al. 2005: 510)。(iv)长时间/不规律的工作时间:在高度季节性的消费品行业中尤为突出,雇主通常要求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或更长时间,通常甚至一个月都没有一天休息。
这些问题并未被政府忽视,某些国家机构,特别是工会和劳动部门,已采取措施试图解决最严重的侵权行为。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下文将详细讨论),该法试图在劳动关系中加强法律遵守。该法大幅增加了对拒绝与员工签订合同的雇主的罚款,并且有许多报告表明,这一措施相对有效。更具体地说,政府最近对煤炭行业进行了雄心勃勃的重组,部分原因是为了减少每年大量的死亡人数。根据官方数据,2009年有2632名工人死亡,同比下降了18%(《卫报》,2010年1月20日)。此外,大城市的工会和劳动部门也努力解决工资拖欠问题。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2008年全国劳动部门追回了83.3亿元人民币的拖欠工资。
所有这些措施都值得欢迎,并且可能有助于缓解过去几年中最残酷的剥削形式。然而,国家采取的大多数行动都是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事后解决劳动冲突。最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该法在中国工人和雇主中引起了最多的关注。希望所有工人都能持有合同,因为劳动部门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无法处理冲突。然而,冲突的根源,即生产环节中缺乏制衡力量,并未通过这些措施得到解决。政府的法律行动仅仅是权宜之计,不太可能解决导致恶劣工作条件的根本权力失衡问题。
3. 中国就业的政治经济
中国劳工的困境根源于中国威权政治体制,权力由中国共产党垄断,工人被剥夺了最关键的武器:自主组织工会的权利。这一结构性问题因改革领导层追求的发展战略而加剧。尽管这些战略在多年中改变了方向和重点,并未形成一个连贯或精心规划的“中国模式”,但三个核心特征对于理解劳动标准的普遍侵犯尤为重要。它们是:地方积累、法治和永久移民。
首先,地方积累指的是经济分权战略,以增强地方精英自由化经济的动力。通过允许省和地方一级的财政收入留存,财政分权在地方官员中产生了巨大的既得利益,他们倾向于培育有利于投资者的亲资本环境,私有化以前集体所有或国有的企业,并允许薄弱的劳动监管制度。中央政府从地方积累创造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中受益,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各省争夺更大的利润份额,这在1994年的财政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总的来说,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主导了就业的商品化和短工化,并共享一种挤压劳动力的发展战略。
然而,积累的必要性必须与合法化的必要性相平衡,即在被统治的阶级中创造共识,并提供某种冲突解决手段,以便在和平和扩大的基础上进行积累。更根本的是,劳动合同的执行需要颁布《劳动法》并建立规范劳动关系的官僚机构。这使我们进入“法治”战略,即试图将冲突引导到由国家控制的官僚和司法机构中。在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的法律改革伴随着中央权威的立法活动的显著增加以及司法和法律队伍的专业化。“依法治国”于1999年写入宪法,并成为政府、立法机构和党的报告中广泛采用的词汇,常被提及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400多项法律中,包括主要的劳动立法,如《劳动法》(1994年)、《工会法》(1992年和2002年修订)、《劳动合同法》(2007年)、《就业促进法》(2007年)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年)。此外,大量国务院法令和部门规章(具有不同程度的正式法律效力)规定了从最低工资水平、工伤赔偿到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规则的一切内容。问题始终在于执行。由于中国司法机构依赖地方政府提供资金和人事任命,而地方官员优先考虑积累,法院在作出裁决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然而,法律和法律机构的存在对工人来说似乎是捍卫他们利益的唯一合法途径。我们将讨论工人的抵抗如何部分被吸收到这个法律和官僚迷宫中,部分被不可预测和威权的“法治”系统推向街头。
最后,中国移民制度的特殊性对于低工资农民工的供应以及防止劳工骚动导致激进化和升级至关重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的一项全国调查,农民工估计有1.2亿,占工业就业总人数的64.4%,占服务业就业人数的33%。他们的平均年龄为32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Qiao 2009: 315)。绝大多数农民工持有农村户口,必须在城市地区申请临时居住证才能生活和工作。许多地方的养老金规定、医疗政策和就业实践对他们存在歧视,因为他们不是法律上的“本地”居民。这种两级公民等级制度自1950年代末以来一直存在,由基于地方的配给制度强制执行。它作为国家对人口物理和社会流动性的控制手段,并保证了农村剩余向城市工业化的转移。自1980年代以来,这一制度逐渐放宽,为国内外资本提供了巨大的劳动力池,并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战略成为可能。中国农民工制度的基石是这些工人原籍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安排。根据法律,每个农村居民都有权在其原籍村获得一块土地,由她作为出生成员的村集体所有和分配。迄今为止,尽管靠近城市开发中心的农村地区土地征用增加,农民工仍然与家庭农田保持长期的社会和经济联系,特别是在失业、结婚和生育时。只要移民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在城市的教育和医疗权利处于劣势或不足,农村经济仍然贫困,中国农民工就被锁定在永久移民的位置上。由于没有成为城市公民的法律权利,农民工依赖城市的工作来支持家庭生计和农村的社会再生产。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安全阀也抑制了集体能力的发展,因为许多人在危机期间返回农村,无法或不愿意维持长期的法律斗争或非法抗议(Lee 2007)。因此,他们薄弱的组织(没有独立工会)和工作场所(主要从事低技能工作)杠杆进一步受到持续集体动员的缺乏的阻碍。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探讨的那样,在中国改革政治经济下出现的劳工行动形式,包括法律和非法动员、工会法律代表和服务导向的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4. 争议领域
法律动员
由于政府推动“法治”、颁布劳动立法以及改革劳动争议解决制度,正式处理的劳动争议数量大幅增加(见表1)。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是提起民事诉讼的前提。
在这一总体争议数量增加的背后,可以辨别出某些模式,说明劳动冲突的焦点和分布。首先,1990年代最具争议的省份是广东、重庆、上海、福建和江苏,这些地区经历了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深圳拥有超过600万农民工,到2000年,仅深圳一地的仲裁劳动争议数量就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就仲裁数量的增长而言,四川、内蒙古、天津、甘肃、山西和新疆在1995年都实现了三位数的增长率,这可能反映了国有部门工人就业条件的迅速恶化。其次,就所有制类型而言,以1996年为例,国有企业占仲裁争议的34%,而外资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占48,121起案件中的21%、26%和10%,涉及189,120名员工。第三,大多数争议是经济性质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支付是最常见的冲突原因(占50%),另有约30%的争议涉及合同终止和解雇。工资拖欠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尤为突出(那些由外资全部或部分拥有的企业)。
大多数这些争议案件源于员工的申诉而非雇主。根据地区的不同,他们在50-80%的案件中成功解决了不满。然而,工人权利的保护仍然不足,因为仲裁裁决的执行并不总是有保障,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很容易屈服于地方政府和雇主的压力。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政府和工人都对这一制度非常重视,2007年通过了新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简化仲裁程序,取消仲裁费用,并延长受侵害工人申请仲裁的时间限制。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了52万起新案件,比2007年同期增长了50%。预计这一数字将在未来几年急剧增加,反映了东南沿海地区工厂关闭和大规模裁员的数量增加。此外,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法律和非法行动之间的界限可能很模糊。当工人被鼓励寻求法律和官僚救济,却发现地方政府经常与雇主勾结时,他们会被鼓励采取集体行动,以引起上级政府的注意,纠正地方的不公。
工人抗议
尽管在毛泽东时代劳工骚动并非闻所未闻(Lee 2010),但国有部门私有化、重组和裁员的加速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未知的叛乱水平。虽然抗议活动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但在东北工业重镇尤为严重(Hurst 2009)。突然面临裁员、临时性的增加、减少的工资和福利以及“生存危机”(Chen 2000),国有部门的工人开始积极并明确地利用毛泽东主义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捍卫他们突然受到威胁的生计(Lee 2000, 2002)。这种抗议的数量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不断扩大,并在2002年春天辽阳的壮观抗议中达到象征性的高潮。虽然工人抗议可能减缓了私有化进程,并说服国家保留大量大型企业(Cai 2002),但这些事件都没有有效阻止商品化和短工化的进程。
在社会关系上(以及很多时候在空间上)远离国有部门的抗议,是中国“新”工人阶级——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的叛乱。尽管这些工人比国有部门的同行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低、女性比例更高,但在过去10年中,他们打破了顺从和被动的刻板印象,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抵抗(J. W.-I. Chan 2006; Pun 2005),既有隐蔽的,也有极其公开的。虽然总体上接受了“法治”的霸权话语,但中国工业中心的农民工在官方渠道未能解决他们的不满时,越来越愿意采取激进的直接行动。工资拖欠、工作和生活条件、管理虐待、工伤和低工资是最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能引发叛乱。通常,农民工会首先尝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他们的不满,如果他们能够忍受漫长的调解、仲裁和可能的诉讼过程,他们有很大的机会赢得赔偿。但很多时候,案件被认为不适合官方干预,或者工人无法等待一年或更长时间来解决,他们会诉诸直接行动。一些常见的策略包括罢工、堵路、静坐和威胁自杀。近年来,有报道称出现了更激进的行动,包括工厂占领、骚乱和谋杀(老板)。尽管有例外,但国家通常避免严厉镇压农民工抗议,并且通常会做出一些让步。
虽然中国的工人抗议尚未对政权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但这些抗议的级别很高,并且在近年来急剧增加。官方报告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在2000年代初迅速增长,最终在2005年达到87,000起。虽然这是政府最后一次发布此类数字,但有广泛报道称,2008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惊人的120,000起(《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2月9日)。这些群体性事件中与工人相关的比例尚不清楚,但肯定占了很大一部分。正如已经讨论的那样,工人法律动员已经增长了15年以上,并且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通过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趋势只会加速。全国范围内,2008年劳动争议增加了98%,并且在2009年上半年继续增加,广东、江苏和浙江三个关键省份的增长率分别为41%、50%和惊人的160%(《财经》,2009年7月13日)。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将受侵害工人引导到法律系统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不幸的是,法律在工作场所的执行仍然薄弱,因此不满继续增加。严重超负荷的劳动法院无法跟上他们收到的案件数量,因此工人经常诉诸更激进的行动。虽然无组织的工人叛乱的增加迫使国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主要是通过立法让步实现的。但国家在给予工人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方面寸步不让。
(a)工人动员的病毒式传播
尽管我们迄今为止认为中国的工人抗议仍然是高度分散的,但有一些相对高调的事件导致了全国其他地区的模仿行动。钢铁和码头工人的连续罢工是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其中一个成功的行动引发了同一行业但在不同地点的工人叛乱。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行动是有意识组织和协调的,而是罢工在媒体报道后“病毒式传播”。
这种“病毒”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7年4月7日,当时深圳盐田港的大约300名工人罢工,瘫痪了码头工作,阻止了10,000个集装箱的装卸(《新快报》,2007年4月9日)。除了要求更高的工资外,工人们还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同寻常的要求,即建立自己的工会,这表明他们希望对自己的工作场所有更大的控制权。鉴于港口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深圳市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劳动局和工会迅速介入调解。很快达成了解决方案,管理层同意将所有工人的工资提高3%,并额外增加500元/月。深圳市总工会决定在公司设立工会,尽管工人不太可能对这一过程有太多控制权。然后,仅仅几周后,在象征性的5月1日,深圳另一个港口——赤湾集装箱码头——的工人也罢工了(《美联社》,2007年5月2日)。数百名罢工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每月至少四天休息,减少罚款的严重性,并要求雇主遵守有关加班工资的相关法律。罢工爆发后,这个故事从媒体上消失了,可能表明政府对不满进一步蔓延的担忧。
这种模仿式的罢工扩散在2009年夏天的另一系列备受关注的事件中再次出现。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的中国钢铁行业重组的一部分,私营的北京建龙公司将获得国有通化钢铁公司的控股权。在重组前的准备阶段,即将上任的总经理陈国君召集通化工人开会,解释公司未来的计划。在会上,陈告诉员工,公司的员工将从目前的13,000人减少到5,000人。不出所料,这引发了一些工人的愤怒,但陈毫无悔意,喊道:“如果你们今天不杀我,让我活着,我保证你们连一碗菜汤都喝不到”(《中国日报》,2009年7月31日)。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广泛私有化期间的激进工人抗议浪潮相呼应(Cai 2002; Hurst 2004; Lee 2002),据报道有30,000人上街抗议,砸毁警车,最重要的是,包围了陈并将其殴打致死。这个故事在媒体上广泛报道,大多数记者对工人表示同情。在互联网上,对工人的支持和对陈国君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傲慢的谴责加剧了局势的紧迫性。重组计划迅速搁置,工人们取得了胜利,尽管是血腥的胜利。
不到三周后,河南省林州钢铁公司发生了非常相似但不太壮观的情况。根据中央政府的钢铁行业重组计划,林州工厂上个月已出售给私营钢铁公司丰宝。由于对私有化中的待遇不满,数百名工人于8月11日开始抗议。几天后,400名工人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政府官员堵在工厂办公室内。由于通化的暴力事件在每个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现场部署了防暴警察,人群最终散去。然而,第二天,政府宣布取消私有化计划,再次将胜利交给了激进的钢铁工人。
尽管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地方的罢工可以激发另一个地方的罢工,但这种抗议的性质仍然是根本上的分散性,因为“细胞”并没有结合形成“组织”。虽然这种通过特定行业的罢工扩散表明工人意识和战斗性的提高,但引发连锁反应的行动在规模、媒体可见性和经济功能的核心性方面都相当特殊。因此,尽管这种跨地区的工人抗议是一个有希望的发展,但这种现象的传播可能会继续受到现有政治条件的限制。
(b)工会
尽管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人的零星和分散抗议并未显著改善劳动条件,但它们确实引发了国家的回应。也许这一点在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及其下属工会的近期行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ACFTU在国家和有时省级及市级层面推动亲劳工立法方面相当有效,但企业级工会仍然非常薄弱,通常无法执行法律和合同(F. Chen 2009; Ding et al. 2002; Lau 2001)。尽管市级工会扩大了为个人提供法律咨询的能力(Chen 2004),但ACFTU仍然坚决反对工人动员或为工人阶级提供自主的集体权力基础。尽管许多近期的法律改革值得欢迎,但中国的工会仍然完全是对集体行动的反应,工人很少承认ACFTU的合法性。
首先,有必要解释一下中国工会的基本性质。ACFTU声称拥有2.13亿会员,这将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全国工会联合会。众所周知,它正式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任何独立工会主义都必然会遭到严厉镇压。工会层级中的每个单位都受到双重政治控制:首先是结构上横向的党组织,其次是直接上级工会组织。
中国工会经常成为嘲笑的对象,有些人问“ACFTU真的是工会吗?”(Taylor和Li 2007),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生活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梦幻世界”中(Metcalf和Li 2005)。中国工会主义者对这些批评自然感到不满,经常声称外国人对ACFTU存在“误解”。我们认为,确实存在一些误解,尽管原因与工会官员所说的不同。与认为中国工会正在变得法团主义(A. Chan 1993)或存在“双重身份”(Chen 2003)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中国工会将自己视为并表现得像政府机构(Lau 2003)。当工会确实参与代表时,重要的是要注意代表关系中的代理位置: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我们代表你”(无论你是否喜欢)的过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我们(工人)授权给你”。一旦澄清了这一误解,ACFTU及其下属工会的许多活动就更容易理解了。
因此,工会对日益增加的工人叛乱的回应并不是试图将这种无组织的社会运动引导到社会权力关系的重组中。相反,它正是人们期望从国家机构中得到的东西:立法和行政。1995年的《劳动法》、2001年的《工会法》以及最近的2007年《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扩大了工人的法律保护,并增加了工会的正式权力。尽管ACFTU在倡导这些法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在《劳动合同法》的通过中最为重要(该法的细节将在下文详细讨论)。这些法律改革是对工人抗议增加的回应,如果没有ACFTU的倡导,这些改革可能不会实现。
然而,正如Feng Chen(2007)所强烈指出的那样,工人个体法律保护的增加被集体权利的缺乏所削弱,特别是结社自由。正如许多工人试图建立自己的组织但未成功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ACFTU保留了工会主义的完全垄断。由于原因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ACFTU结构中的企业级工会仍然非常薄弱,工人很少认同它们(Howell 2003, 2008)。在少数情况下,基层工会主席试图更积极地为其会员的利益而战,他们经常面临雇主无节制的报复。更高级别的工会很少有效干预以阻止这种反工人活动。最明显的案例是在2009年初,当时一位活跃的工会主席被一家由广东省总工会拥有的酒店解雇(《南方日报》,2009年4月23日)。尽管工会活动家被工会拥有的酒店解雇的讽刺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响,但这种基本模式在全国各地无数次出现。由于工会在生产环节完全从属于管理层,人们严重怀疑法律中规定的个人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执行。在工人拥有自己的自治权力基础之前,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c)劳工非政府组织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出现一些以劳工为重点的非政府组织(NGO)。该地区在1980年代曾是资本主义式劳动关系出现的中心地带,到1990年代,这里聚集了数千万受到严重剥削的农民工。这些工人所面临的恶劣生活和工作条件已经在前面讨论过。部分由于全球北方的消费者运动要求“无血汗”产品,部分由于基层劳工活动家的坚定行动,一些中国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旨在帮助工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想强调这些非政府组织活动的两个显著特点:(i)它们大多数情况下积极参与了国家的“法治”项目,并试图将工人的个体申诉引导到仲裁和法院系统中;(ii)它们经常受到国家的骚扰和监视,因此其活动范围仍然相当有限。
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及制度背景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和内容。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在将国际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引导到个体化和“行政化”劳动冲突的目标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正如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一样,基金会和国际组织对非政府组织部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Bartley 2007; Luong 和 Weinthal 1999),其结果之一是,中国工人自己定义的申诉往往被忽视(Friedman 2009)。部分由于中国的限制性政治环境,许多外国基金会(大多数希望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致力于推动“法治”项目。由于禁止会员制资助,结果是大多数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都适应了这些要求。
由于外国资助者和中国国家都支持法律主义的劳工权利活动,大多数组织主要从事法律咨询和法律培训(Yin 和 Yang 2009; Yue 2007)。确实,一些非政府组织更大胆,尝试宿舍组织或建立工人委员会(J. W.-I. Chan 2006),并且在一些情况下,它们为工人提供了指导,如果不是领导的话,在与管理层的更对抗性斗争中。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工人提供组织技能培训,以便他们能够在工作场所中自己进行斗争。尽管如此,大多数劳工非政府组织的注意力集中在为工人提供事后建议,告诉他们如何通过官方管理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程序来解决申诉。由于违反法律不仅仅是偶尔发生的事件,而是国家资本积累模式的固有趋势,劳工申诉是普遍存在的。由于工人没有集体和持久的手段来防止生产环节中的这些违法行为,非政府组织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典型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外,现在还有一种蓬勃发展的“公民代理人”业务,即法律工作者通过收费帮助农民工争取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瞭望》,2007年10月30日)。尽管许多活动家意识到法律主义方法可能非常有限,但由于劳工问题对国家的政治敏感性,加上基金会对法律导向项目的支持,他们往往别无选择。
尽管大多数中国的劳工非政府组织相当保守,通常不参与任何直接的政治活动,但它们经常受到国家的骚扰和压制。2009年1月,广东省党委政法委员会的一份内部报告泄露,证明地方政府对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深感担忧。该报告重点关注“公民代理人”和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被具体点名,并认为它们对广东省的社会稳定构成了“实际影响和潜在威胁”。这些组织被指“加剧冲突”、“破坏劳动关系”、“扰乱公共管理”,以及最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以下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部分摘录,说明了这些担忧:
“由于目前‘职业公民代理人’没有受到政府的有效控制,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抓住了机会,利用其深厚的财力优势,花钱建立了一些专门关注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维权’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接受外国反华势力的资助,并以免费法律代理为诱饵。它们参与一些典型的诉讼案件,积极进行人权工厂调查,并收集有关我国劳动和法律问题的负面信息。这是为外国敌对势力攻击我国的劳动制度、法律制度、人权制度以及诽谤我国政府形象提供口实。”
该报告暗示劳工权利工作与“反华”情绪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揭示了后毛泽东时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但更相关的一点是,尽管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非政府组织有反国家活动,这些组织的运作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在日常运营中面临巨大挑战。
新挑战
我们认为,商品化和短工化是塑造中国就业体系的两个基本过程,并引发了众多分散的工人抗议,这些抗议在政府眼中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政府的回应是通过另一项劳动立法——《劳动合同法》——来加强合同的力量。该法律的措施包括要求雇主向雇员提供书面合同,并限制临时工的使用,但却恰逢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这对《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利。然而,随着中国出口的海外市场大幅萎缩,中国政府被迫进行另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这一次的重点是创造国内消费需求,这意味着提高劳动大众的工资水平,并用技术密集型和更高附加值的产业取代低技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不同的需求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劳工面临的新挑战。
(a)《劳动合同法》
《劳动合同法》——我们已经提到过——被广泛视为自1995年《劳动法》以来中国劳动关系法律框架中最重要的变化。这部新法律引发了或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多的公众辩论。在2006年发布法律草案后,政府收到了超过19万条公众意见,其中许多来自普通工人。虽然官方工会和工人(在个体化的意见中)倾向于支持该法律,但外国和国内资本公开动员反对该法律,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尽管该法律在颁布前被大幅削弱,但它被广泛视为工人的胜利。虽然我们不否认该法律可能对某些工人群体产生积极的物质影响,但该法律的颁布是国家试图“依法治国”并将劳动冲突分散化的又一强烈迹象。鉴于这种政治环境,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新法律能够充分解决生产环节中深层次的权力不对称问题。
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劳动合同法》被当局视为一种手段,通过正式化劳动关系来减少社会冲突并解决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新法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与“无固定期限”合同相关的条款,这使得解雇员工变得更加困难(J. W.-I. Chan 2009; Wang 等 2009)。根据该法律,工人在连续签订两份固定期限合同或在同一雇主工作满10年后,有权要求无固定期限合同。该法律还扩大了工会在谈判集体合同、确定工作规则和裁员方面的作用。最后,该法律要求在裁员时增加遣散费,这在失业保险体系非常薄弱的国家尤为重要(Cooney 等 2007)。
当该法律的草案版本向公众发布时,雇主们采取了非常强烈的反对立场。国内外资本代表,包括欧盟商会和美国商会,大力游说政府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一些组织,最著名的是上海美国商会,公开威胁政府,如果该法律通过,资本将外流。商界充满了恐惧,一些人认为《劳动合同法》意味着中国正在限制“自由企业”(《星期日泰晤士报》,2007年10月21日)。然而,尽管抗议声浪汹涌,中央政府还是推进了该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07年6月批准了该法律。新法律于2008年1月1日生效。
尽管草案法律获得通过,但雇主的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果。2008年3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副部长公开讲话,安抚雇主的恐惧,称“(无固定期限合同)绝不是铁饭碗。它不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中国日报》,2008年3月10日)。根据许多人的说法,他是对的:法律的最终版本增加了管理层的自主权,并显著削弱了工会在确定工作规则和裁员程序中的作用。以前工会需要批准这些行动,而法律的最终版本只要求工会“咨询”,从而为雇主单方面行动开了绿灯。此外,《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14种情况下可以解雇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工人。这些情况包括企业遇到“严重生产困难”、“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和“客观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准确判断这些条件是否适用,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如果工会未在合同谈判或裁员过程中被咨询会发生什么(S. Chen 2009)。这些“战略性模糊”(Ngok 2008)允许地方应用的灵活性,也表明实际实施中存在广泛差异。
现在对《劳动合同法》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进行最终分析还为时过早。但似乎围绕该法律的激烈公众辩论引起了更多工人的注意,结果是许多工人向劳动局提出投诉。特别是,有许多工人投诉雇主未能提供合同,这是新法律严厉惩罚的行为。2008年官方劳动纠纷的大幅增加可以归因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金融危机,因为纠纷在2008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上升。也有迹象表明,该法律对那些拥有其他文化或社会资源的员工更有用(Cooney 等 2007),并且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相对强势的地位。沃尔玛和白领员工以及科技巨头华为的成功反击就是这种现象的明显例子。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法律是否比以前执行得更严格,但似乎更多的工人现在有了书面合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式化的第一步已经实现。
正是在我们讨论为工人提供合同的问题时,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合同法》本质上是一种进一步引导工人个体申诉进入官方劳动调解系统的尝试。确实,法律中有关于集体谈判和工会在确定工作规则和咨询裁员方面的作用略有增强的条款。但在缺乏能够将其成员构成集体力量的工会(或与工人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的工会)的情况下,这些条款变得无关紧要。那么,为什么这部法律是国家试图“依法治国”并将劳动冲突分散化的进一步表现呢?因为法律中最严厉的惩罚是针对那些不向工人提供合同的雇主(并且这一特点被广泛宣传),越来越多的工人现在可以获得合同。这对国家来说绝对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书面合同,劳动局无法处理申诉。因此,向工人提供合同是国家吸收冲突并(试图)将其排除在工作场所和街道之外的必要条件。然而,严重超负荷的劳动局常常无法高效和公平地解决这些冲突,结果是工人仍然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些问题变得尤为明显。
(b)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回应
随着美国住房危机在2008年秋季演变为金融危机,进而成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出口依赖型经济遭受了多年来的首次重大冲击。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这种中断导致了大规模失业,引发了广泛的冲突、抗议和骚乱,并迫使约2000万农民工返回农村(《纽约时报》,2009年2月2日)。这场危机是另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见证中国国家与资本联盟的日益强大,因为政府的回应主要是帮助雇主以促进就业,而不是直接为工人提供工作。
尽管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均衡,但所有以出口为导向的地区都受到了严重影响。2009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21.9%(《彭博新闻》,2009年7月31日)。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是高度依赖出口的珠江三角洲。2008年12月中旬,广东省政府的一位官员透露,当年有15,661家中小企业关闭或破产,但尴尬地坚称“没有出现‘关闭潮’”(《羊城晚报》,2008年12月17日)。在制造业重镇东莞,政府报告称有117名老板在未支付工人应得工资的情况下逃逸。对于那些没有关闭的工厂,订单大幅减少,导致大规模裁员。
虽然数百万工人只是回家过春节,许多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但仍有数千起纠纷、官方投诉、罢工和骚乱。正如前面提到的,纠纷在以出口为导向的江苏、浙江和广东省增长尤为迅速。有报道称,工人采取了激进的直接行动,上海一家电子厂的1000名工人举行大规模静坐,抗议六个月的加班工资和福利未支付(法新社,2009年12月9日),以及北方城市临汾一家纺织厂的6000名工人占领工厂(《星期日泰晤士报》,2009年2月1日)。骚乱不仅限于制造业,出租车司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几乎前所未有的罢工浪潮,司机在重庆、广州、汕头、佛山、三亚、厦门、荆州、随州、周至、南阳、安陵、大理和永登等地罢工。在东莞,一家玩具厂的数百名工人在工作场所内激烈抗议,最终与警察发生冲突,砸毁并掀翻了一辆警车(《广州日报》,2008年11月26日)。此外,还发生了几起由于裁员和遣散费相关的违法行为导致的工人杀害经理事件(《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31日)。
那么,国家的回应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危机的加剧,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开始在某些小方向重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担心失业增加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他们开始说服雇主避免裁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禁止国有企业在未经政府明确批准的情况下裁员(《新京报》,2009年1月15日;《半岛晨报》,2009年1月14日)。地方政府设法说服少数雇主公开承诺不裁员,希望其他公司效仿。许多地方政府采取措施确保雇主不会在未支付工人应得工资的情况下消失。
然而,总的来说,这场危机揭示了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资本的利益作为主导。中央政府宣布允许地方冻结最低工资的增长,并可以减少雇主对员工社会保险的供款(《华尔街日报》,2009年1月16日),许多城市利用了这一政策。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广泛报道称,政府官员为了保持投资者的满意度而忽视雇主的法律违规行为。在山东,有报道称一位政府官员告诉外国投资者不要“太担心”《劳动合同法》(《中国法律博客》,2009年1月),而在广东,执法者被告知可以推迟对涉嫌违法的经理进行调查(《广州日报》,2009年1月1日)。广东省政府辩称,“这种方法是为了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绝不是为嫌疑人提供保护”(《新快报》,2009年1月1日)。
再次,工人阶级无法行使协调一致的集体权力,意味着工人的利益被忽视和侵犯。由于劳动仲裁案件的解决通常需要一年甚至两年时间,法律体系在工人最需要的时候无法为他们伸张正义。此外,在缺乏有组织的劳工游说的情况下,国家的回应主要是帮助雇主。由于缺乏有组织的政治权力,工人阶级的骚乱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试图解决深层次的申诉(虽然通常是徒劳的)。资本的法律违规、通过法律调解未能解决冲突、工人采取直接行动的基本模式在整个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经济危机只是增加了这种动态的频率和强度。
5. 结论
本文的分析聚焦于就业结构的变化、劳工组织和抵抗的模式,以及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试图总结中国工人在过去30年中经历的巨大变化。就业关系的特点是从社会契约向法律合同的转变,这一过程意味着劳动力的商品化。短工化是由于私营部门就业机会的增加,而国有企业则进行了改革,使其更接近私营企业的模式。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差异很大,但员工经常面临长时间工作、低工资、随意解雇以及工资和保险未支付的问题。此外,临时工和“派遣工”在经济中的增加进一步削弱了可能的阶级凝聚力,增加了工人生活中的不稳定性。
工人并没有在面对这些对其利益的攻击时保持被动。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人都频繁抗议,尽管这些骚乱的起源和动态各不相同。虽然大多数工人活动仍然是分散的,并且通常不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质,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定行业的工人骚乱已经蔓延到多个工作场所。然而,国家仍然坚决反对独立的工人组织,这一点从对通常保守的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持续骚扰、监视和压制中可以看出。与此同时,官方工会仍然与以积累为导向的国家机器紧密相连,不愿意与资本对抗。或许ACFTU在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成就是通过了《劳动合同法》,这部法律理论上增加了对工人的保护。然而,对该法律的后续修订却显著减少了对任意解雇的法律保护,并且有广泛报道称该法律的执行不力。最后,当2008年末出口经济崩溃时,国家接受了资本的利益作为主导的程度变得更加明显了。
这些动态揭示了改革时代中国阶级和劳工政治重新配置的重要特征。市场化引发了工人骚乱的大幅增加,但迄今为止,这些骚乱尚未凝聚成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国家的回应是试图通过立法将冲突排除在外,结果是将本应是集体问题的问题个体化。随着官方调解的劳动冲突继续迅速增加,生产环节中的深层次权力不对称——这使雇主有胆量经常无视法律——依然未受触动。党和国家创造了一个近似新自由主义理想的局面,即一群分散的个体被迫作为个体面对国家和资本的主导权力。即使是有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法律,也常常得不到执行,因为地方官员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紧密相连。由于工人比雇主更有动力执行法律,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是允许工人行使集体和独立的权力。赋予工人个体化的法律权利无法解决根本的不平衡。然而,赋予工人结社自由的集体权利是中央政府似乎从根本上反对的一项措施。其结果是,国家高层陷入困境,他们不愿意努力推动其法律的充分执行。
这意味着,国家当前试图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基于国内消费的经济可能会受到现有阶级和国家权力动态的阻碍。随着有猜测称政府可能会试图强制提高工资以减少经常账户盈余并刺激国内消费(《彭博》,2010年2月9日),工资和劳动法律的执行变得至关重要。然而,最近一系列旨在加强工人法律权利和官方工会权力的法律似乎并未减少劳动冲突或增加对法律的遵守。因此,似乎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商品化、短工化和法律个体化不仅对工人——他们不断受到重新配置的阶级统治关系的压迫——有负面影响,而且对实现中央政府的自身目标也有负面影响。
Reference
Bartley, T. (2007). ‘How foundations shape social mov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and the rise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Social Problems, 54 (3): 229–55.
Cai, Y. (2002). ‘The resistance of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in the reform period’. The China Quarterly, 170: 327–44.
Chan, A. (1993).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31–61.
—— (2001).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E. Sharpe.
Chan, J. W.-L. (2006). ‘Chinese women workers organize in the export zone’. New Labor Forum, 15 (1): 19–27.
—— (2009). ‘Meaningful progress or illusory reform? Analyzing China’s Labor Contract Law’. New Labor Forum, 18 (2): 43–51.
Chen, F. (2000). ‘Subsistence crise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4: 41–63.
—— (2003). ‘Between the state and labour: the conflict of Chinese trade unions’ double identity in market re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76: 1006–28.
—— (2004). ‘Legal mobilization by trade unions: the case of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52: 27–45.
—— (2007).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rights: labor’s predicament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0: 59–79.
—— (2009). ‘Union power in China: source, operation, and constraints’. Modern China, 35: 662–89.
Chen, S. (2009). ‘Dui “laodong hetong fa” shishi guocheng zhong ruogan wenti de sikao’ [On some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bor Contract Law]. Hunan sheng gonghui ganbu xuexiao, 23 (3): 30–2.
Coke Concerned Student Group (2009). Hangzhou kekoukele zhuangpingchang diaocha baogao [Investigative Report on Hangzhou Coca-Cola Bottling Plant]. Coke Concerned Student Group.
Cooney, S., Biddulph, S., Li, K. and Zhu, Y. (2007).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 responding to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labour relations in the PRC’.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Law Journal, 30: 786–801.
Ding, D. Z., Goodall, K. and Warner, M. (2002).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role of trade union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3 (3): 431–49.
Eastern Center for Legal Culture (ed.) (2008). The Dispatching of Services. Shangha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Evans, P. and Staveteig, S. (2009).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 Davis and F. Wang (eds.),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9–84.
Friedman, E. (2009). ‘External pressure and local mobilizatio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4 (2): 199–218.
Gallagher, M. (2004). ‘Time is money, efficiency is lif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9 (2): 11–44.
—— (2005).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well, J. (2003). ‘Trade unionism in China: sinking or swimming?’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19 (1): 102–22.
—— (2008).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eyond reform? The slow march of direct elections’. China Quarterly, 196: 845–63.
Hurst, W. (2004). ‘Understanding contentious collective action by Chinese laid-off worker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9 (2): 94–120.
—— (2009). 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u, R. W. K. (2001). ‘Socio-political control in urban China: changes and crisi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2 (4): 605–20.
—— (2003). ‘The habitus and “logic of practice” of China’s trade unionists’. Issues & Studies, 39 (3): 75–103.
Lee, C. K. (2000).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rotes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Ethnography, 1 (2): 217–37.
—— (2002). ‘From the specter of Mao to the spirit of the law: labor insurgency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31: 189–228.
—— (2007). Against the Law: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10). ‘Pathways of labour insurgency’. In E. Perry and M.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Curzon, pp. 71–92.
Li, H. (2005). ‘Fazhan yu yinyou: woguo laowu paiqian xianzhuang zhi wojian’ [Development and hidden dangers: my views on the current conditions for Chinese dispatch labor]. Shengli youtian dangxiao xuebao, 18 (5): 46–9.
Liu, T., Zhong, M. and Xing, J. (2005). ‘Industrial accidents: challenges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afety Science, 43: 503–22.
Liu, Y. (2009). ‘Cong tonggongtongchou kan paiqiangong laodong pingdeng wenti’ [Looking at the problem of equality for dispatch lab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Hunan xingzheng xueyuan xuebao, 2 (56): 49–51.
Luong, P. J. and Weinthal, E. (1999). ‘The NGO paradox: democratic goals and non-democratic outcomes in Kazakhstan’. Europe-Asia Studies, 51 (7): 1267–84.
Metcalf, D. and Li, J. (2005). Chinese Unions: Nugatory or Transforming? — An Alice Analysis.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Ngok, K. (2008). ‘The changes of Chinese labor policy and labor legi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73: 45–64.
Park, A. and Cai, F. (2007).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un, N.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Qiao, J. (2009). ‘The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and labour conditions in 2008’. In Y. Xin, X. Y. Lu and P. L. Li (eds.), Society of China: Analysis and Forecast.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pp. 312–27 [in Chinese].
State Council Research Office Team (2006). China’s Migrant Workers Survey Report. Beijing: China Yanshi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Sun, F. (2009). ‘Laowu piaqian yonggong fangshi xia laozi sanfang xingwei de boyi fenxi’ [An analysis of tripartite labor-capital activities under the system of dispatch labor]. Fazhi yu shehui, 243.
Taylor, B. and Li, Q. (2007). ‘Is the ACFTU a union and does it matter?’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9 (5): 701–15.
Walder, A.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ng, H., Appelbaum, R. P., Degiuli, F. and Lichtenstein, N. (2009). ‘China’s New Labour Contract Law: is China moving towards increased power for workers?’ Third World Quarterly, 30 (3): 485–501.
Wright, T. (200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al mine disasters in China: your rice bowl or your life’. The China Quarterly, 179: 629–46.
Yin, G. and Yang, M. (2009). ‘Shenzhen laogong yu Shenzhen laogong feizhengfu zuzhi’ [Shenzhen’s labor and Shenzhen’s labor NGOs]. Chongqing gongxueyuan xuebao (shehui kexue), 23 (6): 112–15.
Yue, J. (2007). ‘Feizhengfu zuzhi yu nongmingong quanyi de weihu —yi panyu dagongzu wenshu chuli fuwubu wei ge’an’ [NGO and the protection of peasant workers: a case study of Panyu Service Department for Peasant Workers]. Zhongshan daxue xuebao, 47 (3): 80–5.
Zhang, L. (2008). ‘Lean production and labor controls in the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73 (1): 1–21.
Zhang, O. (2009). ‘Ladong hetongfa banbu beijing xia dui laowu paiqiangong daiyu wenti de yanjiu yu sikao’. Zhiye jishu, (106):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