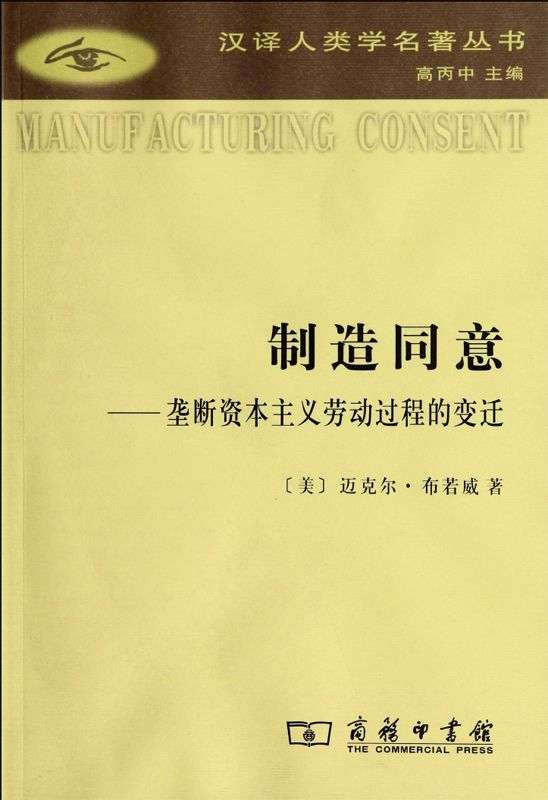转载 | 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
本号不拥有转载文章的任何权利,文章不代表本号观点
若侵犯了您的资产阶级法权,请通知号主删文跑路~
包揽式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
汪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当前的劳工研究过于关注珠三角经验, 而忽视了“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基于在内地城市的田野调研资料, 详细剖析内地中小城市新兴制造业中独特的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形态和劳工抗争行动。研究发现, 虽然受限于地方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分散的劳工生产生活形态, 内地的劳工抗争在规模、战斗性、诉求、制度影响等层面与珠三角地区存在差异。但内地的劳工抗争也自有其特点, 突出表现为劳动纠纷频发化和日常抵抗普遍化。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内地政府扶持政策下勉强生存, 由此导致频繁的劳动纠纷, 本地工人的城市化进程和遍及工厂内外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是这些劳动纠纷的催化剂;另一方面, 本地工人的地域认同、社会网络和家庭化趋势为其普遍的日常抵抗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 包揽式政商关系 本地化用工 劳工抗争 区域差异
一、“世界工厂”的劳资关系:被忽视的区域差异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 多年来被经济奇迹掩盖的劳工权益问题, 在2010年的富士康“连跳”和本田罢工事件后, 终于被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学界更是普遍将2010年作为中国劳动关系的分水岭。研究中国劳工政治的学者不再回答“为什么不”的问题 (Lee, 1998) , 相反, 劳工团结行动的形成动力、组织形态、发展趋势、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潜在影响, 才是近年来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相关文献致力于从各个层面揭示中国劳工抗争政治的变化:工人行动开始部分克服分散、自发的弱点, 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组织性和战斗性, 其影响也超出特定厂区范围, 在特定行业、区域扩散;部分抗争行动不再仅仅是对企业侵权行为和管理方式做出反应, 也不再满足于争取“底线型”权利, 而是要主动争取工资上涨、工会重组等“增长型”利益。推动劳工抗争政治转变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包括:资本全球转移和“用工荒”背景下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增长、 农民工代际结构的变化、信息技术的运用、工业化经历中工人经验与能力的提升、沿海地区产业升级战略下政治机会结构的出现等 (Silver, 2003;Lee, 2007;Chan&Pun, 2009;Pun&Lu, 2010;郭于华等, 2011;蔡禾, 2010;闻效仪, 2014;汪建华, 2015) 。关注阶级不平等的学者从中看到了“阶级形成”的趋势, 而致力于构建集体劳权的学者则将这种变化概括为中国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 (Chan&Pun, 2009;常凯, 2013) 。
劳工群体与各种社会力量的互动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任何人只要对后发国家的劳工运动史稍加整理 (Seidman, 1994;裴宜理, 2001;具海根, 2004) , 便可知这种结合对国家治理的潜在挑战。部分劳工组织顺应劳工行动的变化, 主动调整工作方向。他们为工人的行动带来信息、经验和策略上的支持, 并帮助工人提炼诉求、推举代表、代理集体谈判。劳工组织、劳权律师、高校师生还进一步借助网络媒体, 将劳工权益议题带入到社会公众视野中 (汪建华等, 2015) 。
一些地方工会不得不通过改革来回应这些的变化, 否则将面临失去工人群众的危险。广东省的工人集体维权行动最为频繁, 劳工组织最活跃, 工会改革力度也最大 (闻效仪, 2014) 。广东省在基层普遍建立起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强力协调综治、维稳、信访、公安等部门, 有效应对可能的群体性事件。其他相关举措还包括强化社区监视和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Zhuang&Chen, 2015;Chen&Kang, 2016) 。
然而, 对当前劳工政治的讨论和判断过于依赖珠三角经验。以劳工抗争的实证研究为例, 笔者共检索到65篇中英文文献,①其中, 49篇文献的调查资料来源于珠三角, 10篇文献以珠三角和其他地区的实证调研为基础, 只有6篇文献以其他地区的田野资料为依据。
仅仅将同为沿海重要经济体的长三角引入比较, 便可知珠三角的劳工政治有其特殊性。从劳动权益的各项指标看 (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工作时间、社保购买率、工作环境等) , 长三角要好于珠三角。从典型的集体抗争个案来看, 一些有影响力的罢工行动、三次大规模的城市骚乱和富士康工人的“连跳”, 几乎都发生在珠三角。研究表明, 两大经济体劳工政治的差异, 可能与其早期工业化模式和劳动力来源有关, 长三角在早期突出表现为“本地资本 (乡镇企业) 本地工”, 珠三角则盛行“外来资本 (港台企业) 外来工”的组合 (张敏、顾朝林, 2002;万向东等, 2006;刘林平等, 2011) 。
因此,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世界工厂”的劳工政治时, 应该对其可能呈现的区域性差异予以充分的重视。综合以往相关文献, 笔者认为, 下列因素可能在区域层面对劳工政治产生影响: (1) 区域工业化历史与资本的来源, 比如早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私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和依托地缘优势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珠江模式” (费孝通, 2014) , 以及继承晚清和民国工业传统的华北乡村工业 (顾琳, 2009) , 劳动关系可能各具特色; (2) 地方政商关系, 地方政府在GDP竞赛和分税制改革背景下发展经济的冲动与地方经济的不平衡, 将决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谈判能力和劳动治理方式 (周黎安, 2007;陶然等, 2009) ; (3) 工业集中程度与劳工生产生活形态, 比如, 从历史上看, 台湾地区的工人在空间分布上要远比韩国分散, 分散的工业布局消解了产业工人组织化和集体认同发展的可能 (Sen&Koo, 1992) ; (4) 劳动力市场的本地化程度, 当大量本地劳动者进入到工厂, 企业的用工招聘、生产管理和劳动争议处理可能都要受到当地基层政权、乡缘网络的干预 (Paik, 2014) 。
已有少量研究尝试讨论中国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李静君对广东和东北工人的抗争政治进行了比较 (Lee, 2007) , 不过该研究更多地是对农民工和下岗国企工人两类群体维权方式的比较。其他对区域劳工政治差异的讨论包括:市场化、全球化程度与劳工政治 (Blecher, 2010) , 地方政治资源和治理策略与地方政府治理罢工的模式 (孟泉, 2014) ,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地方工会改革特点 (Friedman, 2011) 。
相对于珠三角区域相关研究而言, 当前学界对沿海其他经济区域劳工政治的讨论固然远远不够;而对于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和沿海省份欠发达城市的劳动关系, 则缺乏实质性的研究和讨论。近十年来, 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沿海地区企业的要素成本和综合经营成本逐渐上升, 用工荒持续存在, 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大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蔡昉等, 2009) 。有鉴于此, 本文将研究聚焦点投向内地, 考察内地中小城市工业化面临的独特环境, 并借此进一步分析内地的劳工政治。
地方政商关系的差异对劳工政治的影响是最不可忽略的。由于并不具备沿海地区在区位、基础设施、产业集群、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内地的地方政府只能被迫在土地、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资本更多优惠, 并在劳动权益和环保方面做更多妥协 (陶然等, 2009;耿曙、陈玮, 2015) 。为了吸引大资本入驻,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下属各级政府组织网络和有限的财政收入, 帮助企业招工, 或者迫使属地的职校、技校学生以实习名义进入企业打工 (郭于华、黄斌欢, 2014) 。相反, 沿海城市则有更大的选择性, 为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部分沿海省份和城市通过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提升劳动权益标准、默许劳工维权行动等方式, 迫使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当地搬离 (张永宏, 2009;孟泉, 2014) 。恰如李静君 (Lee, 2007:11-12) 指出的, 地方发展经济的冲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使得劳工抗议呈现高度地方化的特征。
内地城市的劳动力来源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维度。相比沿海地区聚集大量跨省、跨地市流动的农民工, 内地中小城市企业的工人本地化程度更高。对江西丰城某内迁陶瓷厂的研究发现, 90%的一线员工来自本市或附近地区, 工厂的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相比沿海更人性化, 工人拥有相对完整和丰富的社会生活 (黄斌欢、徐美龄, 2015) 。笔者对太原和郑州两地富士康园区的调研则表明, 大规模土地征迁迫使当地大量年轻人进入到工厂中, 其厂内破坏纪律、厂外报复管理者的行为, 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企业粗暴管理文化的制衡 (汪建华, 2014) 。
本文将主要借助田野材料详细剖析内地中小城市新兴制造业中独特的政商关系、本地化用工形态和劳工抗争政治, 并进一步梳理前两者对劳工抗争政治的影响, 最后, 研究还将尝试对内地中小城市开发区与珠三角工业区的劳工政治进行比较。②
本文的田野材料主要来源于中部某内地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实地调研。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方合市③的城区人口约为50万人, 正好可以作为内地中小城市的典型样本。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于2001年, 后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开发区园区规划面积为100平方公里, 职工总数在3万人左右。自2015年3月开始, 笔者曾4次赴方合市调研内地企业的劳动关系, 2016年4月笔者有幸获准进入开发区3家企业 (1家本土企业和2家内迁企业, 下文将会有详细介绍) 进行短期实地观察。调研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与普通工人、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各级管理者的日常交谈、深度访谈和座谈。另外, 结合笔者在珠三角地区长期的调研资料, 论文还将尝试梳理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
二、包揽式政商关系
在发展主义导向下, 任何地方政府与资本都存在着一定的结盟关系。但在沿海发达地区, 地方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关系是选择性的, 政府可能更倾向于扶持那些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工业资本, 对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企业则逐渐迫使其转移, 且其对资本提供的支持范围也是有限度的。之所以将内地地方政府与工业资本的关系概括为“包揽式政商关系”, 原因有二:第一, 虽然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 在土地、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有可能给予资本一定的优惠条件 (耿曙、陈玮, 2015) , 但内地地方政府却有可能答应资本更为苛刻的条件, 并动用各种行政资源, 在协调贷款、厂房宿舍建设、手续办理、项目政策争取、用工招聘、劳动纠纷预防化解等方面尽可能提供服务。第二, 内地地方政府对资本类型并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对各种层次的外来资本都要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尽管优惠条件会有所差别。
(一) 包揽式政商关系:形成条件、表现形式与可能后果
内地中小城市在发展区位方面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 开发区企业普遍反映的困难包括: (1) 产品出口运输时间长, 物流成本大; (2) 缺乏成熟的产业配套, 企业需要额外支付到其他地区的采购成本; (3) 专业技术、管理和销售人才缺乏。因此, 内地政府对资本类型的选择余地很小。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中, 他们不得不答应资本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 尽可能地为资本提供大包大揽式的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1) 土地、税收、信贷方面的优惠; (2) 通过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工业地产建设, 减少企业前期投入成本; (3) 代办企业入驻相关手续, 争取中央和省里相关项目、政策; (4) 政府帮助招工, 并提供各种就业优惠政策; (5) 放宽环保和劳动权益标准; (7) 帮助企业平息劳资纠纷。
税收方面, 方合市对于新引进的企业, 在地方税种上, 以先收后返还的方式, 前三年全免, 后两年减半。土地价格上, 工业用地8万元/亩, 这个土地价格可能要低于该市在土地征迁补偿、三通一平 (通水、通电、通路、场地平整) 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方面的综合成本。④为了打造特色产业, 政府还进一步为相关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各地争相为支持所谓的特色产业协调贷款、降低土地成本, 通常导致产能过剩和重复性建设的问题, 继而引发企业债务危机, 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 (江飞涛等, 2012) 。方合市当前正在经受类似的困扰。
在硬件环境上, 当地政府除了完善铁路、公路、供电、供水、道路绿化、路灯安装等方面的基础设施, 正在大力打造“工业地产”。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小企业入驻, 开发区建造了若干“科技孵化基地”⑤和一批公租房, 极大降低了企业在厂房、仓库、宿舍、食堂等方面的建设成本。⑥政府期望能从这些“孵化基地”中孕育出若干大中型企业。泰理光电的闫总认为, 100家企业只要能成长起来两家企业便算成功, 泰理光电当年也是从孵化基地走出来的, 现在已经是上市企业, 并且是开发区第一纳税大户 (访谈编号:clcp2319) 。
方合市还为入驻企业提供专门的工作组, 企业只要准备好相关材料, 所有手续由工作组成员协调办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 政府采取市领导挂点、部门结对、官员驻厂等方式, 帮扶重点企业。比如, 通过争取进口旧硒鼓批文、将国检监管站设在厂内等举措, 政府帮助硒伦电子厂有效减少了原材料和物流成本 (访谈编号:clcp2321) 。
企业入驻以后, 最紧要的任务莫过于招工。方合市的年轻劳动力大多跑到沿海就业, 劳动力供给有限, 加上许多中小企业的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缺乏吸引力, 缺工现象严重。早期由于某大企业迅速扩张, 方合市各级政府部门被广泛动员起来招工, 人社部门还专门为招来的职工提供部分岗前培训, 即所谓“招工就业培训三位一体”。当前为了完成招工任务, 园区劳动部门在西南地区和省内周边县市建立了二十余个现场招聘网点, 并与十余家人力资源中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对中介机构的招工予以补贴。为了提升对外地劳动力的吸引力, 开发区出台了一系列外地员工就业优惠政策, 包括推荐就业满3个月奖励、探亲往返车票报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优惠等。在市内, 开发区劳动部门则借助各类媒介 (手机短信、网络、电视) 、各乡镇街道, 以及打横幅的方式来推送相关信息。在企业急需用人时, 还会在人流密集地设立招工点。但这似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用工难的问题。一些企业长期处在大规模缺工的状态, 工人招得多, 流失也快。
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而对企业采取大包大揽的做法, 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资本投资, 但也造成了一些不可忽视的后果: (1) 政府角色错位, 企业过度依赖政府; (2) 政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投入过多, 造成大规模重复性建设、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 并将地方政府拖入到债务连带责任中; (3) 一些企业利用政府急切发展工业的愿望谋求其他利益, 比如有些企业表面上要搞工业投资, 实际上兴趣却在拿商业用地搞房地产, 最后房地产搞起来了, 工厂却早早倒闭了; (4) 鼓励了部分企业的短期行为并引发欠薪问题, 比如, 有些企业在享受当地的优惠政策后, 便搬到其他地区;一些经营不善的小企业在欠薪时逃匿也非常方便, 由于在当地并没有土地、厂房、宿舍, 也没有相关设施投入, 他们只需要把设备搬走即可; (5) 许多原本应该淘汰的企业在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得以继续生存, 在这些企业中, 劳动者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 劳资矛盾频繁多发。⑦
(二) 地方劳动治理方式
要想吸引资本、留住资本, 另外一类隐形的优惠政策自然就是降低劳动和环境方面的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在当地政府部门看来太超前了, 是按照沿海的发展情况制定的, 不符合内地经济发展现状。劳动和环保部门的执法都要服从经济发展的大局。在开发区, 劳动部门的干部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经济景气, 大量招人, 累得要死;经济不景气, 流水一样的离职, 大量的劳动纠纷, 大量的调解工作” (访谈编号:clcp2323) 。而在市人社局, 有一次笔者帮助某电子厂的劳动者反映该企业未缴社保、克扣工资等方面的违法行为, 劳动部门的领导却向笔者解释, 监察大队到企业执法, 需报市领导批准, 而且, 企业对劳动部门的执法也未必配合 (访谈编号:clcp2323) 。开发区一位领导则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劳动部门执意要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 则可能要承担“破坏投资环境”的严重后果 (访谈编号:clcp2310) 。
一方面不敢主动监察、处罚企业的违法问题;另一方面, 劳动部门在处理涉及社保、工资等方面的劳动争议时, 也非常慎重。毕竟许多企业选择到内地投资, 降低用工成本是重要因素, 而规避社保、加班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则是常见做法。因此,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出于对企业的保护, 以“不告不管”的原则行事, 而且对于案例牵涉人数也要仔细斟酌。如果是单个劳动者前来投诉相关问题, 仲裁院一般依法仲裁, 但如果涉及人数较多, 则不得不考虑可能的影响了, 倘若带动起更多的员工前来维权, 企业补偿支付的负担就太大了。
劳动部门如此弱势, 不要说社保、加班工资、劳动合同等方面的监察和规制难以到位, 即便是触及底线的欠薪问题, 也难以解决。遇到劳动者投诉企业欠薪, 开发区劳动部门只能给企业打电话, 讲道理, 给双方做调解工作, 许多调解不了的工作还是要转移到市劳动部门。但市劳动部门的调解工作企业同样不太配合, 仲裁结果也未必能够得到执行。这里最重要的症结在于, 当前并没有约束企业老板欠薪行为的诚信系统, 法律上的“恶意欠薪入罪”也往往由于老板与地方领导的私人关系, 难以真正得到执行 (访谈编号:clcp2323) 。不少劳动者也谈到, 类似欠薪的问题, 到劳动部门投诉, 一般很难得到解决, 除非成规模的员工上街闹, 或者天天上访。
为避免潜在的劳动纠纷, 开发区会定期为企业人力资源主管提供专题性的法律培训。在经济不景气需要裁员时, 规避或减少劳动者的离职补偿便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重要议题。劳动部门一般会和企业保持沟通, 就相关问题统一口径。某大企业曾因为经济不景气, 需要裁掉近万人。为了避免可能的动荡, 省市区各级政府紧急介入, 以灵活的政策将员工分批处理, 省政府为企业补缴了约1亿元社保, 为企业员工提供充足的失业保证金, 市区镇各级政府则广泛参与调解工作。
我们参与桑弘的调解, 给它慢慢分散, 一起去搞肯定不行, 拖一拖有些人就走掉了。有些个别跟他谈, 你也别去闹, 给你点钱, 就算了。桑弘 (职工) 到市委市政府堵门都堵过几次, 到信访局我都去过几次。真正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去补, 桑弘早就关闭掉了。一裁一万人, 怎么补, 补不起。出来一些政策, 和他们座谈, 解决, 走一部分, 留一部分, 你也不用上班, 每天签到, 保证你的劳动关系, 每个月给你600多块钱生活费, 过渡, 慢慢的。太多了, 一万多人, 把他们瓦解了。等到效益好了, 回来上班把这些钱补给你。 (访谈编号:clcp2316)
为了赢得资本的青睐、培育当地有限的资本, 在土地、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条件之外, 地方政府还需要提供各种包揽式的服务, 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厂房宿舍、代办入驻手续、争取项目政策支持、帮助企业招工、降低劳动和环保标准、平息劳动纠纷等。对当地的劳动关系而言, 这种包揽式的政商关系既招来了过多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纵容其侵害劳动权益的行为, 引发层出不穷的劳工抗议行动;也在策略和程序层面有效阻止工人维权行动和诉求的发展。
三、本地化用工
企业选择在内地设厂投资,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对于选择就近工作的内地工人来说, 在薪酬待遇方面的妥协则是以保障完整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为前提。相比沿海地区的外来工, 内地中小城市工人以下四个社会特征对工厂管理和劳动关系的影响不可忽视: (1) 家庭生活相对完整; (2) 社会关系网络广泛存在于工厂内外; (3) 生产、居住空间相对分散; (4) 就近城市化成为趋势。
(一) 工人的地域来源
从笔者与开发区12家企业人力资源主管的座谈资料来看, 一线生产工人和基层管理者多为本市居民, 而中高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则多来自外地。在笔者进行实地观察的三家企业, 人力资源主管提供的企业用工数据也呈现出类似趋势 (见表1) 。总体而言, 绝大多数普工来源于本市, 非本市职工多分布在管理和技术岗位, 且层级相对较高。
表1 方合市开发区三家企业用工情况
| 工厂 | 职工总人数(人) | 普工人数(人) | 普工平均工资(元/月) | 工时制度 | 非本市职工比例及主要岗位分布 |
|---|---|---|---|---|---|
| 沃土粮油厂 | 350 | 245 | 3000 | 两班倒 | 2%(7人),技术工 |
| 泰理光电厂 | 1100 | 700 | 3500 | 两班倒 | 33%(359人),管理、技术工、普工 |
| 硒伦电子厂 | 1000 | 700 | 2400 | 长白班 | 10%(100人),管理、技术工 |
当然, 三家企业的用工特点也有一定差异, 这与企业的发展历程、工时制度、薪酬待遇有较大关系。沃土粮油厂是方合市土生土长的农业龙头企业, 因此包括管理者在内的绝大部分职工来源于本市。而同为2010年以后从沿海搬迁过来的企业, 泰理光电厂和硒伦电子厂显然都倾向于从沿海地区招聘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者。不过从一线工人队伍构成来看, 本地职工相对更倾向于在没有夜班、上班时间相对较短、能够兼顾家庭的硒伦电子厂工作, 而泰理光电厂则吸收了相当一部分周边县市的务工者, 他们大多居住在宿舍或工业区, 更能接受工时长、倒夜班但工资收入高的工作。
进入工业区工作的本市居民, 大部分住在城区或周边乡镇, 骑电动车上下班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那些来自本市偏远乡镇或周边县市的劳动者, 或居住在宿舍, 或与家人租房同住。开发区本市工人的社会来源, 主要有四种: (1) 农业剩余劳动力; (2) 工业区周边失地农民, 这是一个最让企业头疼的群体; (3) 国企改制后的下岗职工; (4) 在城市买房, 需要进厂工作还房贷。
实际上, 开发区的企业普遍倾向于招外地工人而非本地工人。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认为, 本地工人排外心理强, 不服从管理;倘若遇到劳动纠纷, 便要依仗工厂内外的乡土势力闹事;平时也动不动因为农业生产、红白喜事和家庭事务请假。人力资源经理往往还要进一步指出两类工人的两大差别:本地工人稳定性差, 工作条件稍不合意便要离职, 而外地工人大包小包生活物品带过来, 不会轻易离职;本地工人学习能力差, 难以培养, 而外地工人住在宿舍中, 即使下了班, 也可能继续在车间钻研。不过企业管理层也明白, 他们的薪酬待遇对外地工人显然缺乏吸引力, 外地劳动者若要外出, 当然倾向于到沿海地区工作, 收入更高, 还能开阔眼界。那些在方合市工作的外地工人, 无外乎以下三种类型:在方合念书的外地学生;投亲靠友 (不少是外地管理者的亲属) ;因家人在方合市工作稳定而随迁过来。因此, 企业并没有多少选择, 本地化用工是主流模式。
(二) 劳工社区生活形态
相比沿海城市, 拥有完整的家庭生活, 是在方合市这样的内地中小城市工作最大的优势。在推动劳动者从沿海回本地工作的因素中, 首当其冲的是小孩, 比如小孩学习成绩不好、身体不好、想念小孩等;其次是照顾父母;也有许多是看重生活质量的, 比如觉得与家人在一起开心、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要远比住在沿海出租屋舒服、可以经常拜会亲朋好友等。他们也会反复对比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和生活成本, 虽然沿海收入更高, 但食宿、小孩上学、来回奔波的费用也明显更高。因此, 每年春节过后, 许多从沿海回家过年的工人会先在家乡找工作, 实在没有合适的工作, 才外出沿海打工。本地工人如此看重家庭生活, 以至于那些工资待遇高、管理规范的“两班倒”企业, 也面临招工难问题, 泰理光电的人力资源主管认为, 许多工人宁可选择工资低的工作, 也不愿选择工资高但要倒夜班的工作:
沿海企业的话, 每家都差不多, 我在昆山工作很多年, 人家招工的时候根本不用问, 无非是两班倒或三班倒, 必须要倒班的。这边招工就是, (应聘者问) 上8个小时不?双休不? (访谈编号:clcp2319)
实行“两班倒”的企业劳动强度大, 且影响工人的身体和家庭生活, 因此这类企业同时面临招工难和离职率高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切入点同样是挖掘工人的家庭生活需求。比如, 为了稳定员工队伍, 泰理光电厂非常鼓励职工介绍自己配偶进厂, 或者在单身的年轻人中发展出双职工家庭。在生活方面, 泰理光电厂为住在城区的职工安排了专门的厂车接送, 并为住宿舍的夫妻提供了两个楼层的夫妻房。泰理光电厂的口号是:夫妻进厂, 两年买车, 五年买房。开发区另一家做锂产品深加工的企业, 劳动强度较大, 以男工为主, 为了稳住队伍, 会安排一些男工的妻子从事辅助性岗位 (访谈编号:clcp2301) 。
工厂管理不仅要考虑工人的家庭生活需求, 也要考虑工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许多工人都在工业区各企业间反复跳槽, 因此, 除了其原有的亲缘、乡缘、同学关系网络, 他们在反复流动的过程中也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广泛的同事关系。正是通过这些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 工人随时可以了解到任何一家大企业的用工信息、薪酬标准、管理制度。总体而言, 园区主要企业的情况在工人那里基本是透明的, 员工的网络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中型企业的行为形成制约:
在这边的管理与沿海最大的不同就是方合市是一个小城市, 人员不多。你想留住长期的工人, 一定要树立一个好口碑, 如果一个工人觉得这里好呢, 他就要介绍亲朋好友过来。如果他认为这个企业不好, 就告诉亲朋好友不要来。 (访谈编号:clcp2321)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开发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之间的网络, 这类网络往往更紧密。园区企业领导会定期聚会, 讨论贷款方法、政策动向等。在每年调整工资时, 企业领导相互间也会保持沟通, 旨在避免出现一些企业工资过高“破坏市场行情”的情况 (访谈编号:clcp2319) 。同样, 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之间也会有比较频繁的接触。开发区各部门为了协调各企业的工作, 也会建立各种各样的QQ群和微信群。毫无疑问, 中高层管理者相比普通工人, 更有条件强化网络关系。
与工人的家庭化居住趋势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再生产空间的分散化。与珠三角劳工聚居在工厂宿舍和附近的城中村不同 (任焰、潘毅, 2006a) , 开发区绝大部分本市工人每天往返于家庭与工厂之间, 只有一些来自外地和本市偏远乡村的工人居住在工厂宿舍、公租房或出租屋中。从笔者实地调研的3家企业来看, 沃土粮油厂的职工由于基本来自开发区周边农村, 因此工厂根本就没有提供宿舍;硒伦电子厂只有10%的职工住在厂区宿舍, 笔者到工厂宿舍探访发现, 宿舍大量空置, 8人宿舍一般只有4人居住;泰理光电厂由于上班时间较长、外地职工相对较多, 选择住宿的职工要多一些, 但也不到20%。
普通工人的通勤工具以电动车为主, 也有部分居住在城里的工人选择搭乘公交车或厂里的通勤车。每天上下班时段, 都能在通往开发区的公路上看到浩浩荡荡的电动车大军。上下班路途中由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 雨雪天或夜间事故尤其多发。一到冬季, 工人还要迎接风吹雨打天寒的挑战。此外, 部分工人还需要克服休息、饮食上的困难。以推行“两班倒”的金鑫光电厂白班工人为例, 工人在6点半起床, 洗漱、早餐之后, 7点20分从家里出发, 7点50分打卡, 然后是早会、上班;晚上8点下班, 到家已经是8点30分, 由于公司食堂饭菜太差, 许多工人选择忍受饥饿, 回家吃晚餐;简单收拾一番, 便过了晚上10点。在这样紧凑的工作安排下, 工人陪家人尤其是小孩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 但即便这样, 大多数工人也愿意选择每天回家, 他们认为这样的境况总归要比亲子分离、外出打工的生活强。
开发区生产聚集程度同样远低于沿海工业区。与笔者在珠三角地区调研的长兴街道相比, 同样是工业聚集, 方合市开发区的平均人口密度只相当于长兴街道的2%。在珠三角地区, 高度集中的生产生活空间便利了维权工人的行动动员, 并有可能导致抗争行动的小区域传导 (Chan&Pun, 2009;任焰、潘毅, 2006b) 。但在开发区, 劳工的诉求、行动固然有可能在特定的时刻通过本地工人的社会网络串联起来, 但在分散的劳工生产生活形态中, 工人的行动大多是孤立的, 既难以获得外界力量的支持, 也很难对其他工人群体产生影响。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开发区农民工以买房为标志的就近城市化。如果加上到开发区工作的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 工厂工人的城市化比例就更高了。许多农民工正是因为有房贷压力, 才选择到开发区工厂工作。泰理厂蚀刻部门的工人报告, 车间工人30%在城市买了房, 20%原本就是城市居民。泰理厂厂车每天的搭载人数可资佐证。泰理厂每天有11趟厂车在城区和厂区之间往返, 根据笔者搭乘厂车的经验, 每趟车单程搭载人数不少于30人, 则可以判断每天搭乘厂车上下班的工人绝对在300人以上。加上骑电动车、开小车、坐公交上下班的职工, 泰理厂确有一半职工居住在城市中。
农民工城市化以后, 面临的不仅仅是供房压力, 日常衣食住行、水电煤气、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生活成本也会陡然上升。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在一定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可以从父辈获得资源支持。除去买房、小孩抚育方面的支持不说, 一些农村老人甚至要将大量农产品带到城市, 部分用于子女生活, 部分摆摊出售。对那些中年买房的农民工群体来说, 供房、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的压力层层叠加, 难以逃避。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 他们能从父辈获取的支持总体有限。一旦脱离农业生产进城买房居住, 农民工便不得不在城市寻求生计。制造业的工作虽然比服务业辛苦, 不过工资也更高, 因此对那些需要负担高额房贷的劳动者, 更具吸引力。农民工进入城市, 便再无退路, 劳资双方围绕薪酬待遇的冲突也日益频繁。
四、内地中小城市工厂的劳工抗争
内地中小城市包揽式的政商关系和分散的劳工生产生活形态,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工人抗争行动的规模、诉求、影响。在珠三角地区, 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劳工抗争行动屡有发生, 南海本田工人长达半个月的团结行动争取到大幅度加薪, 重组了工会, 开启了常规化的劳工集体谈判, 并触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潮 (汪建华、孟泉, 2013) ;东莞裕元数万人工人持续十余天的罢工行动则引发了各级工会和各类劳工组织的介入, 同时也将社保、公积金等劳工法律权益落实问题呈现在公众面前 (黄岩、刘剑, 2016) 。但内地的劳工抗争政治也自有其特点, 突出表现为劳动纠纷频发和日常抵抗普遍化。一方面, 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内地政府各种政策扶持下勉强生存, 由此导致劳动纠纷层出不穷, 本地工人的城市化进程和遍及工厂内外的社会关系网络则是这些劳动纠纷的催化剂;另一方面, 本地工人的地域认同、社会网络和家庭化趋势为其普遍的日常抵抗提供了基础。
(一) 围绕日常管理制度的斗争
粗暴的管理文化是工人日常抵抗的主要目标。若将开发区工厂与笔者在沿海调研的企业对比, 那么毫无疑问, 开发区工人的日常抵抗是一个更突出的问题。企业管理层的结构是重要诱因。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大多为外地人, 与本地社会缺乏联系, 生产管理中遇到问题, 他们也习惯性地将其归因为本地人素质不行。基层管理者则多为企业内迁后迅速培养起来的本地人, 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一线工人, 都认为基层管理者队伍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有待提高。这样的管理结构遇上工人的本地意识和乡缘亲缘网络, 自然是矛盾纠纷不断。在座谈会上, 人力资源主管普遍提到本地工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势力, 管理上的疏忽往往引发工作现场的骚动或厂外报复 (访谈编号:clcp2301) 。
工人威胁、报复管理者的现象在开发区非常常见。在一些大型电子厂, 管理层频繁被男工报复, 即使企业长期面临招工难问题, 也不得不下定决心不招男工。本地工人各种形式的抵抗确实影响了企业的管理文化和纪律要求。有人力资源主管抱怨说, 面对本地工人频繁的违纪行为, 管理者怕惹麻烦, 不想管且不敢管 (访谈编号:clcp2301) 。
工人第二类抵抗目标为企业的工时制度, 许多本地工人进入企业, 往往想着既能兼顾家庭, 又能赚点钱补贴家计。但在当前激烈的代工竞争和招工难背景下, 一些企业往往选择通过调整倒班制度、延长工作时间的方式来减少工人数量、节约用工成本, 比如将“三班倒”调整为“两班倒”, 但这对于许多想要兼顾家庭的本地工人来说往往难以接受。有一个企业在将“三班两倒”调整为“两班两倒”后, 工资虽然普遍上涨了800元以上, 工人却走了好几百人, 因为在新的工时制度下, 工作更辛苦, 且没有充足时间照顾家庭 (访谈编号:clcp2301) 。
工人不仅通过各种非正式抵抗行动影响工厂的日常管理, 有时还尝试以集体罢工的形式施压。在金鑫光电厂, 由于上班时间长 (每天12小时) 、休息时间少, 工人便针对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的10分钟早、晚例会罢工 (这20分钟不算上班时间) , 迫于员工压力, 资方将早、晚例会缩减为上班前和下班后各5分钟 (访谈编号:clcp2323) 。
还有工人因为企业的伙食问题而罢工。在沃土粮油厂, 公司原本管白班工人的午餐和晚餐。但工人普遍觉得公司饭菜实在太难吃, 因此通过罢工向公司施压, 集体要求不在厂里吃晚餐, 将晚餐折算成5元补贴发给职工。工人向笔者抱怨, 要不是中午回家吃饭不方便, 他们连午餐也不想在公司吃。在工人的行动压力下, 公司只好取消午餐并给予工人相应的补贴, 但是将白班下班时间提前了1个小时, 晚班上班时间因此长达13个小时。管理层试图以此迫使工人知难而退。后来企业又重提此事, 表示如果觉得晚班太长, 可以考虑均衡两个班次的工作时间, 前提是工人要在企业吃晚餐, 但工人并没有答应。
除了罢工、威胁、报复、离职, 说方言似乎也是一种日常抵抗手段。
我们企业管理层大部分都是外地的, 沟通不是很方便。本地的员工招的都不是年轻的, 就不会说普通话, 沟通很困难。然后他们不断在那里说土话, 在那里叽叽歪歪, 管理人员就不让他们说, 但没有用。他会说, 你连我个人的人身自由都束缚啊? (访谈编号:clcp2315)
许多企业为了防止工人抱团, 在分配生产岗位时, 都会有意识地将同一个地方的工人打散。但他们发现这种做法并不是特别奏效, 一则同一个地方的工人实在太多, 二则即便拆散了他们的乡缘关系, 也难以知晓其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 “工作以后才发现, 这个是兄妹关系, 那个是表亲关系, 好多亲戚” (访谈编号:clcp2309) 。
(二) 权益之争
要了解方合市开发区劳工抗争行动的主要类型, 有两个背景不可忽略:一是在包揽式政商关系下, 大量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得以在内地寻求生存机会;二是近年来经济下行, 企业订单更不稳定, 盈利空间更小, 劳动权益也因此更没有保障。开发区的劳动权益争议因此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类: (1) 企业经营不善, 欠薪逃匿, 工人讨薪, 这种现象最为突出, 由此引发的劳动纠纷最为频繁, 据一些人力资源主管估算, 开发区有60%的企业有欠薪问题, 以小企业为主; (2) 企业为了减少用工成本, 在社保、底薪、加班费等方面不遵守法律标准, 工人追讨相关权利; (3) 企业裁员, 工人要求离职补偿, 为了增加维权行动成功的筹码, 企业其他违法行为也被一并牵出; (4) 即便是那些相对规范的企业, 在经济下行、成本上升的压力下, 也不得不以增加计时产量、压低计件工价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 由此导致工人抗议。
通过劳动部门追讨工资、社保、离职补偿、加班费等法定权益是最常见的维权方式。倘若劳动纠纷涉及企业多数职工, 那么工人往往会直接采取集体罢工、上访等方式。近年来员工法律意识上升非常快, 原先企业习以为常的一些违法行为, 比如调休调班但不给工人算周末加班工资等做法开始越来越多地遭到工人的抗议。
因为没有按规定及时调整基本工资, 方合市开发区一些效益相对较好的电子企业还出现过一次短暂的罢工潮。早在2013年4月, 该省人社厅就公布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 但到7月许多企业还拖着不涨工资。罢工首先发生在专门为苹果做数据线代工的电子厂, 企业很快开除了几名带头罢工的工人。没想到这几位工人随即又进入另外一家电子厂工作, 在他们的带领下, 该厂也开始罢工。这几位工人接连潜入几家企业策动罢工后, 开发区的企业终于反应过来, 将他们纳入黑名单。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因为工人的社会网络在开发区分布非常广泛, 另外几家效益相对较好的电子企业受了影响也陆续罢工。据硒伦电子厂的人力资源经理回忆, 当时硒伦厂也发生了罢工, 以制造部门的一线工人为主, 最后企业通过与工人代表谈判, 每月加100元工资平息事端。
在这次罢工潮中, 除了本地工人广泛的社会网络, 城市化背景下工人的生计压力也是重要推动因素。这种生计压力在每个月发工资时能很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果企业未能及时发放工资, 那么工人很可能就要集体罢工, 因为许多工人等着拿工资还房贷。
工人的城市化进程和生活压力也在推动一些利益型争议的产生。在不断加剧的代工竞争压力和逐渐上升的生产成本面前, 企业既不可能向品牌商讨价还价, 也不可能压缩税收、物流、原材料等方面的成本, 只好在工人身上打主意。许多企业为了压缩用工成本而采取 (计时制) 加产量或 (计件制) 降工价的做法, 不断激起工人的相对剥夺感, 导致工人频繁罢工。
我们金鑫厂总是尽可能地给职工加产能。公司不赶货的时候, 从8点上到7点, 单位时间产能就高, 总是试图达到我们的身体极限;赶货的时候, 从8点到8点甚至9点, 工作时间实在太长, 单位时间产量可能相对加得少一点, 总之都是要到人的身体极限。如果产量没做到, 不能下班。在节假日, 还出现过产量不达到没有加班费的情况。金鑫厂动不动给员工加产能, 员工做不到, 于是以产线为单位频繁罢工。有一个车间只有6个人, 白班3个晚班3个, 都是操作机器的, 他们也罢工。总经理跑过去说, 你们6个人居然也能罢起工来! (访谈编号:clcp2323)
但是围绕工价和产量的集体抗议行动似乎并没有太大作用, 如前所述, 每年的工资涨幅各大公司其实已经统一商定了。“不满意就走人”, 是这些企业对待罢工工人的态度。在开发区, 虽然大部分企业缺工, 但给劳动部门施加点招工压力, 生产总归能大体维持下去, 况且资方也知道, 工人并没有多少就业选择。在开发区工作时间长了, 工人大抵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 去哪里都差不多。
与这些内迁企业的态度一样, 本地的沃土粮油厂为了压制工人的加薪诉求, 不惜损失几十万的原材料成本。参与罢工的只有6个罐装操作工, 他们都是开发区周边的工人, 入职时间最长的也只有22天, 却非常清楚自己的谈判能力, 知道如果自己不开工, 那么已经调好的三缸料液 (每缸成本在10万元以上) 都要成为废水。为此这6名工人与公司管理层在厂门口谈判, 但是双方态度都很强硬。公司表示宁可遭受损失, 也不能受这些工人要挟, 否则以后工人都会要求加薪。开除这6名工人后, 公司赶紧从省内其他兄弟企业调来几个罐装操作工, 一边生产一边培养新人。这个案例体现了内地劳工政治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本地化、城市化的劳工行动倾向、发展诉求日益提升;另一方面, 内地企业太过低端, 让步空间有限。
除了上述权益争议, 开发区附近的失地农民与企业往往牵扯其他历史遗留问题。比如, 桑弘太阳能在早期投资建厂的时候, 为了迅速推进征地拆迁进程, 给一些四五十岁的失地农民安排了工作。但到2011年, 企业经济不景气, 需要大规模裁员, 又要失去生计的失地农民自然要到企业讨说法。企业只好找来各级政府做工作, 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给失地农民宣讲法律政策, 镇政府则给他们弄了一些低保名额, 村委会则在企业和失地农民之间反复调解。
最让企业头疼的是工伤、工亡事故。一旦事故发生, 本地工人的亲属便会被广泛动员起来, 索要上百万赔偿, 否则企业就别想开工。许多企业不过是小作坊, 上百万的赔偿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此时, 各级政府又会通过调解、给政策等方式, 帮助企业早日摆脱困境。
活跃在开发区周围的, 不仅仅有工人的乡土网络和基层政府, 也有其他力量, 比如专门到医院找工伤工人的律师, 他们在帮助工人讨要赔偿的同时也能拿到可观的抽成 (访谈编号:clcp2315) 。不过推动工人维权的力量, 无论是公益还是商业性质, 都是非常有限的。
从笔者掌握的经验材料来看, 内地中小城市开发区工人的抗争行动在规模、诉求、影响力上都自有其限制, 类似劳工组织、工会的介入也很少出现。但内地工人的抗争也有其独特之处, 劳动纠纷非常频繁, 各种小型的罢工行动接连不断, 而基于本地工人对工作、生活自主性的追求, 日常抵抗也是比较普遍的。如前所述, 内地工人的抗争政治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包揽式的政商关系和本地化用工形态。
五、迈向对“世界工厂”劳资关系的区域比较
以往的劳工研究似乎过于关注那些规模化的、增长型的集体劳工抗争, 似乎过于关注劳工政治中的集体化转型或阶级形成面向, 因此, 对劳工政治的考察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区域。理论、行动与政策层面的关怀固然有助于我们挖掘劳工政治演进的可能动力, 但过度强调这些关怀, 也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现实遮蔽。诚如裴宜理 (2001:328) 所言,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家, 学界尤其应该注重劳工政治的区域差异。当前对“世界工厂”劳工政治的考察, 亟需回到其多样化的现实土壤中, 回到区域层面的工业化历史、政商关系、劳动力市场构成和劳工生产生活形态中, 回到资本和工人活动的政治、市场和社会环境中。
基于在珠三角和内地城市的田野调查, 本文尝试对当前两个区域的劳工政治进行比较 (表2) 。跨区域的比较旨在厘清珠三角那种规模化、增长型的劳工抗争政治形成的独特环境, 并力图展现与珠三角不一样的劳工政治。当前珠三角城市与内地中小城市的工业发展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地方政商关系, 其劳动力队伍构成也差别很大。从政商关系来看, 珠三角城市的地方政府与资本的结盟关系是高度选择性的, 只有那些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企业才有可能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 而低端制造业则是其定期清理的对象。同时, 相比珠三角地区, 内地政府要在土地、税收、基建、手续、项目政策、信贷、招工等方面对新引进的资本予以支持。地方劳动治理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为了顺利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珠三角地区可能会加强劳动执法, 规范企业用工, 并根据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特点, 对劳工集体维权行动和增长型诉求给予有限度的默许。相比之下, 内地中小城市缺乏选择余地, 即便是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对这些城市来说也是稀缺的。他们要做的就是为这些企业提供尽可能的服务, 包括选择性忽视企业的劳动权益问题、积极预防化解可能影响企业生产的劳动纠纷等等。
表2 珠三角与内地劳工政治的比较
| 珠三角城市 | 内地中小城市 | |
|---|---|---|
| 地方政商关系与劳动治理方式 | 与资本选择性结盟: · 扶持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企业 · 土地、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 · 加强劳动执法、规范企业用工 |
对所有资本大包大揽: · 大量引进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 · 土地、税收、基建、进驻手续、项目政策、信贷、招工等方面的支持 · 降低劳权标准,帮助企业预防化解劳动纠纷 |
| 劳动力来源与社区生活形态 | 跨省、跨地市流动农民工为主: · 低度家庭化 · 社会关系趋于原子化 · 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集中 · 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 |
本市、本县工人为主: · 家庭化 · 社会关系网络广泛分布 · 生产生活空间高度分散 · 就近工业化、城市化 |
| 劳工抗争政治 | 集体抗争政治的扩展: · 零星的日常抵抗 · 存在规模化集体抗争的形成土壤 · 追求多种法定权益,增长型诉求 · 各种社会力量介入到劳动纠纷中 · 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 |
日常抵抗与有限的劳工团结: · 普遍的日常抵抗 · 规模化的集体抗争难以形成 · 被压制的增长型诉求 · 本地势力介入到劳动纠纷中 · 仅限于在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治理方式 |
在劳动力来源与劳工社区活形态方面, 珠三角与内地中小城市也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别。珠三角的工厂中聚集了大量跨省、跨地市流动的农民工;大多数工人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周围的城中村中, 生产与生活空间高度集中;他们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这种无根的、流动的城市生活也在不断瓦解其有限的社会关系;工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不同步的, 在珠三角打工, 在老家所在的城市买房, 到一定时候返乡就业, 是部分工人折衷的城市化路径。内地中小城市则截然相反, 企业用工是高度本地化的;劳工家庭生活也相对完整;工人的社区生活比较丰富, 社会关系网络广泛分布于工厂内外;不少工人已经在当地买房居住, 尽管这会带来较为沉重的生活压力;最后, 内地开发区的生产与生活空间是高度分散的, 多数本地工人不在宿舍居住, 他们每天往返于工厂和家之间。
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抗争与珠三角差别很大, 这仍然可以追溯到地方政商关系、劳动力来源与劳工社区生活形态中。从日常抵抗来看, 由于本地工人对工作、生活自主性的追求, 以及其独特的本地身份认同和广泛的关系网络, 内地中小城市工厂的日常抵抗比珠三角更为普遍。从集体抗争爆发的频次看, 两地都日趋频繁, 经济形势和制造业成本变化导致企业关停并转后的欠薪问题都比较突出, 但不同的是, 内地中小城市的地方政府扶持了较多本应淘汰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 以至于在日常生产经营中, 企业的欠薪和其他违法行为也较普遍, 劳动纠纷格外突出。从集体抗争的形成规模看, 珠三角高度集中的生产生活空间为大规模的劳工抗争政治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而内地分散的生产生活空间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劳动纠纷的广泛介入则基本限制了劳工集体抗争的可能规模。从劳工抗争诉求看, 两地工人的增长型利益诉求都在逐渐增多, 但珠三角部分行业存在实现工人利益诉求的条件, 而内地企业在艰难的代工竞争中只会选择强力压制这些诉求;即便是追求底线型的法定权益, 珠三角的工人倾向于在劳资纠纷中将薪资、经济补偿金、五险一金、超时加班等问题“新账老账一起算”, 以最大化地争取自身权益, 内地工人则可能要为追讨应得的工资而尝试各种办法。⑧从劳工集体抗争与社会的关系看, 频繁介入到珠三角劳工集体维权行动中的是各种劳工组织、高校师生、维权律师等;而内地中小城市的工人则多通过动员本土势力提高行动的威慑力。最后, 从制度影响来看, 珠三角层出不穷的劳工抗议行动和一些标志性事件正在不断影响政府的治理方式和工会的角色, 也推动了政府落实相关劳动标准;而在内地中小城市, 我们尚难见到各种劳工抗争行动产生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影响, 但这些行动确实在微观层面影响了企业的管理文化。
本研究只是对当前内地中小城市和珠三角地区的劳工政治进行比较, 但现阶段内地中小城市的劳工政治是否只是珠三角某个历史阶段的重复呢?内地的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 从时间段和经济运行环境来看, 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内地的劳工政治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珠三角的情况更有可比性, 从表面上看也颇有相似之处。比如, 关停并转裁和欠薪引发频繁的劳资纠纷;为保证经济和社会稳定, 地方政府降低劳动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然而, 当前内地地方政府的劳动治理方式与2008年的珠三角仍有很大差异, 似乎并没有研究证据显示, 珠三角各级政府会广泛动用各级行政资源帮助企业解决招工问题;或者以协调巨额贷款的方式深度介入到企业发展中。在金融危机时, 珠三角的地方政府与资本保持着更强的结盟关系, 但这种政商关系远不是包揽式的。社会环境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 2008年珠三角各级政府面临的是高度集中、数量庞大的外地劳工, 而当前内地中小城市面对的是布局分散、规模有限的本地劳工。
无论是珠三角还是内地, 工人的城市化进程都已不可阻挡, 其对劳工政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工人从“半无产化”到“无产化”的进程 (Pun&Lu, 2010) , 是否一定导致“阶级形成”或者“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基于田野经验和过往的研究文献, 本文对此持保留态度。从横向看, 不同区域的工业化路径差别太大, 地方政商关系、劳动治理方式、资本来源、产业构成、劳动力来源、劳工生产生活形态也不尽相同。从纵向看, 虽然工人的劳工权益意识和行动倾向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逐渐增长, 但地方政府的劳动治理方式也在不断改进。在高昂的制度成本、畸形的房地产经济和激烈的全球代工竞争中, 实体经济的发展走向更是难以预测。而当前劳工政治不断发展, 其重要前提就是总体经济和就业环境大体平稳, 工人仍有一定的市场谈判能力。因此, 劳工政治可能呈现出强烈的地区性、产业性和阶段性差异, “阶级形成”或“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可能只会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中。
研究者往往关注劳工政治在制度层面的可能影响, 然而底层劳工却往往更关心如何在当前的结构条件下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这些朴素的追求和选择在研究者宏大的制度愿景中可能并不重要, 因此在劳工政治的考察中也经常被忽略掉。在内地开发区, 工时的延长往往导致大批需要照顾家庭的工人离职, 劳动纪律的收紧引来厂外街头的报复, 糟糕的伙食激起野猫式罢工;但很多时候工人为了生计, 又不得不克服劳累、饥饿、寒冷, 在短暂的抗议后最终接受苛刻的计时产量或计件工资。底层工人类似的选择和行为有可能带来生产环境的一点改善, 但也可能不会对宏观、微观制度环境产生任何影响。类似的经历可能成为未来阶级经验的重要成分, 但也可能无助于甚至妨碍阶级团结。但这些行为和经历却是工人日常、普遍的状态, 贯穿于其中的可能是工人最珍视的价值与意义, 因此同样是劳工政治不可忽略的面向。保证基本生计、寻求法定权益、争取实现基本的人性需求 (比如家庭团聚、在生产中得到基本尊重等) , 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仍是最主要的行动诉求。
当然, 必须予以说明的是, 相比学界对珠三角地区劳工政治相对密集的研究, 对内地中小城市劳工政治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的结论还有待更多区域研究案例的补充和修正。根据笔者对方合市周边县市情况的掌握, 该开发区的经验在区域范围内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说, 内地中小城市普遍缺乏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产业配套基础, 因此在政商关系上有较强的相似性;并且从劳动力来源看, 内地中小城市的企业缺乏吸引外地工人的薪资待遇和发展空间, 只对希望兼顾家庭的本地工人有吸引力, 这两个方面应该是许多内地中小城市劳工政治形成的相似条件。但内地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地理范围,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分布、工业化历史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 与本研究中“外来资本本地工”的构成不同, 在华北保定等地的乡村工业中, 盛行的是“本地资本本地工”的组合形态, 其政商关系、企业生产管理制度、劳资关系等与本文考察的案例, 应该会有所不同。即便是在方合市域范围内,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外也存在其他层次的开发区, 各种层次的开发区在企业经济实力、政商关系、劳工队伍构成等方面也有所差异。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但学界对不同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劳资政关系、劳工经历与体验、劳工行动方式等似乎还缺乏应有了解。即便在最为发达的长三角经济区域, 相关研究也比较缺乏。劳工研究不应该在集体化转型或阶级形成的问题意识下找经验, 而应该扎根于本土丰富多样的工业化进程, 挖掘工人复杂而多样的经历和体验, 在多区域的深度研究中梳理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
引用文献和注释
蔡昉、王德文、曲玥, 2009, 《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 《经济研究》第9期。
蔡禾, 2010, 《从“底线型”利益到“增长型”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 《开放时代》第9期。
常凯, 2013, 《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费孝通, 2014, 《行行重行行——中国城乡及区域发展调查》, 北京:群言出版社。
耿曙、陈玮, 2015, 《政企关系、双向寻租与中国的外资奇迹》, 《社会学研究》第5期。
顾琳, 2009, 《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 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郭于华、黄斌欢, 2014,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新时期工人状况的社会学鸟瞰》, 《社会》第4期。
郭于华、沈原、潘毅、卢晖临, 2011, 《当代农民工的抗争与中国劳资关系转型》, 《二十一世纪》总第124期。
黄斌欢、徐美龄, 2015, 《工厂内迁与劳工的再嵌入——江西陶瓷厂的工厂政体研究》, 《学术研究》第6期。
黄岩、刘剑, 2016, 《激活“稻草人”:东莞裕元罢工中的工会转型》,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1期。
江飞涛、耿强、吕大国、李晓萍, 2012,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 《中国工业经济》第6期。
具海根, 2004,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梁光严、张静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林平、雍昕、舒玢玢, 2011, 《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孟泉, 2014, 《塑造基于“平衡逻辑”的“缓冲地带”——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劳资冲突模式分析》, 《东岳论丛》第5期。
裴宜理, 2001,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刘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任焰、潘毅, 2006a,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社会学研究》第4期。
——, 2006b, 《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 《开放时代》第3期。
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 2009, 《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经济研究》第7期。
万向东、刘林平、张永宏, 2006, 《工资福利、权益保障与外部环境——珠三角与长三角外来工的比较研究》, 《管理世界》第6期。
汪建华, 2014, 《新工人社区生活的社会政治意涵——基于经典理论视角的阐述》, 王春光主编《社会政策评论》 (总第5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5, 《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汪建华、孟泉, 2013,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 《开放时代》第1期。
汪建华、郑广怀、孟泉、沈原, 2015, 《在制度化与激进化之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 《二十一世纪》总第150期。
闻效仪, 2014, 《工会直选:广东实践的经验与教训》, 《开放时代》第5期。
张敏、顾朝林, 2002, 《农村城市化:“苏南模式”与“珠江模式”比较研究》, 《经济地理》第4期。
张永宏, 2009, 《争夺地带:从基层政府化解劳资纠纷看社会转型》, 《社会》第1期。
周黎安, 2007,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经济研究》第7期。
Blecher, Marc 2010,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Reform, and Labor Politics in China.”Global Labor Journal 1.
Chan, C.K.C.&Ngai Pun 2009,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198.
Chen, Feng&Y.Kang 2016, “Disorganized Popular Contention and Loc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n China:A Case Study in Guangdong.”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
Friedman, Eli David 2011, “Rupture and Representation:Migrant Workers, Unions and the State in China.”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2 (1) .
Lee, Ching Kwan 1998,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s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Modern China 24.
——2007, Against the Law: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Berkeley,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n, Ngai&H.Lu 2010, “Unfinished Proletarianization:Self, Anger and Class Action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 in Present-Day China.”Modern China 36.
Paik, Wooyeal 2014, “Local Village Workers, Foreign Factories and Village Politics in Coastal China:A Clientelist Approach.”The China Quarterly 220.
Seidman, Gay 1994, Manufacturing Militance:Workers’Movements in Brazil and South Africa1970-198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n, Y.S.&Hagen Koo 1992,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letarianization in Taiwan.”Critical Sociology 19.
Silver, Beverly J.2003, Forces of Labor:Workers’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huang, Wenjia&F.Chen 2015, “‘Mediate First’:The Revival of Mediation in Labour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222.
注释
① 检索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 中文文献限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和南大CSSCI来源期刊,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 关键词包括“工人”、“劳工”、“农民工”、“集体抗争”、“集体行动”、“维权”;英文文献通过百度学术检索, 关键词包括“China”、“worker”、“migrant worker”、“labor”、“unres”t、“strike”、“collective action”、“protes”t、“movement”, 通过关键词检索到相关文献后, 进一步借助“相似文献”、“参考文献”、“引证文献”搜寻相关文献。
② 裴宜理 (2001) 在《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中, 将工人与产业资本家的关系、与政党的关系、工人中的帮派行会组织及其他非正式关系、工人的抵抗行动, 都纳入到“工人政治”的范畴中。受裴宜理的启发, 本研究将劳资政三方关系、工人生活周围的社会力量和内部的关系网络、各种各样的抵抗行动都纳入到“劳工政治”的范畴中。
③ 根据学术惯例, 本文经验材料中涉及到的所有地区、企业和人物名称都经过处理。
④ 该市2014年土地征迁补偿标准约为24000元/亩 (不包括青苗、附着物等补偿费用) 。
⑤ 许多小企业都集中在“孵化基地”里面, 企业只要租下里面的房间, 搬来产线, 即可开始生产。一些地方官员称企业完全可以“拎包入住”。
⑥ 早期引进的企业往往自己建厂房和宿舍。那时正值房地产热, 一些老板会在投资工业的同时要求政府额外给他们一块商业用地。但土地有限, 且房地产市场变化很快, 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 以建设“孵化基地”和公租房的方式, 吸引更多小企业入驻。
⑦ 当然, 政府对企业许诺的各种优惠政策未必都能兑现, 甚至存在“开门招商, 关门打狗”的现象 (耿曙、陈玮, 2015) 。在田野调查中, 也有一些企业领导反映, 虽然地方政府积极为企业发展提供各种优惠政策, 但在执行过程中, 却因部门或官员个人利益而大打折扣, 这表现在: (1) 企业融资难, 虽然有提供贷款的项目资金, 但银行却附加其他条件, 比如要求企业为其消化部分呆账坏账; (2) 虽然地方政府对许多收费项目进行减免, 但由于收费部门太多, 且有一些属于重复收费, 企业负担还是较重; (3) 一些官员怕担责任, 在企业办理相关手续时不敢签字, “脸好看事难办” (访谈编号:clcp2315) 。另外, 本地企业与从外地引进的企业待遇差别也很大, 很难像后者那样得到土地、税收等优惠 (访谈编号:clcp2320) 。
⑧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珠三角地区工人的经验和法律意识比内地工人更强 (尽管近年来内地工人的经验和意识也在上升) , 他们更了解与经济补偿金、五险一金、加班相关的法律规定;二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 (尤其是许多外资企业) 总体经济实力更强, 更可能支付工资之外的赔偿和历史欠账, 而内地工人则非常清楚, 他们的企业能发出工资就不错, 大多数时候即便费尽周折也只能讨得部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