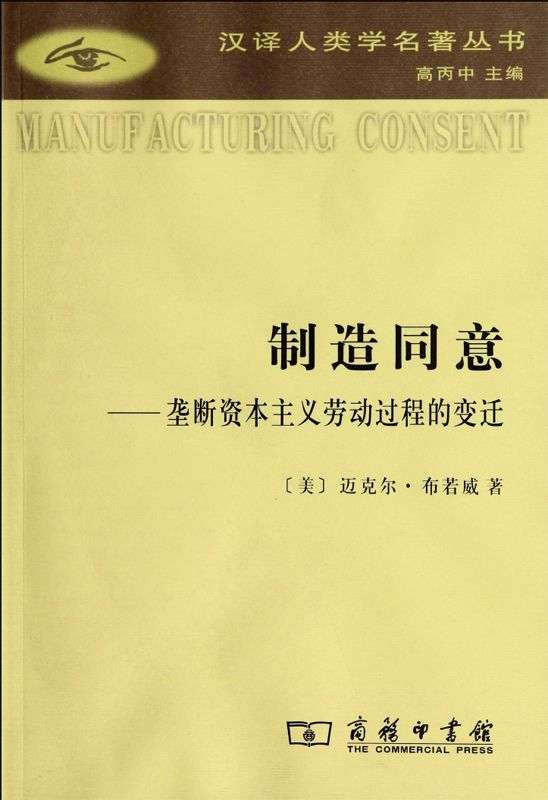转载 | 劳动世界的性别化:华南经济奇迹中的女工、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政治 - 李静君
本号不拥有转载文章的任何权利,文章不代表本号观点
若侵犯了您的资产阶级法权,请通知号主删文跑路~
劳动世界的性别化:华南经济奇迹中的女工、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政治
李静君 香港中文大学
我进行了一项比较民族志研究,探讨了华南制造业地区两家工厂中的两种性别化生产体制。这两家工厂由同一家企业所有,由同一管理团队管理,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使用相同的技术劳动过程,但它们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车间政治模式,分别称为“地方性专制”和“家族霸权”。为了解释这些模式,我认为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产生了工人依赖的多样化条件。这些不同的依赖关系决定了管理层的控制策略、工人的集体实践以及他们对工人性别的共同建构。本案例研究引发了对生产政治理论以及全球工厂中女工的女性主义文献的批判与重构。
在华南,经济奇迹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女工的控制?我观察到两种生产体制,它们在如何建构性别以及这些建构如何促进阶级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为什么在同一家企业所有、由同一管理团队管理、生产相同电子产品并出口到相同海外市场、使用相同技术的两家工厂中,会分别出现“地方性专制”(深圳)和“家族霸权”(香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
“地方性专制”描述了管理层通过对移民工人的强制纪律体制进行控制,利用工人的地方性网络,并将女性建构为顺从的“少女工人”。而“家族霸权”体制则以霸权而非专制的方式进行控制。在家族霸权下,管理层通过车间的家族主义话语、促进女性履行家庭责任的工厂政策,以及将女性建构为经验丰富且强势的“主妇工人”来建立控制。通过对这两个案例的系统比较,我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差异导致了工人依赖条件的不同。在深圳,单身移民工人依赖地方性网络来获得工作、贷款和紧急支持,而在香港,已婚女性参与有偿工作则取决于她们的家庭条件。针对这些差异,管理层采用了不同的劳动力整合方式,而女工则采取了不同的抵抗模式,从而形成了两种性别化的生产体制。
通过解决这一经验难题,我提出了两个理论主张。首先,我认为女性主义对性别的分析需要发展特定领域的理论,以解释性别如何在不同的权力关系中被社会建构。重构的生产政治理论有助于理论化工业场所中的性别问题。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必须认识到性别是管理控制的一个维度。为了解释性别为何以及如何重要,生产政治理论需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构:(1)重新审视管理层的控制逻辑;(2)将劳动力市场与工人的依赖条件联系起来;(3)认真对待工人的性别主体性。
性别与生产政治
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见解是,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并且是权力关系的一个构成维度(Scott 1988: 42)。随着特定领域研究的出现,展示了性别在学校(Holland 和 Eisenhart 1990)、家庭(Hochschild 1989)、公司(Kanter 1977)和服务业工作场所(Hochschild 1983; Williams 1989)中的作用,理论挑战在于发展特定领域的性别理论。在工业生产领域,关于全球女工的文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女性在正式(Chapkis 和 Enloe 1983; Nash 和 Fernandez-Kelly 1983)和非正式(Beneria 和 Roldan 1987; Mies 1986; Ward 1990)就业部门中的生产性和再生产性劳动的信息,涵盖了国际资本转移的起源地(Lamphere, Zavella, 和 Gonzales 1993; Rosen 1987)和目的地(Ong 1992)。一个持续的争论集中在女性参与全球市场生产的后果上。一些学者(Lim 1981, 1983; Salaff 1981)认为,工业就业使女性从边缘化和地方父权控制中解放出来,而另一些学者(Ward 1988; Elson 和 Pearson 1981)则认为,国际资本重新组合并加强了女性在地方社会中的多重从属地位。尽管存在分歧,这些研究都遵循了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包括国家、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以及地方社会制度中早于跨国公司到来的父权和种族等级制度。研究表明,在台湾(Hsiung 1991)、新加坡(Lim 1978)、印度尼西亚(Wolf 1992)、马来西亚(Ong 1987)、墨西哥(Fernandez-Kelly 1983)、希腊(Hadjicostandi 1990)和爱尔兰(Pyle 1990),国家的发展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利用女性的廉价和顺从劳动力,通常与父权家庭合谋。少数族裔女性还受到基于种族的额外支配(Hossfeld 1990)。女工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斗争,从默许和适应到日常抵抗和有组织的抗议(Ong 1992)。
尽管启发式框架可能打开了支配和抵抗模式的多样性,但经验上的差异需要能够解释共性和差异的理论。现有关于性别和工业工作的文献缺乏严格的比较分析(Ragin 1987),这是其致命弱点。没有能够生成理论的方法论严谨性,学者们对诸如在加利福尼亚硅谷,管理层利用女工之间的种族分歧来实现控制(Hossfeld 1990),而在阿尔伯克基,种族在理解工作场所的控制和抵抗中并不重要(Lamphere 等 1993)这样的发现感到困惑。为什么在阿尔伯克基的区域经济中,搬迁的工厂在是否对同一批女工采用等级制或参与式控制模式上存在差异(Lamphere 等 1993)?
Burawoy(1979, 1985)的生产政治理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为理论化国际资本主义对女工的多样化控制模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起点。Burawoy 没有像 Braverman(1974)和 Edwards(1979)那样将生产中的两个政治时刻混为一谈,而是在理论上区分了“劳动过程”——生产中的技术和社会任务组织,和“生产的政治装置”——调节和塑造工作场所政治的机构。“工厂体制”的概念指的是生产的总体政治形式,包括劳动过程的政治效应和生产的政治装置(Burawoy 1985:87)。有两种基本类型的体制:专制和霸权。专制生产体制建立在工人依赖工资就业维持生计的基础上,工资与工作场所的表现挂钩。国家干预,如提供福利和规范劳资关系,消除了强制的基础,催生了以同意而非强制为主导的霸权工厂体制(Burawoy 1985:125-26)。
我在华南(香港和深圳)一家电子企业的两家工厂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了 Burawoy 理论的三个经验异常,并据此重构了理论。第一个异常是,尽管香港工人缺乏独立于工资劳动的生计基础,并且几乎没有国家保险或福利的保障——Burawoy 认为这些条件应促成专制体制——但香港工厂却出现了霸权体制。另一方面,在深圳工厂,尽管移民工人有可能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计,独立于工资劳动,但却出现了专制体制,这再次与 Burawoy 的假设相悖。我认为,Burawoy 错误地假设管理层在有能力实施专制时总是倾向于使用强制手段。尽管在香港和深圳,管理层都相对不受国家干预和法规的约束,但他们可能并不倾向于使用专制手段,因为这是一种成本更高的控制方式。在香港,管理层认为没有必要使用专制手段,因为制造业工作正在减少,女工们迫切希望保住工厂工作。在深圳,专制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允许,并且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专制也是必要的,因为工人尚未获得工业工作的纪律。
Burawoy 还忽视了劳动力市场的组织作为工人依赖的关键决定因素。我发现,工人并不依赖国家或企业,而是依赖劳动力市场中的机构来维持生计并参与有偿劳动。在深圳,来自同一农村村庄或县城的网络将移民女工从农田引入工厂。工人依赖这些地方性关系生存,而管理层则利用这些关系来控制劳动力。因此,我描述了深圳工厂中的地方主义政治。在香港,工人依赖他们的家庭和亲属,管理层有意识地促进女性履行家庭责任。因此,家族主义在香港工厂中占主导地位。
第三个异常是,Burawoy 的生产政治理论完全忽视了日常车间关系中控制和抵抗的性别维度。在这两家工厂中,女工的性别被管理层和工人多样化地建构,通过这些建构,车间权力关系被构想、合法化、自然化和批评。“少女工人”和“主妇工人”是关于女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它们源于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条件。由于工作的性别隔离,我无法在同一工作中比较女性和男性。我仅关注女工及其男性管理者的对待方式。我通过展示这些行动者如何利用性别差异来组织和解释社会生活,确立了性别的分析作用。
地方性专制
深圳工厂的控制是公开的、可见的、惩罚导向的,并且公开展示。工厂四周被高墙围住,主入口由携带警棍的保安全天候把守。生产线旁的公告板上列出了每日和每小时的产出目标,每周评估的“最佳”和“最差”工人名单,以及每条生产线的每日清洁评分。墙上用醒目的中文写着“禁止吐痰”、“有问题问上级”和“质量第一”等标语。这些规则的可见展示只是专制体制的冰山一角。新员工被要求阅读一本长达10页的详细规章制度手册。环境与卡尔·马克思时代的典型工厂惊人地相似,当时“所有惩罚自然都归结为罚款和扣工资”(Burawoy 1985:88)。Liton 的《工厂规章》手册充满了专制的规定和惩罚,禁止工人的行为和着装:
工人必须在制服上佩戴工厂身份证。违反者罚款5元。穿拖鞋上班、吐痰或乱扔垃圾的工人罚款10元。……代打卡的工人罚款三天工资。不按规定排队打卡、不按规定换鞋、不戴头巾、指甲过长或卷起制服袖子的工人罚款1元。工人上厕所必须申请“请假卡”。每次违规罚款1元。拒绝加班的工人第一次罚款2元,第二次4元,第三次8元,第四次扣除全部工资。……未经事先许可的缺勤第一天罚款30元,第二天15元。事先许可的缺勤罚款15元。……
在工厂的纪律体制中,三个方面对女工造成了最大的痛苦:身体控制、时间控制和扣工资。工人的身体活动被限制在他们工作的楼层和生产线上。办公室是整个工厂中最神圣的区域。办公室与车间截然不同,工人通常不允许进入。在空调办公室里打电话是高级线长及以上人员的特权。食堂和宿舍分为A、B、C三个等级,为不同级别的员工提供不同质量和数量的食物。宿舍的区别在于是否有电风扇以及每个房间的床位数。工厂财产的严格分区与工人以前在乡村自由活动的自由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新员工经常强烈且公开地抵制管理层的调动指令。从一条生产线的一个座位调到另一个座位,或被“像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对工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是对他们个人尊严的侵犯。通常,只有在主管或经理亲自出现在车间时,工人才会服从。
与对工人身体活动的控制密切相关的是工厂生活的时间纪律,它既严格又充满不确定性。固定的工作时间由车间铃声和打卡机控制。工作从早上7:30开始,持续到下午4:30,每周六天,中午有45分钟的午餐时间。加班由管理层决定,通常只提前一小时通知,使工人无法计划非工作时间。在正常情况下,每天需要加班两小时。在旺季,通常是夏季为圣诞节库存下订单时,工作日加班五小时和周日全天加班往往是强制性的。这种对时间的控制被体验为专制,但工作日的长度和车间的高温并不被工人视为专制。正如一位女工解释的那样:
“实际上在家更累,烈日当头。在这里至少我们头上有个遮阳的地方。但尽管田间劳动非常忙碌和辛苦,我们有很多自由时间。工作完成后,你可以和村里的朋友一起玩。在这里你必须憋尿,直到他们给你上厕所的许可。”
在 Liton 的所有规定中,最令人厌恶的是对所有类型的请假都扣工资,即使工人有事先许可或医生的病假通知。管理层坚持这一惩罚性规定,以尽量减少缺勤,并减少工人去其他工厂面试的机会。在工人眼中,这不是不平等的奖励制度,而是“老板工厂”(工人用来区分外资企业和更“仁慈”但利润较低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术语)中最“不公平”和“不人道”的做法。一位女工抱怨道:
“村里也有不平等。一些农民家庭有更大的房子和更多的土地,一些人在副业和生产中赚得更多。我们出来工作的人知道经理比我们工人挣得多。但当你真的生病时,主管却不相信你,这真的很不公平。即使我们中有些人在工作中几乎晕倒,他们也把我们当作骗子对待。”
工人因专制纪律而遭受痛苦的客观迹象包括体重减轻、“面色”恶化和皮肤问题,这些都是中医中健康状况恶化的指标:
“你看我的脸色变得多糟糕。我失去了食欲。他们固定了我们吃饭的时间,即使你不饿。当你饿的时候,他们不允许你吃。在家时,我想吃就吃,一次吃一点。我可以吃三大碗米饭。现在,我只感到胃痛。深圳的水质不好。我们中许多人因为水质问题皮肤上起了疹子。”
然而,专制规则的执行因工人之间普遍存在的地方性关系而有所缓和。工人之间更多地通过他们的省份或县籍以及介绍他们来的人来识别彼此,而不是通过名字(许多名字是假的)。当我第一次出现在车间时,工人问的第一件事是“谁介绍你来的?”有传言说我是老板的妹妹,这一身份我在前两个月的田野调查中试图反驳但未能成功。根据工人的家乡村庄、县或省份组织的地方性网络,并包含不同级别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在车间中很容易辨认。在装配线上,可以听到不同的方言,标志着地方性社区的排他性和边界。地方性关系还延伸到各种小恩小惠:当拿到“请假卡”去取水时带上同乡的杯子,发出信号提醒其他人管理人员的接近,互相教授工作技能,或者帮助同乡清理堆积的工作,如果他们碰巧坐得近的话。每当有机会在车间走动时,像拉同乡的辫子、突然在背后打一拳或丢一张小纸条这样的小动作被用来开玩笑和打招呼。
线长、领班和主管的裙带关系比比皆是,并对工人的物质利益产生了深刻影响。香港管理人员了解并容忍其初级员工的这些做法。从洗手间访问的时长、分配难易任务、申请探亲假,到技能传授、晋升机会和引进同乡的能力,优先权都给了同乡。同乡的成员资格标准取决于利益所在。最基本的区分将所有工人分为两组:“北方人”,来自长江以北的省份;和“南方人”,来自长江以南的省份。每组都以贬义词构建“他者”:“北方人”是乡巴佬,愚蠢、粗鲁、吝啬;“南方人”狡猾、放荡、不诚实、挥霍无度。更多时候,工人通过县籍对自己进行更细致的区分。小恩小惠大多沿县籍线分配,而像晋升或引进同乡这样的稀缺资源则仅限于同一村庄或亲属群体的同乡。工厂的组织结构图带有地方主义的印记。在两名香港经理之下有四名楼层主管,他们都是来自广东省龙川县的客家人。其中三人姓叶,第四人姓吕。这两个姓氏群体是来自邻近村庄的表亲。在这四名主管之下的九名生产领班中,四名也是客家同乡。90%的线长和维修工是南方人。清洁工和杂工是来自北方省份的老年男女。地方主义是如此根深蒂固的习语,以至于工人用它来解释工厂的日常生活。裙带关系的故事被传播、相信,并被写入投递到“意见箱”的投诉信中。
“少女工人”
管理层利用嵌入地方性网络中的性别等级制度,对大多数年轻单身女性施加额外控制。“少女工人”的概念强调了年轻女性的单身状态、不成熟、即将结婚、因此对深圳工厂工作的短期承诺、低职业抱负和低学习技能的动机。将女性社会建构为“少女工人”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而是嵌入在实践中的。它促进了亲属对女性在工厂内纪律的控制,并合法化了管理层将女性降级到低级别的非技术性工作岗位。
由于主管和领班通常是男性,管理层可以利用来自同一地区的男性主管或领班对女性亲属的家庭或地方性权威来控制女性的行为,并确保她们对 Liton 的承诺。一位女工曾安排发一封电报给自己,以便有借口申请探亲假。她的哥哥是 Liton 的技术员,负责筛选请假申请的香港经理向她哥哥核实了电报内容。她哥哥对电报一无所知,并被告知告诉他的妹妹她的申请被拒绝了。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在 Liton 工作的女性试图辞职去一家工资更高的工厂工作,但她的努力被她叔叔否决了,她叔叔的妻子和她住在同一间宿舍:
“在宿舍里,我姑姑、表亲和我住在同一个房间。我姑姑的床就在我的下面。每次我出去,她都会问我去哪里,和谁一起去。我的一些朋友离开 Liton 去了隔壁的工厂。我叔叔和姑姑不允许我去。他们担心我可能会远离他们学坏。他们写信给我的父母,父母回信坚持我不应该离开 Liton。”
由于管理层认为“少女工人”工作只是为了攒够嫁妆,她们更热衷于为婚姻做准备而不是在工厂工作中追求职业生涯,因此管理层只培养男性新员工获得公司特定的技术技能。从维修工到技术员、助理领班和主管的晋升轨道对女工是封闭的。这常常导致线长(大多是女性)和男性维修工之间的冲突,维修工在装配线上正式隶属于线长。由于接受了少量的电子培训,并有晋升的前景,维修工对女性的技术无知表示蔑视。当女性线长抱怨维修工反应迟钝时,争吵总是爆发,男性维修工愤怒地挑战女性自己尝试修理生产线。
要理解为什么年轻女性接受“少女工人”的概念并与地方性专制控制达成妥协,必须理解她们的多层次主体性。许多年轻女性逃离家乡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许多人也有个人目标,如获得经验、为嫁妆攒钱或资助自己的教育。由于她们打算在某个时候结婚,工厂工作比其他服务性工作更受欢迎,因为工厂工作与吃苦耐劳和纪律严明的劳动相关联,这些特质被认为是未来妻子的理想品质。因此,进入工厂意味着在赚取现金收入的同时保持少女的适当女性气质,并享受探索恋爱关系的自由。
实际上,女性对她们少女身份的理解与管理层和她们的男性同乡不同。首先,她们的少女身份使约会成为一个合法的关注焦点。通过深圳的地方性网络,女性结识了其他工厂或行业的男性同乡,如果她们没有来深圳,她们就不会认识这些人。尽管跨省约会,尤其是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的约会,被污名化为“胡闹”,但在“少女工人”中有一个共识,即在深圳工作给了她们更多的择偶自由和更多资源来改善她们找到理想丈夫的前景。
年轻女性赋予她们少女身份的第二个意义是,她们应该为工厂工作之外的未来做准备。与管理层假设的顺从态度不同,年轻女性将未来的婚姻视为情感和财务责任的开始。她们对婚姻的愿景不是家庭主妇,而是寻找比老板工厂更重要和有意义的工作的伙伴关系。因此,在淡季加班较少时,一些女性参加了英语、打字和计算机的晚间或周末课程。其他人则有创业抱负,如开一家小餐馆或一家卖零食或杂货的小店。在北方省份,这些创业的初始资本大约为5000到7000元,这是那些有意识攒几年工资的女工能力范围内的金额。
总之,在“地方性专制”体制下,强制统治通过地方性网络和对女性作为少女工人的建构得以实施。虽然管理层利用地方主义作为一种统治模式,但工人也积极利用地方主义来缓和管理层的专制。将女性社会建构为少女工人是工厂体制的性别维度,尽管各方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和目的。
家族霸权
香港工厂的霸权劳动控制是隐蔽且不显眼的。通过下属的内化纪律实现,下属在服从过程中体验到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合法性,霸权统治总是以强者的让步为条件,因此始终是一个开放且有争议的过程(Thompson 1978; Williams 1977)。Liton 香港工厂的工厂生活以缺乏成文规则而显著。工人之间存在着有序的自主性,他们在车间的着装和行为反映了比深圳更自由的生产体制。大多数女性穿着自己的衣服,没有头巾或肩带区分等级。每天早上8点,女工们开始进入空调明亮的生产车间,打卡并与总是微笑的保安打招呼。工作日从早餐仪式开始,这是工人们自发的创造,而不是像深圳那样由管理层强加的食堂例行公事。工人们轮流为彼此带早餐。食物——通常是炒面、粥或新鲜烤制的面包——是从他们的社区购买的。其他人则带来报纸,附近的工人会每人拿一页阅读或进行简短的交谈,直到8:15的铃声响起。在工作时间,女性可以接打电话。她们也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上厕所。然而,当工作流程紧张时,她们会评论说她们需要上厕所但没有时间。由于女性的育儿责任,迟到并不罕见,车间经理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于工人在公司的长期任职,平均10到15年,女性通常知道同事的孩子生病或家中其他紧急情况导致她无法准时上班。线长和工人会为迟到或缺勤的工人顶班。传递和吃零食,尽管正式禁止,但却是日常行为,领班、线长甚至生产经理都知道、看到并容忍。然而,工人们偷偷摸摸地吃,仿佛在公开声明她们知道吃巧克力是被禁止的。领班和经理会主动将意外暴露在生产线上的零食袋藏起来。在这些行为中,管理层容忍或仁慈的底线是生产不受影响。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这种默契理解形成了一种自我监管的自主性,这对双方都有利。
日常生产程序也以负责任的自主性为标志。经验丰富的线长基于对她们手下经验丰富的“线女孩”工作习惯的深入了解,被允许交换工人的任务,通常无视工程部门下达的设计。两个条件使得这种自主性成为必要。近年来,产品型号的变化更加频繁,工人年龄增长,导致工作速度变慢,视力下降。为了跟上每日生产目标,线长发现有必要将动作较慢的工人的装配任务与她的上下游邻居交换。线长自己也参与帮助动作较慢的工人完成更复杂的工作程序。经理和领班很少质疑线长在做出这些改变时的主动性。其中一位自豪地向我建议:“有时当我们给她们错误的材料或在设计工作程序时出错,是她们向我们指出的。她们就是那么有经验!”
霸权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车间话语的盛行。Roy(1958)指出,日常的身体和对话互动使工人能够忍受“单调的野兽”。为了让漫长的一天过去并打破工作日,工人们发展出标准化的互动——香蕉时间、窗户时间、鱼时间和可乐时间——以及对话主题——开玩笑的主题、悲惨故事、教授主题和闲聊主题。群体互动是“消费性”而非“工具性”交流的一个例子,它使工作变得可以忍受。在 Liton,女性也参与了车间话语,我认为,这些话语是群体过程,通过这些过程,性别和阶级关系被社会建构和集体理解。抓住车间中的这些话语空间,女工们重申了彼此的家庭承诺和身份。这些下属的文化强调是霸权体制中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们使主导权力能够控制和表达自己的利益(Gramsci 1971; Williams 1977; O’Harlon 1988)。
关于女性家庭生活的反复主题主导了车间对话,这些对话以闲聊、八卦、嬉闹和严肃讨论的形式出现。“孩子主题”是每日的主要内容,围绕孩子的学校表现和健康状况展开。那些有成年孩子的人要么夸耀孩子的孝顺,要么哀叹他们新发现的独立于父母的自由。在“与男人的关系”主题上,女性交换了与丈夫相处的策略,并向少数单身女工提供了约会的建议。有时,欢快的笑声会演变成关于离婚、单亲母亲和婚外情的悲惨故事。午餐时间,谈论食谱和最佳购物是主要内容。性生活是另一个反复出现的话题,女性们对此出奇地坦率。她们拿自己的性生活开玩笑,主要是关于在公共屋邨里过性生活的不便,那里整个家庭住在一个150平方英尺的单间里。当领班在这些生动的玩笑中走过时,女性们会抓住机会让他尴尬。回应领班的工作指示,线长会对他说“我喜欢的时候再做”,这在粤语中是“我喜欢的时候再做爱”的双关语。领班会在工人的喧闹笑声中悄悄走开,仿佛他是个冒犯者。
除了这些集中的主题外,还有一种家庭昵称的做法,这在深圳工厂中没有发现,它有助于人性化领班、线长和女工之间的等级权威。例如,四位四十多岁的线长被四十多岁或五十多岁的“线女孩”称为“妈妈”。几乎每个人都有昵称,暗示他们的家庭情况(例如,“富太太”是一位以拥有富裕丈夫而闻名的女性,她在车间化妆)。“胖婆婆”是一个有三个未婚女儿的胖女人的名字。“婆婆”,意思是奶奶,指的是一个周末照顾孙子的老年妇女。一位领班把家人留在了他的家乡海南岛,因此他被昵称为“海南岛”。生产经理被工人和线长称为“爷爷”。“姐姐”前缀几乎加在每个人的名字前。因为这些亲属称谓允许参与者模拟家庭关系,所以关于工作表现失败的责备对管理层来说更容易传达,对工人来说也更容易接受。
家族主义文化(Lee 1993)也存在于实践层面。尽管上述话语是女性自己的文化产物,并非由管理层设计,但管理层有意识地通过公司政策适应女性的家庭身份。家族主义实践的一个例子是管理层允许一到两个小时的紧急假期而不扣工资。这与深圳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在深圳,即使有医生的病假通知,也会扣除近三天的工资。在香港工厂,生产经理会询问请假原因,然后在工人的打卡上签字,以便人事部门知道这不是“迟到”或“请假”的情况。管理层认为家庭原因是紧急假期的正当理由。如果孩子或年迈的岳父母生病,或孩子的学校老师要求开会,女性可以请假而不受惩罚。女性认为这种灵活性是在 Liton 工作的主要优势,她们小心地自我监管,不滥用管理层的宽容。因此,当一位女性在结婚后几乎每个星期五都请病假时,其他工人中出现了批评。线长甚至向经理建议,不应再批准该女性的假期,因为她显然在利用公司。
“主妇工人”
“师奶”,一个粤语俗语,指工人阶级家庭中强势的主妇和母亲,经常被管理层和工人用来解释女工的行为和关注点。对管理层来说,“师奶”意味着女工认为工作和工资次于家庭责任。女性还关心在外工作的道德影响,并希望确保自己的女性气质和家庭的道德声誉不会受到不利影响。Liton 的五天工作周政策和紧急假期的宽松规定就是基于这种理解设计的。重要的是促进女性履行家庭责任,而不是提高工资或创造晋升前景。管理层对香港工厂女工的集体描绘如下:
“她们(女性)工作是为了给自己买花。如果她们在乎赚更多的钱,她们早就离开了。在这里,工作时间稳定,工作不太累。她们的丈夫喜欢这是一家工厂,这样没有人指责她们的妻子在公共场合露面。Liton 是师奶的理想选择。她们可以两全其美:照顾孩子,同时避免呆在家里的无聊。”
对领班来说,允许女性在车间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意味着更好地利用女性的经验来提高生产。尽管领班和男性维修工被排除在女性的话语社区之外,并经常受到女性的玩笑和戏弄,但男性并不在意这些收入和组织等级上都低于他们的师奶。根据女性的强势行为是一种取悦她们并使工作场所愉快的方式,而不是顺从或恐惧的表现。
然而,女性对“师奶”身份的认同包含了她们对自己在组织中从属于男性的理解,以及她们抵抗管理层控制的可能性。一方面,女性通过承认男性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来合法化男性的地位。“他们是家庭的男人。我们挣的那点钱怎么能养家呢?”另一方面,她们看穿了官方头衔的表象,承认如果她们愿意,她们也可以获得电子技术,使她们成为女领班。然而,家庭责任使她们无法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此类培训。因此,女性并不犹豫对领班或维修工表示蔑视。“臭男人什么都不懂!”是她们对那些经常与她们的“妈妈”——线长相比的男人的评论,线长负责所有日常生产程序,从安排生产线到获取材料供应。制造业是香港的夕阳产业,这也使女性更加重视她们对家庭和孩子的承诺,而不是领班在夕阳职业中的职业生涯。因此,女性以怜悯而非羡慕的眼光看待她们的男性上司。最后,女工们意识到,家庭责任为她们规避管理层的要求提供了借口。Liton 在深圳开始生产后,线长们义正言辞地拒绝了管理层指派她们定期访问深圳工厂的任务。因为这些任务涉及跨境通勤和在深圳过夜,这些女性以性别不便和家庭育儿负担为由拒绝了这一额外工作负担。在外过夜和离开孩子违反了师奶的家庭女性气质,以至于管理层不愿过于强硬。
总之,两家工厂有许多相似之处:性别化的组织等级、劳动力的地方性多样性、技术、产品范围和所有权。然而,不同的生产体制出现了。使用扩展案例方法(Burawoy 1992),以下分析比较了塑造这些日常政治多样化模式的宏观制度力量。
国家与管理自主性
Burawoy(1985)的生产政治理论将国家干预和监管作为区分两种基本工厂体制的关键。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国家的作用并不能解释所有体制差异,因为深圳和香港并不处于国家干预产生理论预期结果的国家。具体来说,深圳的庇护主义国家和香港的最小国家都没有限制管理层在劳动控制实践中的自主性。此外,这两个国家都没有为工人提供福利或社会保险。在这种高度管理自主性的条件下,不同控制策略的部署更多是对各自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和工人特征的回应,而不是国家施加的约束。
庇护主义关系,或称“关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Walder 1986; Oi 1989)。深圳的开放工业化有几个特点特别有利于庇护主义的扩散。国家权力的下放,加上地方之间为吸引外国投资者而提供优惠条件的竞争,使劳动法规更加灵活和可协商。大多数香港投资者在特区外设立加工厂,以规避特区内的更多监管官僚机构。香港投资者与中国大陆之间预先存在的亲属和籍贯关系赋予了香港投资者一种外国投资者无法比拟的象征资本(Smart 和 Smart 1991; Leung 1993)。这些关系也成为庇护主义的滋生地:礼物和个人恩惠的交换使双方受益。
Liton 的管理层反复强调,决定他们在深圳工厂生产管理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他们与负责税收、进出口关税和劳动管理的三个地方国家部门的关系。由于国家官员有权提高利润税率、在海关检查站造成延误或执行禁止外省工人的规定,Liton 的管理层格外小心地维护与这些地方官员的庇护主义关系。通过庇护主义关系最大化企业自主性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更直接的方式是参与礼物经济。在传统中国节日期间送礼(从昂贵的干邑白兰地和干海鲜到进口香烟和日历)、举办晚宴和卡拉OK派对、家访、以制造商价格向官员出售 Liton 的高保真产品,以及捐赠给当地学校和道路建设项目是一些主要的礼物。偶尔,优先考虑介绍朋友或亲戚子女到 Liton 工作的官员。这些礼物防止了地方国家部门的问题。在第二种庇护主义使用中,管理层利用与一个部门的庇护主义关系来抵制另一个部门的不必要干预。例如,由于 Liton 与外贸局的密切关系,Liton 的管理层可以抵制劳动管理局提高工资率和改革惩罚性工厂法规的压力。因此,庇护主义增强了深圳的管理自主性,那里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加工厂工人的最低工资,也没有社会保险立法或强制工会承认或集体谈判来保护工人免受任意解雇。
香港的管理自主性得益于最小的国家监管和提供的社会保险。在他们对香港劳资关系的开创性研究中,England 和 Rear(1981)发现,在1967年之前,“工作场所外部几乎没有规则,无论是法律还是集体谈判,这使得一个宽容的系统有利于那些在工作场所内部掌握权力的人——雇主”(第361页)。对于产业工人来说,没有最低工资,没有每日工作时间的限制,也没有法定产假或遣散费。1967年骚乱和大规模停工后,英国殖民政府引入了劳资关系和社会福利的立法干预。《雇佣条例》规范了雇佣合同的终止、工资期、扣工资、休息日和遣散费。其他法律将女工的加班时间限制为每天两小时。1970年代还建立了解决纠纷的申诉机制。最后,在福利方面,尽管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开发了世界上第二大的公共住房系统,但政府对自由放任的不干预主义的支持仍然坚定,仍然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系统。因此,即使在1967年后的改革之后,香港的劳资关系今天仍然“严重不发达”,尤其是因为缺乏集体谈判和工会的软弱。香港的工会法为工会提供了“负面措辞的豁免权,免于共谋侵权和其他法律障碍”,但并未“授予任何积极的工会承认权”(Lethbridge 和 Ng 1984:83)。此外,由于工会从未在工作场所高度组织化,没有发达的车间代表系统,集体谈判在劳资纠纷解决中很少见(Levin 和 Chiu 1993:203)。因此,England 和 Rear(1981)认为,自1967年以来,英国自愿调解模式在香港的应用对工作场所关系的现实几乎没有影响,原因是缺乏工会从车间对管理层施加的压力。
总之,在深圳和香港,管理层在企业内部享有高度的生产组织和劳动控制方法的自主性。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国家对管理层的约束较弱,并为工人提供了最少的生活资源,国家的作用并不像 Burawoy 所说的那样关键。相反,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决定了工人的依赖,并对管理层和工人施加了约束。
劳动力市场与工人的依赖条件
我将劳动力市场的组织与工人的依赖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车间利益。在深圳的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经验的移民女工依赖地方性网络获得工作和生存。管理层利用这种依赖来合法化和促进专制控制,这是从新生工人阶级中获取纪律所必需的。另一方面,在香港,女工参与有偿工作取决于家庭责任的履行。女性还依赖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子女。管理层顺应女性的家庭限制,以换取负责任的自主性和自我监管的控制,这是由女性的长期公司任职、公司特定经验以及她们在萎缩的制造业中保住工作的渴望所促成的。
Liton 深圳工厂的工人来自中国14个不同的省份。来自广东的工人仅占总劳动力的47.7%,其次是湖北(21.8%)、四川(8.7%)和河南(6.1%)。其余来自广西、湖南、江西,甚至远至新疆。80%的劳动力是女性,年龄在16至25岁之间。这些工人是1970年代末农村经济改革后出现的“流动人口”或“移民劳动力潮”的一部分,释放了1.14亿至1.52亿(或中国农村劳动力的30%至40%)的剩余劳动力(Taylor 1988)。截至1990年初,全国约有8000万“流动人口”,其中500万在广东(Solinger 1991:10)。管理层在移民劳动力的大量人数、他们的年轻、农民出身和缺乏工业工作经验中看到了专制主义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尽管一位经理将女性比作绵羊,因为两者都温顺且无知,但另一位经理谈到了培养意识和纪律的必要性:
“在香港,你不会看到工人随地吐痰。但在这里,这是他们的习惯,即使你站在他们旁边。这是他们在农村的行为方式。……我曾经看到一个新工人在下雨时放下工作冲回宿舍。她去收挂在外面的衣服。……我们这里提供的条件对你来说可能微不足道,但对农村女孩来说已经很多了。至少,她们不必在烈日下工作,我们提供三餐和一张床。我相信有很多新移民会免费工作,只要有这些条件。”
与“流动人口”一词所唤起的流动形象相反,这些农民通过地方性网络进入了“老板的工厂”。对工人的采访揭示了这些地方性网络调解老板工厂劳动力供应的五种主要方式。首先,地方性关系对于使女性能够初次前往深圳至关重要。一些地方性关系充当了父母托付孩子的监护人。在春节假期期间,返乡的地方性关系传播了关于工作机会、生活水平和工资的信息,并帮助年轻人获得父母的许可。许多逃离家庭的女性依赖地方性关系资助初次旅行,并在陌生城市提供初始住宿:
“我们到达的第一晚已经很晚了。我的表亲带我去我们一个同乡的宿舍。第二天,我去沙井找我二姐。我偷偷溜进宿舍,在那里躲了一个星期,直到那家工厂贴出招聘通知。我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和我姐姐在同一层。后来,当 Liton 招聘时,我和我姐姐一起离开,来这里找我三姐。”
其次,地方性网络是工人非法获得工厂招聘时要求的三份必要证明的渠道:暂住证、身份证和婚姻状况证明。工人请同乡找专业人士伪造文件或贿赂当地公安局官员,支付100到200元。在许多其他情况下,同乡直接借用与自己面部特征相似的同乡的证件。这导致了工人中普遍使用假名。第三,获得和更换工作以及晋升依赖于同乡的推荐。地方性网络传播了正在招聘的工厂信息,并将同乡推荐到好的工厂,即那些工资较高、宿舍体面、水电供应稳定和食物良好的工厂:
“如果你不能说出在那里工作的熟人,工厂门口的保安不会让你进去。这在许多工厂都是一样的。有时你必须付钱给保安,他会声称你是他的熟人,并带你去找经理。但如果你有熟人,即使他们不公开招聘,你仍然可以得到一份工作。”
第四,地方性网络成员之间经常提供经济援助,以应对工资延迟支付或紧急情况。涉及的金额从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一位女性解释了两个经济困难的情况:
“通常当我们寄钱回家时,我们希望寄更多,因为去邮局很麻烦。所以我们向几个人借钱,这样我们可以每次寄一大笔钱。我们通常在下一次工资到账时还清债务。……有一次,我叔叔和其他四个同乡因为无证工作被公安局逮捕。其他同乡赶紧告诉我,让我拿1200元去保释他。我立即向五个同乡借钱,每个人都借给我一些。”
第五,在生病时,工人依赖工厂里的同乡做各种杂事,如从食堂取食物、打水洗澡、洗衣服和陪她们去诊所。同乡也是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在所有这些方面,工人依赖地方性网络生存。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有兴趣将地方主义纳入车间实践,以促进和合法化控制,并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最后,女性只是短期工人,更关心婚姻而不是工作的印象也源于她们在公司中的短期任职。然而,这种高流动性也是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深圳新工厂的激增争夺相对有经验的工人,以及大量移民工人竞争进入更好的工厂。
香港和深圳劳动力市场的三个差异对于理解两种体制很重要。与深圳大量移民劳动力供应不同,香港的劳动力市场紧张,缺乏有经验的工人。留在制造业的工人拥有长期的公司任职,与深圳工人在工厂之间的高流动性形成对比。最后,香港工人依赖家庭和亲属,而不是地方性网络,来获得政府或雇主未提供的关键资源。
自1980年代初以来,深圳的工业化与香港的去工业化同时发生,制造业在总就业中的贡献从1981年的47%下降到1989年的29.7%。电子行业(不包括电子手表和时钟制造商)的从业人数也从1980年的93,005人减少到1991年的59,341人,反映了工厂向内地迁移的趋势。此外,制造业劳动力的老龄化明显,与深圳青少年工人的主导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在香港,制造业中25岁以下女工的比例从1971年的50.9%下降到1986年的27.7%。因此,Liton 中已婚工作母亲和祖母的集中反映了香港的总体情况。这些已婚女性的平均公司任职时间为10到15年,因此她们在生产 Liton 的高保真模型方面非常有经验。由于在衰退行业中招聘劳动力的困难以及女工的公司特定经验,管理层看到了霸权控制形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然而,这种霸权体制的家庭特征根植于女性对家庭的依赖,管理层有意识地顺应了这种依赖。
对在香港 Liton 工作的女性的工作历史分析表明,两个共同特征对我的分析至关重要。首先,许多女性经历了间歇期,期间她们依赖丈夫的收入生存,要么是因为她们是没有独立收入的全职母亲,要么是因为她们是收入低于生活工资的外包工。作为 Liton 的全职工人,这些女性在为家庭金库做出贡献的同时,继续依赖家庭的资源。其次,亲属在育儿和家务方面的帮助是决定她们工资就业不同模式的关键因素。一位女性回忆了她作为工作母亲的职业生涯的几个阶段是如何受家庭环境限制的——全职母亲、外包工、半日制工作和全日制工作。
“我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一直待在家里。六年来,我在家缝制棉手套。当我的小儿子上小学时,我成为了 Liton 的兼职工人。我上早班,时间安排得很完美:我的小女儿下午1点放学,而我12:30下班。我去市场买新鲜食材,然后为我们俩做午饭。后来,当我的小女儿上初中时,我开始在 Liton 全职工作。”
同样,她的一位同事在家庭环境允许并需要她进入有偿工作时成为了一名工厂工人:
“我结婚一年后生了第一个儿子。那是1965年。之后,我每年生一个孩子,一共生了四个孩子。有四个小孩,我怎么能工作呢?所以全家都靠我丈夫,他是一家裁缝店的裁缝。当我的小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我们负担很重,要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我的二女儿已经足够大,可以接送最小的孩子上学,所以我丈夫同意让我去工厂工作。……多年来,我早上上班前为他们做早餐和午餐。晚上下班后,我去市场购物,回家做晚饭。”
一些女性比较幸运。在亲属的帮助下,她们在成为母亲后能够继续工作。一位在 Liton 工作了25年的女性得到了她嫂子的帮助:
“我嫂子在工作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我只在周末接孩子回家。当然,我付钱给她。但因为我们是亲戚,这比找其他保姆便宜。两个孩子每月要花3000多港元。如果是外人,费用会翻倍。”
女性的家庭环境不仅决定了她们何时进入或退出有偿工作,她们的家庭责任也使她们依附于能够适应她们家庭责任的特定雇主,并让她们放弃了其他提供更高工资的行业的工作机会。访谈显示,Liton 允许女性工人在一系列考虑因素之间取得平衡:拥有独立收入、履行对子女和家庭的承诺、保持社交性而不损害她们的女性气质。女性工人并不想最大化任何一个目标,而是希望兼顾潜在的竞争目标。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假期制度和管理政策允许这种整合。这位工人的推理反映了许多同事的想法,她们更喜欢在 Liton 的工厂工作,而不是更高薪的服务工作:
“我们这些妈妈很高兴有星期六休息。而且请假很容易,比如你生病了或孩子的老师要见你。……服务工作通常晚上10点才下班。我可以赚更多,但我没有时间陪女儿。那样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兼职服务工作是一个选择,但收入太少。所以,就工作时间和收入而言,Liton 还不错。……”
总之,工厂工作的条件和工人赖以生存的社区资源在边境两侧的女性工人中有所不同。深圳的地方性网络和香港的家庭与亲属调解了劳动力供应,并提供了国家和雇主未向女性提供的资源。将地方主义和家族主义纳入各自的工厂体制,减少了管理层的财务负担,合法化了管理控制,并满足了女性工人的日常利益。
结论
为了解释全球经济重组过程中对女性工人的多样化控制模式,Burawoy 的生产政治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类别:工人的依赖条件。然而,在亚洲背景下——本研究的香港和深圳——国家是工人依赖条件的较不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地方社区机构如地方性网络、亲属和家庭则更为重要,它们支撑了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本研究表明,由于这些社区机构调解了女性劳动力的供应,并为维持女性工人的生计提供了手段,管理层和工人都有兴趣将这些机构纳入车间实践,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工厂体制。
与此相关的是,工厂体制的概念必须被重构,以便这些体制被视为谈判和性别化的秩序,而不是 Burawoy 所建议的国家与企业互动的性别中立产物。尽管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工人提出了管理层必须满足的要求,即使只是为了更有效的控制。地方主义和家族主义的纳入反映了工厂体制的谈判元素,因为这些工作场所特征是管理层适应工人需求的结果。此外,性别在生产政治理论中很重要,因为管理层和工人诉诸女性的性别来设计和合法化控制与抵抗。工厂体制的性别特定维度是资本与劳动之间谈判的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女性和工业工作的女性主义文献必须开始理论化女性性别在工业工作场所中的多样化建构方式。本研究表明了两种这样的建构:“少女工人”和“主妇工人”。我得出结论,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差异解释了车间中女性的多样化建构,以及性别作为阶级关系构成要素的多样化机制。这种对劳动力市场、工人社区网络、企业和国家的本地和复杂关联的关注,对从事性别和跨国公司(TNCs)研究的社会学家特别有启发。本研究揭示了一种替代类型的跨国公司,它从事出口加工,但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子公司不同。在华南地区,这些跨国公司由香港和台湾投资者组成,往往是中小型独立制造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使用低技术水平,热衷于削减生产成本(Hsing 1994)。这些跨国公司避免国家政府的干预,而国家政府通常不会正式监管这些小投资。由于财务限制,这些跨国公司无法通过企业福利主义来控制或留住劳动力。在这些条件下,管理策略,包括对女性工人的控制手段,较少受中央政府政策、工会主义或世界金融机构(Ward 1988; Nash 1983)的影响,而更多受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组织和工人社区网络等本地条件的影响。
李静君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师。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东亚的性别与职业,以及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性工作与经济重组。
REFERENCES
Beneria, Lourdes and Martha Roldan. 1987. The Crossroads of Class and Gend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averman, Harry. 197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Brinton, Mary. 1993. Women and the Economic Miracl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5.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England: Verso.
———. 1992. “Extended Case Method.” Pp. 271–87 in Ethnography Unbound, edited by M. Burawoy et a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kis, Wendy and Cynthia Enloe, eds. 1983. Of Common Cloth: Women in the Global Textile Industry. Washington, DC: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Cho, Soon-kyoung. 1987. How Cheap is “Cheap Labor?” The Dilemmas of Export-Led Industrializatio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dwards, Richard. 1979. Contested Terrain. New York: Basic Books.
Elson, Diane and Ruth Pearson. 1981. “The Subordination of Wo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actory Production.” Pp. 18–40 in Of Marriage and Market, edited by K. Young, C. Wollowitz, and R. McCullagh.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England, Joe and John Rear. 1981.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rnandez-Kelly, Maria Patricia. 1983. For We Are Sold, I And My Peopl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80. “Two Lectures,” pp.78–108 in Power/Knowledge, edited by C. Gordan. New York: Pantheon.
———.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Vintage.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djhosrandi, Joanna. 1990. “Facon: Women’s Formal and Informal Work in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Kavala, Greece.” Pp. 64–81 in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s, edited by K. W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ochschild, Arile. 1983.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Viking.
Holland, Dorothy C. and Margaret A. Eisenhart. 1990. Educated In Roman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ssfeld, Karen. 1990. “Their Logic Against Them.” Pp. 149–78 in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edited by K. W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sing, You-tien. 1994.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Transnational Networks Between Taiwanese Investors and Local Bureaucrats in Souther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cific Rim UC Berkeley–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nference on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apitalism, August 8–13, Singapore.
Hsiung, Ping-chun. 1991.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Kanter, Rosabeth Moss. 1977. 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Kim, Seung-kyung. 1990.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Autonomy: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the Korean Economic Miracl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ung, Lydia. 1983.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abor Department. 1992. Labor an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Lamphere, Louise, Patricia Zavella, and Felipe Gonzales. 1993. Sunbelt Working Moth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ee, Ching Kwan. 1993. “Familial Hegemony: Gender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on Hong Kong’s Electronics Shopfloor.” Gender and Society 7:529–47.
Lethbridge, David and Sek-hong Ng. 1984.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mployment.” Pp. 70–104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edited by D. Leithbrid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ung, Chi Kin. 1993. “Personal Contacts, Subcontracting Linkag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Zhujiang Delta Reg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3:272–302.
Levin, David and Stephen Chiu. 1993. “Dependent Capitalism, a Colonial State and Marginal Unions: The Case of Hong Kong.” Pp. 187–222 in Organized Labor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dited by S. Frenkel. Ithaca, NY: ILR Press.
Liao, Pak Wai, Yu-jim Wong, Yun-wing Sung, and Pui-king Lau. 1992. China’s Open Door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Survey Report. Hong Kong: Nanyang Commercial Bank.
Lim, Linda. 1978. Women Worker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n Arbor, MI: Michigan Occasional Papers in Women’s Studies.
———. 1981. “Women’s Work in Multinational Electronics Factories.” Pp. 181–90 in Wome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dited by R. Dauber and M. Cai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1983. “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Patriarchy: The Dilemma of Third World Women Workers in Multinational Factories.” Pp. 70–91 in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dited by J. Nash and M. P. Fernandez-Kell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ui, T. L. and S. Chiu. 1993.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Under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5:63–79.
Maruya, Toyojito. 1992.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Province.” Pp. 126–46 in Guangdong, edited by T. Maruya.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ies, Maria. 1986.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London, England: Zed.
Nash, June. 1983. “The Impact of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on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Labor Force.” Pp. 3–38 in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edited by J. Nash and M. P. Fernandez-Kell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ash, June and M. P. Fernandez-Kelly, eds. 1983. Women, Me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O’Harlon, Rosalind. 1988. “Recovering the Subject: Subaltern Studies and Histories of Resistance in Colonial South 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22:189–224.
Oi, Jean. 1989.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Ong, Aihwa. 1987. Spirits of Resistance and Capitalist Discipline. New York: SUNY Press.
———. 1992. “The Gender and Labor Politics of Post-Modernit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279–309.
Pyle, Jean L. 1990. “Export-Led Development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Women.” Pp. 85–112 in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edited by K. War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osen, Ellen I. 1987. Bitter Choices: Blue Collar Women In and Out of Work.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oy, Donald. 1958.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158–68.
Salaff, Janet. 1981. Working Daughters of Hong Kong.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Joan. 1988.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t, Victor and Siu-lun Wong. 1989.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in an Export-Oriented Economy.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mart, Josephine, and Alan Smart. 1991. “Personal Relations and Divergent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5:216–33.
Solinger, Dorothy J. 1991. China’s Transients and the State: A Form of Civil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USC Seminar Series no.1.
Sung, Yun-wing. 1992. Non-Institu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Via Cultural Affinit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m, Siu-mi Maria. 1992. The Structura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omen Workers of Shekou Industrial Zon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 HI.
Taylor, Jeffrey R. 1988. “Rural Employment Trends and the Legacy of Surplus Labor, 1978–86.” China Quarterly 116:736–66.
Thompson, E. P. 1978.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133–65.
Walder, Andrew. 1986.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ng, Xue Ming. 1992. “Guangdong: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1980s.” Pp.18–48 in Guangdong, edited by T. Maruy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rd, Kathryn. 1988. “Women in the Global Economy.” Women and Work: An Annual Review 3:17–48.
———, ed. 1990. Women Workers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Ithaca, NY: ILR Press.
Williams, Christine L. 1989. Gender Differences at Work.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Diane. 1992. Factory Daughter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avella, Patricia. 1987. Women’s Work and Chicano Famil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Zhongguo Tongjiu. 1992.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China (in Chinese). Beijing, China: Zhongguo Tongjiu.